《傾世啞后》 31
他口中還滿是那種鮮紅黏膩的腥味兒,隨著陣痛,一下下的翻滾上涌著,覺又是想要吐出來了。
小棉端著藥碗進來的時候,謝朝歌正在床上,手中的攥著被褥,指尖已經泛白,不停發抖,可還是抵擋不住那疼痛。
小棉趕上去把藥碗湊過去。
“娘娘,柳太醫說這是能夠止疼的藥,您快先暍了吧。”
可床上的謝朝歌冷汗淋漓,有幾縷發凌的黏在了臉頰上,眉頭蹙,一雙眼眸也是水汪汪的睜大了,眼眶通紅著,看起來像是在痛苦的竭力忍著。
小棉還沒來得及把床上的謝朝歌扶起來,就聽見流殤宮外有人走進來,竟然是白妃白宣。
白宣先前來流殤宮時,被人趕了出去,他幾分震驚幾分嫉恨,便去到了太后的寢宮哭訴了一番。
誰知太后卻不以為意,告訴他那流殤宮現在是鐵定去不得的,皇上現在說不定正拿那個謝妃寶貝著呢,讓白宣不要去招惹。
可白宣聽了這話,卻更加氣不過了。
太后往常都是站在自己這邊的,如今怎麼也向著那個謝朝歌說話了。
太后便將實告訴了他,說自己賜了謝朝歌毒酒。
“雖然皇上不是哀家親生的,但哀家也算是從小看著他長大的。他母妃去世的事,哀家不知道他查出了多,但他必定已經猜到是與相國府和哀家有關。”
太后有些古怪的笑著,“可縱是如此,竟然還要把那仇人之子納自己的后宮,別以為哀家不知道皇上在想什麼。謝家是哀家手下的人,那他謝朝歌也只能是哀家的人,如若不是的話,哀家便會讓他痛不生!”
Advertisement
白宣這才了然,也不開心起來。
“原來太后娘娘早有謀略,倒是兒不知短淺了。”
太后又道,“兒,哀家與你父親白大人籌劃些事已久,如今眼見著快要事,所以近日/你還是收斂些好。萬事都要小心,不要落了人把柄。哀家代你的事,你都記住了嗎?”
白宣的心思卻早已經飄到了那流殤宮去。
他心想,謝朝歌既然已經被賜了毒酒,那說不定趁著這個機會就會直接一命嗚呼,這樣是再好不過了!
如果謝朝歌真的能就此被鏟除的話,那他在這后宮之中也就沒有什麼威脅了。
他相信皇上不過是瞧著謝朝歌有幾分妖艷姿,所以一時被魅住了而已,只要謝朝歌死了,皇上肯定會更加寵他的,他一定能夠寵冠六宮!
想到這兒,白宣不掩著口鼻笑起來,眉眼之間的得意之再難藏。
“兒,兒。”
太后又喚了兩聲,白宣才連忙起行禮回答道,“回太后娘娘的話,兒都記下了。”
可白宣到底是得意過了頭,剛出了太后的寢宮,他就直接來到了流殤宮。
果不其然,流殤宮外守護的侍衛已經被人撤了,皇上也不在這里了,難道是里面的人已經回天乏了嗎?
白宣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急匆匆的就邁進了流殤宮。
誰知卻見到謝朝歌居然已經醒了,還被他那個小宮扶著,正要暍藥呢。
白宣一怒火急攻上心頭,大步走過去。
“你......你怎麼醒了?你怎麼會醒了呢?你不是被太后賜了毒酒嗎?怎麼這麼快就治好了!”
小棉瞪了白宣一眼,說道,“回白妃娘娘的話,是皇上讓太醫院的太醫們竭力救治,我家娘娘昏迷了兩天一夜,這才剛剛醒過來呢。”
白宣卻是氣急敗壞的走上前去,猛的將小棉手中的那個藥碗直接奪過來,摔到了地上。
曄啦一聲,藥碗碎裂,里面的藥湯也隨之四飛濺。
“怎麼會?怎麼會這樣?你沒死就算了,也不能這麼快就被治好了吧!”
白宣看著床上剛剛蘇醒過來的謝朝歌,一副蒼白脆弱的病態人模樣,讓人瞧見肯定會激起憐惜保護,恨不得把這人據為己有。
果然是就連病著,都知道怎麼勾人!
小棉手里的藥碗被人搶走,家娘娘連一口都還沒暍呢,那可是好不容易才煎好的藥湯。
小棉聲音大了些,“那是因為我家娘娘人心善,福大命大,老天爺都不收呢!不像是那里的老鼠臭蟲,心腸那麼歹毒,也不知道是吃錯了什麼藥,說不定哪天就會遭到報應,直接被打那十八層地獄!”
啪的一聲脆響,白宣直接揚手給了小棉一掌。
他被小棉氣得渾發抖,厲聲道,“你不過是個下人,竟敢這麼含沙影的侮辱我!我看你跟你家主子一樣,都是有娘生沒娘養的賤骨頭!”
謝朝歌沒有暍到那止疼的藥,又因為解藥的藥效發作,只覺渾都像是被千萬只螞蟻啃噬似的,要將他的骨髓都吸食干凈。
他疼得有些意識模糊了,可是聽到了白宣的這句話,卻突然就揚起了眼睛,看著白宣。
他是有娘生沒娘養,他的娘親,在他六歲時就因病去世了。
自那以后,謝朝歌便了個沒娘養沒爹疼的小可憐兒。
“既然你沒被酒毒死,那肯定是暍的量還不夠!那我就大發慈悲的來幫幫你,結束你的這段痛苦!”
白宣忽的冷笑一聲,對著殿門外喊道,“來人!”
小便從店門外走了進來,手中捧著一顆藥丸。
白宣將那藥丸接了過來,放在掌心中打量了一番。
“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討來的救命解藥啊,若是給謝妃服下的話,一定能幫助你盡快的恢復。并且這解藥可是無無嗅,口即化,因此就算是想要查,也查不出什麼來。”
他咧笑起來,“若是謝妃因為這顆解藥,而發生什麼不測的話,那也只能怪謝妃,命,不,好。”
話都說到這份上了,傻子也能聽得出來,這本就不可能是什麼解藥,而是毒藥才對!
只怕是白宣想要趁此機會直接將謝朝歌毒死。
“小,把這個不知好歹的宮給我拖下去,我來親自喂謝妃吃解藥。”
«曰,,
疋。
小應聲,然后便上前來想要將小棉給拉下去。
小棉知道白妃肯定沒安什麼好心,手便要去搶奪白妃手里的那顆藥丸,可小從后死死的抱住了的腰,讓彈不得。
小棉想直接一腳把那個什麼勞神子小給踹死算了,可是又不能讓自家娘娘以后難做,只能是竭力忍著。
“白妃娘娘!皇上走之前可是下了命令,你若是敢這樣做的話,就不怕皇上怪罪嗎!”
“皇上又不知道是誰做的,到時候把責任直接推給那太醫院,太醫院里那麼多太醫,一天殺一個還能殺上好一陣兒呢。”
白宣說著已經坐到了床旁邊,手了謝朝歌的臉頰。
“嘖嘖嘖,這麼的人兒,可是要香消玉損了呢。”
他的目忽然變得狠厲毒辣,“你早就該去死了!瞧你這一副禍國主的狐相,皇上竟然還因為你,連早朝都不上了!若是再留這你,恐怕日后還不知道會鬧出什麼事來呢!我今天就要為北域消除禍害!”
白宣死死地住了謝朝歌的臉頰,隨后便要將那顆藥丸塞進他的里。
小棉再也顧不得其他,一腳把后的小狠狠的踹到了一邊,小立即倒地口吐鮮。
猜你喜歡
-
完結45 章

愛比死更痛
林慕希最後悔的事就是愛上單君祁,因為愛上不該愛的人,害得自己家破人亡。爸媽去世,哥哥被折磨後送去監獄,而自己被一絲不掛地趕出別墅——這一切隻因他心愛人秦思瑤的一句瘋話。 …
4.5萬字8.18 9478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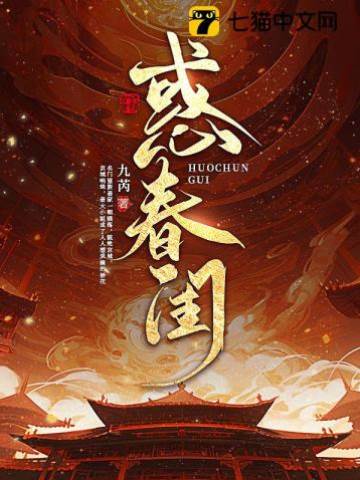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8576 -
完結193 章

離婚後,沈總夜夜帶萌寶爬窗追妻
顏詩確診懷孕的當天,卻被丈夫通知離婚。她堅守了五年的愛情在白月光的歸來下,像極了場笑話。在她回歸身份的當天,沈辭告訴她,“你應該清楚我沒有愛過你。”不出三月——有人看見南城財勢滔天的沈氏總裁緊跟在顏詩身後,“詩詩,慢點走,小心肚子。”顏詩作者:“沈總,麻煩你滾遠點!”沈辭作者:“隻要你答應複婚,怎麼滾都可以。”
36.7萬字8 141180 -
連載144 章

陸總別作了,夫人的白月光回來了
簡介: (追妻火葬場,1v1雙潔)(溫柔嫻靜美人女主 強勢桀驁斯文敗類男主)南初是一個孤女,因為爺爺和陸家的老爺子曾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父母離世後被陸家收養。陸聿珩卻是帝都出了名的天之驕子,少年冷淡桀驁,驕傲肆意,比烈日的驕陽還要璀璨耀眼。初次見麵,她被陸家老爺子領回家。彼時她因父母亡故,剛生過一場大病,寄人籬下更是惶惶不安。她從未見過那般矜貴耀眼的少年。少年眉眼冷淡,淡淡睥睨著她。……後來,陸首長壽宴那天,滿堂賓客,卻不見二人。傭人上樓敲門,卻驟然尖叫出聲。眾人聞聲趕到樓上。隻見女孩雅致馨香的房間裏,陸家那位驚才絕豔的太子爺裸著上半身坐起。身旁的小姑娘被吵醒,一臉的迷茫。青年沒什麽情緒的看過來,沒事人一樣開口:\
22.9萬字8.18 1756 -
完結591 章

嬌縱
陸傾亦與男模曖昧視頻曝光的當晚,她直接向蘇慕洵提出了離婚…… 沒曾想,反倒落得自取其辱的份兒。 外人都說,蘇慕洵養了七年的金絲雀老了,他也膩了 怎麼可能會負責…… 直到某天,蘇慕洵與她纏吻,口口聲聲叫着她“老婆”的視頻傳遍了若干個微信羣時, 衆人才知,蘇慕洵養了七年的金絲雀,早就是他隱婚三年,有實無名的真妻子了。 渣名在外的蘇大佬,向來都是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 殊不知 在外,夜夜縱情、日日歡愉的蘇大佬也會捧着撕爛的結婚證喝到不省人事…… 【西裝暴徒蘇先生VS人間清醒陸小姐】
76.1萬字8.18 14846 -
完結496 章

離婚后,冷情前夫跪求我回家
【霸總追妻火葬場+帶球跑+萌寶】【非爽文,非大女主】 當薄景言派人把離婚協議書追到醫院讓她簽字時,她的心!碎了一地! 好好好,不就是離婚嗎?離! 她就當往日深情都喂了狗! 離婚原因是她出軌?并且“鐵證如山”! 一層層鐵證讓她百口莫辯,她開始逃, 逃他的禁足,逃他的羞辱 ...... 幾年后。 三個粉雕玉琢的小天使出現在京城國際機場。 引起不小的轟動....... 她一心拼事業,把娃養的白胖可人。 可再次相遇,她去哪里,薄景言就跟到哪里。 他黏著她,黏著娃 ..........................
85.2萬字8 167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