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鍾》 第18章
18
清晨尚早,府中長廊傳來輕巧腳步聲。
白萍拾著擺一路小跑,片刻之前聽主院侍來傳話,說是莊主有急事尋,當即便令心有不安。
在白萍看來,唐橋淵有用過一個「急」字,因此立刻放下了手中事務,跑得微微小。
然而其實傳來吩咐的那人並沒有急不可耐,唐橋淵清晨醒來時思緒混沌,腦中像是空一片,又像是充斥著無數雜畫面,攪得他茫然生,更在無意道出「急」字之後,自己也到莫名驚訝。
白萍跑到主院,難得不及問候便自行進到寢房之中,開珠簾才總算停下腳步。這姑娘氣息不平,抬眼之後頓了一頓,見唐橋淵並未抬首看,而是沉默坐在桌旁,低頭著手中走神。
「莊主。」白萍漸緩過來,將手扶在腰側福問禮。
唐橋淵聽見聲音終於回神,轉頭,分不清是在疑問還是陳述,緩緩開口道:「我過親了。」
白萍愣住,彼時才看向空空床鋪,約浮起什麼念頭,幾分震驚,亦有幾分困。
唐橋淵將手中東西轉了一面,看著上面略顯糙的繡字試探著低聲念道:「‘素’……方素?」
白萍不作回答,猜不著任何前因後果,此時除了詫異不解唯剩張而已,難得會遇著何事讓完全不知其裡,很有一番無以招架的滋味。
唐橋淵蹙的眉頭漸漸舒展下來。
這人今晨醒來之後,仿佛做了一場長夢,夢中片段皆在腦中,卻朦朦隔了一層細紗,如同旁觀他人演繹。
其實半月以來的諸多細節,唐橋淵都並未忘記,只是此刻卻備不真實,膛沉沉悶悶的,道不明緒究竟是如何。
Advertisement
唐橋淵沉默許久,又看了看白萍,忽然問道:「我很喜歡?」罷了見沉默,好不容易意識到自己的失常,終於搖頭解釋道,「秦眉莞給我下了毒,差錯,弄如今這樣。」
白萍恍悟,驚得睜大了眼,腦裡湧上無數想法,想那人愈發不知好歹,竟敢荒唐到如此地步,恨得咬牙切齒。到最後又冒起一個略顯失意的想法:難不寶在方素上,真是想得太過簡單……
「那莊主的意思,表小姐該如何?」
「容後再說,」唐橋淵搖頭,「表舅那邊我總不能全然不顧。」
這人提起長輩,白萍自然無可辯駁,只能又問道:「那夫人……」話落半句,等這人自行考慮。
「夫人……」唐橋淵低低念了幾遍,不知想著什麼,搖頭輕笑,把手中荷包系到腰間,回道,「既然是夫人,便要接回來,拜堂親總是真的。」
白萍眉角輕輕一,施禮道:「奴婢派人去城外尋找。」
「不必,」這人想了一想,記憶雖有些輕飄飄的不實之,但卻輕易便能想起來,吩咐道,「備車去城東,還有,不許秦眉莞離開翡院,待我閒了……再想想如何才好。」
「是,」白萍眼笑意,不掩飾心中私怨,欣然應道,「奴婢定讓人圍籠整座院子。」
唐橋淵這人慣來護短,笑一笑便過,假意不察覺的私心。罷了站起來,順手又了腰上荷包,腦中雖還茫然迷糊,卻無端端到舒暢快意。
昨夜一場大雨徹底轉了時節,晴後耀目,氣候愈熱。
盈卷私塾裡聲嚷嚷,正是休息時候,汪先生手捧書卷慢慢踱步於院中,頃,見一輛悉馬車停靠在私塾之外。
汪先生停下腳步,微斂眸去,等著來客掀簾下車。
唐橋淵邊彎著淺淺笑容,院後向他行來,也不問方素是否在此,施一記晚生禮,直言道:「叨擾先生,在下前來接子回府。」
汪先生昨夜才一禮,今日又一禮,聞言著頜下胡須沉片刻,無奈輕歎,手中書卷指一指側院方向,搖頭笑道:「能得一合心之人不易。」
「先生說得是。」唐橋淵不作解釋,再道一聲「多謝」,向側院行去。
不待走近,約便可聽得裡面傳出的對話聲。似乎是一位老婦人,正耐心指點什麼,方素偶爾低聲回應,或道出簡單疑問。
「這買賣的東西啊,不比自家用,是結實怎麼行,還要巧好看……你這針法不夠好,來我再教教你。」老婦人說著,從方素手裡接過線活,過不片刻又心疼歎道,「不過也是,你一個男兒做這些活兒也是勉強了點……你要什麼盤纏,老頭子拿給你便是,你先前贈給私塾不,你還不要……」
方素偏頭看著手頭作,也不嫌年邁囉嗦,搖頭回道:「師娘,那不是我給私塾的銀子。」
正行近之人聞聽此言腳步微頓,隨後繼續向裡走,聽著老婦人那句「強得很」,出現在兩人眼前。
方素約覺得余中有人,不轉頭來看,眼一瞬面上神滯住。
他一夜未睡,本就神略顯恍惚,很有幾分不可置信,懷疑出現在眼前之人究竟是否真實。方素想要開口喊他名字,話到邊卻不知如何稱呼才好。
不過一瞬之間,他竟想了許多。想唐橋淵為何還記得他,為何還來尋他,是否厭他骨,是否要親自趕他離開麟州城……
——如若不是,會不會……秦眉莞給他的解藥其實有假?
他想得格外慌,眼神疏忽不定,還未來得及想明白時,那人卻已走近前,看了看他,對他出手來。
如此作悉無比,仿佛正是當初他下花轎之時,在紅喜帕之下看到的那只溫暖手掌。
方素怔然,本能地想要回應,手在途中時卻又恍然一驚,急忙想要收回。
唐橋淵瞧得分明,往前半步主握住那只手,帶他起,隨後向一旁老婦人頷首問候。
老婦人停下手中活,先前也見過這人一回,因而不疑,欣笑著把人送走。心裡不明真相,裡倒十分熱,以為兩人是鬧了矛盾,便只怕方素繼續置氣似的,說著滿寬話。
唐橋淵但管應「是」,把方素的手握在掌心,意外地到一份無比悉的覺,綿綿,竟很滿足。
方素懵懵地跟著他走,忘了剛才腦裡的擔憂都是哪些。
前院裡,白萍還在等著,看見來人之後彎眸輕笑,側面向汪先生,盈盈施禮道:「我家夫人與莊主鬧了小子,此番多謝先生照顧……」
汪先生但笑擺首。
馬車自城北大道穿行回府,方素局促坐在車,旁除了最令他掛心那人,還有一位白萍姑娘,讓他有話問不出口。
對座人確乎是變了一個模樣,不比從前親熱,卻始終帶著溫和淺笑看他,如舊目中多了幾許疑與興味。
唐橋淵已看出方素有話想講,但他不問,看他煎熬模樣暗自覺得討喜。
等到好不容易回到唐府主院,兩人終得獨,方素才帶著些心悸問道:「你……好了嗎?」
唐橋淵聞言一頓,隨即低笑出聲,驀然覺得如此好,這一回因果荒唐,而他誤打誤撞娶回家的夫人卻著實可。
想著他便頷首回道:「好了。」
這人說著,一邊往書桌後行去。方素離他幾尺,一直徘徊不近,站在原地隨著他轉雙眸。
唐橋淵假裝視若無睹,輕桌上畫紙,墨跡已干,紙上繪著些他從前並不畫的乖巧,他了眉梢,抬眼看看方素,又垂眼再看紙上小東西,覺得真是有幾分相像。
唐橋淵無聲彎,想起昨日擁方素在懷作畫的親暱樣子,心中微妙又,半晌聲音含笑,毫無預兆地開口講道:「‘樹妖對書生暗生愫,庇佑他不被其他妖所傷,卻因此不得不與之別離’……我昨日是不是講到這裡了?」
房中靜了許久,唐橋淵耐心等著,仿佛等了相當之久,終於聽見有聲音遲疑回道:「那……後來呢?」
他不住順眉,雙眸正視著他,道:「為了讓書生活命,樹妖毅然離去,為保書生萬全,不惜自己苦。後來書生忘了所有,圓滿一生,樹妖卻枯葉落,再無生機。」
「如此豈不是很悲慘……」方素聽得於心不忍。
唐橋淵低笑點點頭。
「是啊,親手栽種之樹淒涼收尾,究竟是傷人還是傷己?明明結局不必如此,這書生不是尋常人,難道還護不住一棵樹嗎?」
方素呆住,後知後覺,總算發現這人擅自誇大了結局,意在暗指什麼……
尚未說話回應,唐橋淵已自桌後行出,靠近他後探出手去,以手背輕他臉龐,像是親那日所為的溫作,又說:「我唐橋淵的夫人就該留在這裡為我所佑,你不必心有芥,既然信過一次,何妨不再信一次?」
話語擲地有聲,方素眼眶漸漸發紅,字字句句皆沉沉落耳裡。
「即便不是一見鍾,卻未嘗不可日久生……方素,留在我邊。」
猜你喜歡
-
完結222 章

退婚后被殘疾大佬嬌養了
真千金回來之後,楚知意這位假千金就像是蚊子血,處處招人煩。 爲了自己打算,楚知意盯上了某位暴戾大佬。 “請和我結婚。” 楚知意捧上自己所有積蓄到宴驚庭面前,“就算只結婚一年也行。” 原本做好了被拒絕的準備,哪知,宴驚庭竟然同意了。 結婚一年,各取所需。 一個假千金竟然嫁給了宴驚庭! 所有人都等着看楚知意被拋棄的好戲。 哪知…… 三個月過去了,網曝宴驚庭將卡給楚知意,她一天花了幾千萬! 六個月過去了,有人看到楚知意生氣指責宴驚庭。 宴驚庭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在楚知意麪前伏低做小! 一年過去了,宴驚庭摸着楚知意的肚子,問道,“還離婚嗎?” 楚知意咬緊牙,“離!” 宴驚庭淡笑,“想得美。” *她是我觸不可及高掛的明月。 可我偏要將月亮摘下來。 哪怕不擇手段。 —宴驚庭
60.5萬字8 33429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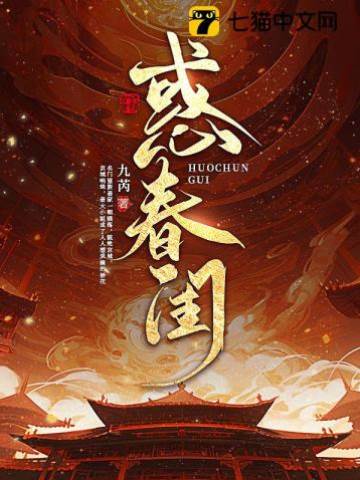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8576 -
完結142 章

蓄謀深愛
【我們家慢慢,做什麽都慢。但唯獨在愛我這件事上,快的不得了】 【網絡作家??高嶺之花】 宋慢怎麽也沒想過,自己有一天竟然會跟閨蜜的哥哥同住一個屋簷下?! —— 見麵的第一天,江淮為宋慢親手泡好了愛心自熱鍋。 宋慢一激動,蹦了某個曖昧的稱謂出來。 “江淮哥。” 江淮手一頓,熱水灑了一桌。 —— 宋慢站在空房間前看江淮,“你住哪個?” 江淮吊兒郎當地笑:“想對哥哥圖謀不軌?” 宋慢結巴了:“我隻是不知道你住哪個……” “所以想住我的?” —— 社團聚餐,某個女生端著酒走到了江淮麵前。 江淮扭頭問宋慢:“我能喝嗎?” 宋慢沉吟幾許:“你不是開車了?” 江淮點頭附和,“嗯,不喝了。” 女生不死心,掏出手機跟江淮加微信,江淮又看向了宋慢。 想到某人掉進廁所裏的手機,宋慢頭也沒抬,“你手機不是掉廁所裏了?” 江淮勾唇,“嗯,不加了。” 望著女生落寞的背影消失在桌旁,江淮滿意地摸了摸宋慢的腦袋。 第二天,學校裏傳開了。 江淮是個妻管嚴,幹什麽都得過問宋慢。 睡夢中的宋慢莫名成了萬千少女的情敵。 —— *小甜餅全文無虐放心入 *年齡差三歲 *為別人絕美愛情流淚的高光時刻
23.7萬字8.18 4866 -
完結191 章

小嬌奴
從小被賣作揚州瘦馬,好容易遇上年輕英俊的侯門三公子,以為得了歸宿,卻沒想到他卻將她送給他七十歲的父親!老侯爺遭不住,三個月即暴斃,他轉身又逼她去伺候他佛緣深厚的
36.7萬字8.18 3821 -
完結172 章

獨你悅人
高考後,樑空出國前跟駱悅人分手。 她喜歡他兄弟,他帶她到自己圈子裏玩,這場不見天日的暗戀,他裝得瀟灑,也算仁至義盡。 大一寒假,駱悅人來洛杉磯找樑空複合,在機場被偷了包,裏頭有一副給樑空織的手套。 樑空哄她說沒事,丟了就丟了。 離開洛杉磯時,她以爲樑空不愛她。 後來半個洛杉磯黑市都翻過來了,破屋裏找到那副被人踩髒的毛線手套,深淺兩種灰,雙股線,蠢斃了的連繩式。 洛杉磯四季如夏,那雙永遠用不上的手套陪他度過一千多個日夜。 —— 駱悅人的青春,因家庭變故而突生叛逆。 樑空曾慷慨送她離經叛道的機會,在她享受完刺激後,又將她安然無恙送回原軌。 山水其間,我愛你,從來無怨。
26萬字8.18 2839 -
完結222 章

啞寵
李書妤個“啞巴”,沒享公主尊榮,卻以公主之命死了。 晉國大亂,霍家鐵騎所到皆血流成河,那個傳聞中侮辱皇后的霍家家主,親自提刀sha上了晉陽城。 嗜血的將軍捏着淚雨的公主,“本君擔惡八載,不若坐實了這污名如何?” 他屠盡晉國皇室,獨留李書妤。 大軍撤離那日,不料有殘軍赴死,李書妤不幸被一箭穿心。 重生回來是在十六歲,霍家已然起勢。 李書妤被送往霍家平息恩怨。 大婚之夜她嚇的發抖,但還是在他掌心寫下—— “我乖,別sha我。” 他橫坐在牀頭,掃過瑟縮在牀尾的她,朝人伸手。 “過來,再寫一句。” 霍衍山一時興起寵着李書妤,最後竟也放不下。 多年鐵衣熱血,終寵她爲至尊。 【小劇場】 茫茫草原,李書妤被一羣莽漢盯着,“夫君——” 要走的男人一愣,說好的啞巴呢? “乖,把刀放下,有話好說。” “你丟我,不…要乖。” “要,誰不要誰狗。” 李書妤哇的一聲哭出來—— “你狗,丟我你不對。” 霍衍山:“…恩。” 小姑娘聞言,這才伸出兩隻細細的胳膊。 “那給你抱抱!”
33.5萬字8 45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