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鋒對決》 第94章
☆、94
吃完飯後,顧青裴一刻也不想多留。
他本就不該出現在原煬家裡,以倆人原來的關係,這太不合適。
原煬並沒有留他,但卻執意送他回去。
顧青裴堅持道:“我下樓打個車就行了。”
“我把你接出來,我當然送你回去。”
“不用,這個點兒很好打車。”
原煬雙手抱,瞇著眼睛看了他一會兒,“你是怕我知道你住哪兒?”
顧青裴皺了皺眉頭,他倒這麼想,不過以原煬現在莫名的態度,不知道更好。
原煬哼笑一聲,“我要是想知道,你攔得住我?”
顧青裴終於放棄,任原煬跟著他下了樓。
車開上主幹道後,顧青裴道:“前面那裡調頭,往東三環開。”
原煬懶懶地說:“我說了,我想知道,你攔不住我。”
顧青裴仔細品了下這話裡的意思,難道原煬知道他住哪兒?
過了幾分鐘,顧青裴就得到了答案,原煬真的知道他住哪兒,本不需要他指路。顧青裴口有些發悶,他很想質問原煬,這些莫名其妙的舉究竟是什麼意思。
一邊著朋友,嫌棄他年紀大,一邊給他做飯,連他住哪兒都知道。
他甚至開始懷疑,原煬是不是在耍他玩兒。
顧青裴沉聲道:“原煬,我現在忙得要命,沒空跟你拐彎抹角地玩兒一些遊戲,你究竟想怎麼樣,直接說出來。”
原煬目不斜視地看著前方,大言不慚地說:“很簡單啊,顧總的滋味兒一直讓我回味的,反正你也有需求,我也有需求,偶爾互相滿足一下怎麼樣?”
顧青裴諷刺道:“一個朋友應付不了你?”
原煬趁著等紅燈的時候,扭頭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包含曖昧和赤地,“那種小丫頭,哪兒比得上顧總讓人銷魂。我還記得顧總下邊兒那張小有多、多熱,我每次進去的時候,你的腰都直晃,屁夾得更,你那兩條纏著我的腰的時候,比人有勁兒多了,還有顧總被我幹得神志不清的時候,就會發出特別勾人的聲……”
Advertisement
“夠了!”顧青裴臉青一陣紅一陣,“原煬,別弄得自己跟發的公狗似的,好歹現在也是老闆了,要點兒臉好嗎。”
“哈哈哈哈。”原煬大笑道:“顧總高的時候比發的母狗還,要比臉皮,我覺得比起被男人幹得出來的顧總,我還矜持的。”
顧青裴被他氣得腦仁疼,看著原煬得意的模樣,他突然意識到原煬是故意的,原煬似乎就是想看他的窘迫和難堪,他越是生氣,原煬越是高興。
這人是不是他媽有病。
顧青裴冷笑道:“多謝原總誇獎,可惜你以後不著了。”
原煬握著方向盤的手了,他沒有說話,而是笑著出一口森白的牙齒,像是即將食的狩獵者。
顧青裴把頭扭向了一邊,心裡默默罵著原煬。時隔兩年了,原煬外在變得強大了,可是在卻愈發不是東西。而且對他懷有某種莫名的敵意,說的話句句帶刺兒。
原煬他憑什麼?憑什麼?
車開到他家樓下後,顧青裴一言不發地甩上車門走了。
原煬盯著他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門裡。
他失神地看著那個門,看了很久,直到手機鈴聲響起。
“喂,彭放。”
“原煬啊,幹嘛呢?出來喝酒吧。”
“懶得去。”原煬靠在椅子上,閉上眼睛,滿腦子都是顧青裴惱的樣子,那個表用來下飯,真是再味不過了。
“怎麼了呀,弄得自己七老八十似的,自從顧青裴從新加坡回來,你就不跟我們出來了,什麼意思啊。”
“你說什麼意思。”
彭放嘆了口氣,“我說兄弟啊,做人不能這麼倔啊,你這是不撞南牆不回頭啊。”
原煬淡淡道:“我就這一堵牆了,回不了頭。”
“我現在都鬧不明白你想幹什麼了,你要是想把人弄回來,你就得態度一點兒,不能跟有仇似的啊。”
“你以為只要服,就能打他?”原煬嘲諷地笑了笑,“你太小看顧青裴了,他的心比誰都。”
“那你想怎麼的。”
原煬斜著眼睛看著顧青裴做過的副駕駛,手指輕輕從座位上起一短髮,他低聲道:“我要讓他……離不開我。”
顧青裴回家之後,覺特別累。儘管他沒幹任何力活,可是一天的腦力勞簡直超過了負荷,不說白天在公司的忙碌,就是晚上那頓飯和原煬的針鋒相對,就夠他腦缺氧的。
他一開始還以為自己和原煬之間,終於能井水不犯河水,看來他想錯了。原煬在以戲弄他樂,也許是因為兩年前他的不告而別,也許是覺得當年對他的執著太過丟臉,總之,在原煬事業如日中天春風得意的時候,似乎他的存在,就是在昭告原煬過去的愚蠢和失敗。
所以原煬容不下他?
顧青裴嘲弄地笑了笑,作為原煬年無知時期一個最大的污點,他確實應該被抹去。
他躺在沙發上休息了一會兒,正打算去洗澡,手機突然響了。接通電話後,那頭傳來了一個又悉又陌生的聲音。
“顧總,你好啊。”
顧青裴愣了愣,突然反應過來這個聲音是兩年多不曾聽過的原立江的聲音,他頓了幾秒,淡道:“原董。”
“不錯,還記得我的聲音。”
顧青裴重新坐回了沙發,“這兩年記憶力有些下降,不過原董的聲音,還是不會忘的。”
“聽說你回北京了,時間過得真快啊。”
“原董給我打電話,不是來懷舊的吧。”顧青裴現在對原立江連表面上的客氣都省了,事過去了兩年,可每當他想起原立江給他的辱,他都依然無法徹底釋懷。
“我只是想問你幾件事。”
“是,我和原煬見過面了。”
“你知道我想問什麼?”
“除了原煬,還有什麼呢。”
原立江“呵呵”笑了兩聲,“說得也是。你回來時間不長,不知道你對原煬的事瞭解多。”
“非常有限,我和他兩年前已經結束,現在更沒有互相瞭解的必要,原董儘管放心,原煬已經走上了正道,我也不是個沒正事兒的人,你已經沒什麼好發愁的了。”
“是嗎。”原立江輕輕嘆了口氣,“可我的兒子兩年多沒踏進家門,你說我該不該發愁呢。”
顧青裴道:“你大可放心,原煬早晚會領著朋友回家見父母,這確實只是……早晚的事。”
原立江沉默了幾秒,才道:“他兩年前說過,除非帶著你進門,否則他不會回去。”
顧青裴心臟痛了一下,他揪了一下子,再慢慢鬆開,才道:“兩年前不經大腦的話罷了,人是會變的。”
“他確實變了很多,我有點兒不認識他了。”
顧青裴無意陪著原立江傷春悲秋地嘆教育兒子地失敗,這關他屁事。
他有些冷地說:“虎父無犬子,原董看到原煬的今天,應該高興才對。我只知道我已經做到了原董對我的要求,其他的,我就無能為力了。”
原立江聽出了顧青裴口氣裡的不耐,嘲弄地笑了兩聲,“顧總,我真不知道該恨你,還是該謝你了。”
顧青裴沒有回答,他本不在意。
結束通話後,顧青裴又一次到了疲憊侵襲全的覺,那種頭腦一片空白,四肢懶得抬起的倦意,讓他就想癱倒在沙發上不彈。
仔細想想,自己這兩年拚命賺錢,忙東忙西,最後除了荷包鼓了一些之外,似乎什麼都沒改變。
回家依然沒有一口熱飯,枕邊依然沒有一個知心人,生活中除了工作,再沒有別的重心。原煬都有了面的朋友,他卻還在糾結原煬戲弄的一句話,一個吻,這表示,他太寂寞了吧。
該找個人了,是該找個人了。
顧青裴第二天早上收拾完自己,拎著電腦包下樓了,剛走到小區門口他就愣住了。
原煬穿著一鐵灰的西裝,依靠在商務車上,眼神沒有目標地看著遠,裡慢慢吐著煙圈。
時彷彿一下子倒回了兩年,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原煬都會不知道早他多久等在樓下,從來不坐車裡,不管多冷,顧青裴也下樓,總是第一眼就能看到原煬在等他。
每天都在等他。
顧青裴眼睛有些發脹,那記憶裡的一幅幅畫面,翻湧上心頭,讓他重新面對這番場景時,第一反應竟是轉想走。
可惜他還沒,原煬已經發現了他。原煬把煙掐了,抬了抬下,“上車。”
“你這是幹什麼。”
“昨天不就說好了。”
“什麼?”
“你昨天坐我車走的,今早,我送你上班。”
顧青裴想說不用,可人已經在他眼前了。他懷著連自己都無法形容的心,上了車。
倆人沉默了十來分鐘,顧青裴突然問道:“你以前來接我的時候,都是幾點到?”
原煬怔了一下,沒料到他會問這個問題,他想了想,“七點左右。”
顧青裴想起,以前上班的時候,他都是七點半下樓,原煬每天都要等他至半個小時?
“為什麼這麼早。”
“我有很強的時間觀念,不能接遲到。”
“不能接遲到?你一開始的時候,遲到還了?”
“廢話,那是我故意的。”
顧青裴淡淡一笑,“是,你故意跟我對著幹。”
他幾乎已經忘了,他和原煬之間的關係曾經一度水火不容。可惜到了最後,水火不容的相模式都比互相捅刀子好。
顧青裴心裡又難了起來。
好不容易在那種讓人窒息的氛圍下挨到了目的地,顧青裴幾乎是逃進了公司。
一大早心鬱卒,他以為這一天的開始已經足夠倒霉,沒想到剛見到自己的財務總監,就得到了一個更讓他頭疼的消息。
他們抵押貸款的事進展得不順利,此時卡在了一個新調任的副行長手裡,原計劃這個月拿到錢,現在看來完全無了。
如果這個月資金不賬,他們的項目就要到嚴重影響,後果實在無法想像。
顧青裴吃了份書給他打包的早餐後
作者有話要說:白天去他市出差了,一個字兒沒寫,最近各種忙啊
猜你喜歡
-
完結224 章
一級教師[星際]
众所周知,灰末星的协风学院是全星际最乱的学院,其臭名昭著的程度,仅次于星际监狱! 这里没有任何一位正常的学生,也没有任何一位正常的老师,学院“教师”全部来自于十大佣兵团,各个体质a级以上,凶悍强大。 然而今天,协风学院突然迎来了一位新人—— 新教师明央容貌精致,气质脆弱,精神力f,体质e。 简直……简直就是废渣中的顶级废渣!! 整个协风学院……不,整个灰末星都轰动了。 无数人等着看明央笑话,猜明央几天内会被血肉模糊地扔出来。 …… 然而,第一天...... 他们听说明央轻而易举收服了挑衅的刺儿头。 第十天...... 他们见到协风学院原本画风最恐怖血腥的一个班学生跟在明央后面,集体乖乖叫老师。 第一百天...... 他们看到星际直播上的明央在星际学院联赛上虐爆了一众联邦学院大佬! 同时协风学院的疯学生们还上了新闻—— 因为其他星球的学生试图挖走明央去自己学校教课,疯学生愤而暴起,和比他们人数多几十倍的其他学生展开了大战! …… 明央在魔界快活了近万年。 在渡劫飞升时,却遭遇了天道暗算,险些被劈死,灵魂穿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年代,成为了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 看着面前一众暗暗呲牙时刻准备阴死自己的小崽子们,明央露出一个愉悦的微笑。 这里貌似很有趣呢。
48.2萬字8 9825 -
完結244 章
全球進化后我站在食物鏈頂端
末世来临,可怕的污染病卷席世界。 「我们把它叫做畸变,而后世的歷史书上也许会说,这是一场进化。」 进化界十分內捲。 今天那个人分裂两颗头,明天那朵花长獠牙,后天那条鱼迈开腿爬上岸…… 陆言:而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治疗污染病的医生罢了。 * 病患A:当初我长了18根触手,在海边吃[嗶——]吃的很开心。陆医生一来就帮我剪了17根,真是妙手回春! 病患B:我是一颗毒蘑菇,我的孢子剧毒还能寄生,我生了几十万个小孢子,给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陆医生一来就帮我践行了计划生育,这份大恩大德没齿难忘!病患C:我长了8张嘴,挑食还只吃荤,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屠宰厂。陆医生治好了我的挑食,信女愿一生吃素,换陆医生此生幸福安康。 陆言,食物链顶端,永远的神。
54.7萬字8 6878 -
完結2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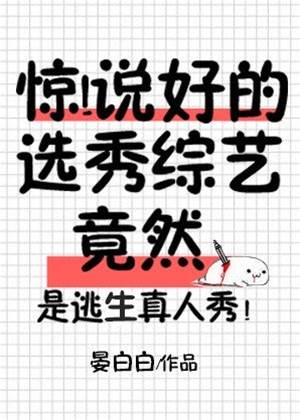
驚!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某娛樂公司練習生巫瑾,長了一張絕世美人臉,就算坐著不動都能C位出道。 在報名某選秀綜藝後,閃亮的星途正在向他招手—— 巫瑾:等等,這節目怎麼跟說好的不一樣?不是蹦蹦跳跳唱唱歌嗎?為什麼要送我去荒郊野外…… 節目PD:百年難得一遇的顏值型選手啊,節目組的收視率就靠你拯救了! 巫瑾:……我好像走錯節目了。等等,這不是偶像選秀,這是搏殺逃生真人秀啊啊啊! 十個月後,被扔進節目組的小可愛—— 變成了人間兇器。 副本升級流,輕微娛樂圈,秒天秒地攻 X 小可愛進化秒天秒地受,主受。
89.5萬字8 8616 -
完結506 章

媚婚之嫡女本色
陌桑穿越了,穿越到曆史上沒有記載的時空,職場上向來混得風生水起的白領精英,在這裏卻遇上讓她恨得咬牙切齒的克星,高冷男神——宮憫。 他嫌她為人太過陰詭狠毒。 她嫌他為人太過高冷孤傲。 本想無事可做時,虐虐渣女渣男,逗逗小鮮肉。 豈知一道聖旨,把兩個相互看不順眼的人捆綁在一起,組成嫌棄夫婦。 自此兩人過上相互猜測,彼此防備,暗裏算計,夜夜心驚肉跳的生活。 豈知世事難料,兩個相互嫌棄的人看著看著就順眼。 她說“你是護國賢臣,我是將門忠良,為何跟你在一起,總有種狼狽為奸的覺悟。” 他說“近墨者黑。” 陌桑點點頭,確實是如此。 隻是,到底是誰染黑誰啊? 再後來…… 她說“宮憫,你是不會笑,還是從來不笑?” 他看了她十息,展顏一笑“陌桑,若知道有一天我愛你勝過愛自己,一開始就不會浪費時間防備你、猜疑你,而是把所有的時間用來狠狠愛你,因為一輩子太短,我怕不夠愛你。” 陌桑咽著口水道“夫君,以後千萬別隨便笑,你一笑,人就變得好風騷……” 宮憫麵上黑,下一秒就露出一個魅惑眾生的笑容“娘子放心,為夫隻對你一人笑,隻對你一人風騷。” 某女瞬間流鼻血…… 【這就是一個白領精英穿越到異世古國,遇上高冷男神,被帝王捆綁在一起,相殺互撕,最後相親相愛、強強聯手、狼狽為奸的權謀愛情故事。】
187.7萬字8.18 3351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