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謀》 第305章 回絕親事
任家爲燕北的普通商戶,原本不至於牽扯進這些政治鬥爭中去,可是任家偏偏撞到了燕北王府的槍口上。
任益均想著任家長輩們的那些行事,若是這次他祖父和父親能夠平安回來,並且由這次的事件吸取到教訓,那麼以後任家或許還能繼續在燕州立足,否則的話任家這一艘船總有要翻的那一日。
任益均並不覺得自己的想法是杞人憂天,今日任家老太爺和任大老爺的牢獄之災就已經預示著任家在走下坡路了。
也就是在這一刻,任益均意識到了自己的百無一用,平日裡齊月桂罵他的話並沒有錯,如果他不是任家三爺,他還能做什麼?若是有一日他不再是任家三爺了,他又能做什麼?
這一個下午,任益均和齊月桂就這麼待在了花圃裡,和齊月桂的那一段對話之後,他又想了許多,而齊月桂則不知道什麼時候歪倒在了他上睡著了。
任益均察覺到之後,皺著眉頭很是嫌棄地看了一眼睡得口水直流的人,他有些猶豫地出手想要把給推到地上去,可是手到的肩膀的時候卻又鬼使神差地緩緩了子調整了一下自己的姿勢,好讓能睡得舒服一些。
任益均暗自給自己的行爲找藉口,等到他任三爺真到了的落魄了的那一日,能養活的估計也只有這個一頓只要求吃三碗米飯就滿足了的人了,所以以後還是稍微給點好臉看吧。
而這個時候的榮華院那邊,任五老爺和任三老爺終於把任大老爺任時中給接了回來。
只是衆人在看到任時中的時候都被嚇了一跳。
任時中爲任家嫡長子,是任老太爺欽定的任家上下承認的下一任家主,他平日裡是很注重自己的形象的,至每一次出現在人前的時候都是一穩重鮮的穿著,言行舉止也很有準當家人的氣勢。
Advertisement
可是今日任時中卻是被任時茂和任時敏兄弟兩人給扶回來的。
任時中出門的時候穿的那一青的杭綢直裰已經皺皺得不了樣子,儘管現在他上還披了一件任時茂馬車上的備著的深藍緞面披風。但是出來的襬還是看得出來有些破損。
他眼下有些青烏,看上去很疲憊,脣更是水到乾裂,頭上的髮髻雖然沒有歪,但是還能看得出來是之前不久才匆匆梳好的。
任老太太瞧見他的模樣震驚得了一聲“大郎”之後就說不出話來了,而任大老爺跪倒在任老太太面前的時候神也是有些激,大太太和大在一邊瞧著直抹眼淚。
任老太太也哭了一會兒,然後纔想起來任老太爺還在府的牢房裡沒有被放出來,可是看著任大老爺現在的模樣,任老太太實在是有些不敢開口問任老太爺如今的形。
倒是任時佳急忙開口問道:“大哥。你是在牢裡吃了苦頭了?父親呢?父親現在如何了?”
任大老爺臉疲憊地道:“那些獄卒倒是沒有手打人,只是這兩日一直在被人審問,一共才睡了兩個時辰不到,牢裡十分溼冷,我還好,父親他著了涼有些發熱。原本我是想讓父親出來,我繼續在牢裡待著的,可是好說歹說,府就是不肯放父親出來。說他纔是任家的現任家主,我又想著自己要不也先不要出來,我和父親兩人一起也算是有個照應,可是父親他不同意。今日我出來的時候。五弟他們已經求了穆大人給父親請了個大夫。”
任五老爺也嘆氣道:“只是衙門那邊怎麼也不允許我們進去探,說是這次案牽涉極大,怕父親與外面的人竄供,在事沒有水落石出之前需要先將父親收押。”
任老太太聽得越發提心吊膽。
任三老爺道:“大哥能回來也好。至這些場打點之事你比我和五弟都悉,父親那裡還要仰仗著你。”
任老太太也想起來了,忙道:“大郎你先回去歇著。等休息好了再想辦法將你父親救出來,花多錢也沒有關係,只要人能出來就好。”任老太爺不在,任老太太就像是了主心骨一樣,實在是不敢想象若是任老太爺真的回不來了該如何。
任大老爺確實是疲累得連站都站不住了,可是他知道現在無論是救任老太爺出獄,還是讓任家平安渡過這一次大劫難都需要他拿主意,這也是任老爺子一定要讓他回來的原因。
任大老爺讓大太太扶著他坐到了丫鬟搬上來的撲了墊的椅子上:“我再代幾句話就回去休息。”
任老太太立即道:“你說。是不是你父親代了你什麼事?”
任大老爺想了想,然後道:“從這兩日在獄中之時那些差審問我和父親的話來推測,任家今日的禍事或許真的與曾家有些牽連。”
任老太太與屋裡的衆人想起來今日任益均說的那些話,都是臉一變,任老太太的臉尤其好看。
任大老爺看了任三老爺一眼,嘆了一口氣:“三弟,或許當日真應該聽你一句,不與曾家結親的。”
站在外圍的任瑤華聞言看了任瑤期一眼,任瑤期低著頭站在邊上,臉上沒有什麼表。
任老太太道:“現在說這些有何用,何況我們與曾家還沒有正式換庚呢,也算不上是正經的兒親家,曾家那一頭拒了就是了。”任老太太說道這裡有些擔心的問任大老爺道,“如果我們不與曾家結親了會如何?府會放你父親回來嗎?”
任大老爺嘆了一口氣:“那就要看燕北王府的意思了。”
任老太太不安道:“這還不行?那還要怎麼做?”
任大老爺沉默了片刻才?道:“恐怕京都那邊的煤棧,任家需要先放棄了。”
任老太太立即皺眉:“這怎麼行?任家的煤棧好不容易纔有了今日的規模,你又不是不知道這些年來你父親花了多的心在上頭?”
將任家的煤棧開遍整個大周,這是任老太爺的心願,也是已故的那位太老爺任寶明的願。
任大老爺道:“父親說,如果迫不得已,任家只能丟卒保車了。”
任老太太不由得一臉頹然,任老太太這時候不由得在心裡怨恨起了東府和方家,原本任老太爺並沒有打算立即就應下曾家這門親的,可是偏偏在那個時候收到了東府二老太爺和方雅存的來信。
任大老爺說了這麼多,便有些支撐不住了。
任大太太忙道:“老爺,您還是先回去歇歇吧,既然父親已經這麼說了,我們照做就是。你不休息好,哪裡有經歷應付接下來的事?”
任老太太也道:“你去歇著吧,曾家那邊我安排人過去回絕,其餘的事等你休息好了再說。”
這次任大老爺沒有拒絕,讓任大太太陪著回了自己的院子。
任老太太現在也的疲累的很,人多吵得腦仁疼,衝著衆人擺了擺手道:“你們也都別守在這裡了,都出去吧。”
衆人便從榮華院退了出去。
任老太太知道與曾家劃清界限之事已經刻不容緩,立即讓人去隔壁的東府請任家二太太過來。
任家二太太出蘇家,蘇家與曾家又是姻親關係,所以這件事由蘇氏去當這個中間人最合適不過了。
二太太蘇氏也聽到消息說大老爺回來了,正想讓人去找二老爺一起過去西府看看。不過任二老爺還沒有找到人,任老太太的丫鬟就過來請的。
蘇氏稍稍收拾了一下就自己過去了。
任老太太躺在炕上將自己請蘇氏過來的來意說了,蘇氏聽完之後心下皺眉,問道:“大伯母,這些都是從衙門裡打聽回來的消息嗎?”
蘇氏問的是任家因爲曾家而被牽連的事,任老太太雖然沒有明說,但是話語裡似乎就是這麼個意思。
任老太太之所以會出這些,是因爲蘇氏雖然出蘇家,曾家也只不過是蘇家的一門姻親,而蘇氏卻是實打實的任家媳婦。
任老太太嘆道:“若非實在是迫不得已,我們也不想出爾反爾,可是你看看你大伯父現如今還在牢裡吃苦頭……”說著任老太太就哽咽了起來。
蘇氏輕言安的任老太太一番,知道這件事是還在牢裡的任老太爺的意思,蘇氏便沒有再多言了,任家當家做主的是誰清楚的很,任老太爺說要拒絕曾家的親事,那就說明沒有反轉的餘地了。
所以蘇氏從任老太太這裡離開的時候答應了任老太太會盡快回一趟蘇家,請蘇家出面回絕曾家的求親,有蘇家做中間人,雙方的臉面都會好看一些。
猜你喜歡
-
完結585 章
小公主又幫母妃爭寵了
穿書成了宮鬥劇本里的砲灰小公主,娘親是個痴傻美人,快被打入冷宮。無妨!她一身出神入化的醫術,還精通音律編曲,有的是法子幫她爭寵,助她晉升妃嬪。能嚇哭家中庶妹的李臨淮,第一次送小公主回宮,覺得自己長得太嚇人嚇壞了小公主。後來才知道看著人畜無害的小公主,擅長下毒挖坑玩蠱,還能迷惑人心。待嫁及笄之時,皇兄們個個忙著替她攢嫁妝,還揚言誰欺負了皇妹要打上門。大將軍李臨淮:“是小公主,她…覬覦臣的盛世美顏……”
105.9萬字8 170382 -
完結729 章
東風第一枝
葬身火場的七皇子殿下,驚現冷宮隔壁。殿下光風霽月清雋出塵,唯一美中不足,患有眼疾。趙茯苓同情病患(惦記銀子),每日爬墻給他送東西。從新鮮瓜果蔬菜,到絕世孤本兵器,最后把自己送到了對方懷里。趙茯苓:“……”皇嫂和臣弟?嘶,帶勁!-【春風所被,第一枝頭,她在他心頭早已綻放。】-(注:無血緣關系無血緣關系無血緣關系,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97.7萬字8 8970 -
完結467 章

全家帶著千億物資去逃荒
【全家穿越、空間萌寵、逃荒、種田】 蘇以安撓著雞窩頭看著面前冰山臉少年,心里一頓MMP。 全家集體穿越,本以為是個大反派制霸全村的勵志故事,這咋一不小心還成了團寵呢? 爹爹上山打獵下河摸魚,他就想老婆孩子熱炕頭,一不小心還成了人人敬仰的大儒呢。 娘親力大無窮種田小能手,就想手撕極品順便撕逼調劑生活,這咋還走上了致富帶頭人的道路呢? 成為七歲的小女娃,蘇以安覺得上輩子太拼這輩子就想躺贏,可這畫風突變成了女首富是鬧哪樣? 看著自家變成了四歲小娃的弟弟,蘇以安拍拍他的頭:弟啊,咱姐弟這輩子就安心做個富二代可好? 某萌娃一把推開她:走開,別耽誤我當神童! 蘇以安:這日子真是沒發過了! 母胎單身三十年,蘇以安磨牙,這輩子必須把那些虧欠我的愛情都補回來,嗯,先從一朵小白蓮做起:小哥哥,你看那山那水多美。 某冷面小哥哥:嗯乖了,待你長發及腰,我把這天下最美的少年郎給你搶來做夫君可好? 蘇以安:這小哥哥怕不是有毒吧!
87.4萬字8 47099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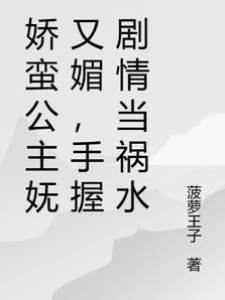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57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