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秦記》 第六章 餘情未了
五人你眼我眼,無言以對。
崑山乘機道:“小人早說必是有人中傷沈執事哩!”
年常有點老怒的道:“橫豎我們來了,總不能教我們白走一趟,沈執事一手吧!”
項龍笑道:“這個容易,沈某的劍法雖不堪五位大家之眼,但卻有手小玩意,看刀!”
猛喝聲中,左右手同時揚起,兩把早藏在袖口的匕首到手裡,隨手擲出,左右橫飛開去,準確無誤的分在東西兩邊的窗框,高低位置分毫不差。包括崑山等在,衆人無不駭然變。最難得是左右開弓,均是那麼快禮和準。
項龍知已鎮懾著這幾個初生之犢,躬施禮道:“沈某尚有要事辦理,不送了!”從容轉,離開廳堂。
項龍借肖月潭馬車的掩護,離開聽鬆院,往找“最可靠”的李園。
肖月潭讚道:“龍真懂齊人面子的心態,這麼一來,五個小子哪敢說出真話,只會揚言你向他們認錯,弄到誰都再沒興趣來找你。”
項龍搖頭嘆道:“仲孫龍既是面子的齊人,怎肯罷休。”
肖月潭道:“你這次找得李園出馬,仲孫龍怎都要忍這口氣的。”又低聲道:“知不知道剛纔菲和小屏兒在幾個心腹家將護送下由後門離開呢?”
項龍愕然道:“你怎知道?”
肖月潭答道:“雲娘見到嘛!是告訴我的。”
項龍皺眉道:“會否是去見韓竭?我若可跟蹤就好了。”
ωωω ▪ttκΛ n ▪c o
肖月潭道:“你在這裡人地生疏,不給人發現纔怪。”
此時蹄聲驟響,數騎從後趕來。
項龍探頭出去,原來是金老大金就和幾名手下策馬追來,道:“沈執事留步。”
Advertisement
肖月潭吩咐手停車。
金老大來到車窗旁,道:“沈執事有沒有空說幾句話?”
項龍哪能說“不”,點頭答應,對肖月潭道:“老哥記得給我弄稷下宮的圖則,我會自行到李園。”
步下馬車,金老大甩蹬下馬,領他到附近一間酒館,找個幽靜的角落,坐下道:“沈兄!你這次很麻煩呢。”
項龍苦笑道:“我的麻煩多不勝數,何礙再多一件。”
金老大豎起拇指讚道:“沈兄果是英雄好漢,我金老大沒錯你這朋友。”
項龍心中一熱道:“金老大才真夠朋友,究竟是什麼事?”
金老大道:“昨晚田單爲呂不韋舉行洗塵宴,我和素芳都有參加,我恰好與仲孫龍的一個手下同席,閒聊中他問我是否認識你,我當然不會我們間的真正關係。”
項龍笑道:“不是懸賞要取我項上的人頭吧!”
金老大啞然失笑道:“沈兄真看得開,但尚未嚴重至這個地步,你聽過‘稷下劍會’這件事嗎?”
項龍搖頭表示未聽過。
金老大道:“每月初一,稷下學宮舉行騎大會,讓後起者有顯手的機會,今天是二十七,三天後就是下月的劍會,照例他們會邀請一些賓客參加。嘿!那只是客氣的說法,其實是找人來比試。”
項龍道:“若他們要我參加?我大可託病推辭,總不能將我押去吧!”
金老大嘆道:“邀請信是通過齊王發出來的,沈兄夠膽不給齊王面子嗎?聽說仲孫龍的兒子仲孫玄華對沈兄震怒非常,決定親下場教訓你。他雖不敢殺人,用的只是木劍,但憑他的劍力,要打斷沈兄的一條絕非難事。”
項龍立時眉頭大皺,他怕的不是打遍臨淄無敵手的仲孫玄華,而是怕到時田單、呂不韋等亦爲座上客,自己不暴份就是奇蹟。
金老大低聲道:“沈兄不若夜離開臨淄,小姐必不會怪你。”
項龍大爲意,這確是最妙的辦法,但董淑貞們怎辦呢?如此一走了之,日後會一條梗心之刺,休想心中安樂。
金老大再慫恿道:“仲孫龍勢力在此如日中天,有份地位的公卿大臣也畏之如虎,沈兄怎都鬥他不過的。”
項龍嘆道:“多謝老大的提點,這事我或有應付之法。”
言罷拍了拍金老大肩頭,往找李園去了。
項龍來到李園客居的聽竹別院,與聽鬆別院只隔了兩個街口。由此可見菲的地位竟可比得上貴爲相國的李園。
他在門報上沈良之名,那人肅然起敬道:“原來是沈大爺,相爺早有吩咐,不過相爺剛出門,沈爺有沒有口訊留下呢?”
項龍很想說著他來找我吧!但想想這似非自己目下的份該說的話,遂道:“煩先生你告知相國我來過便。”
此時中門大開,一輛華麗馬車在前後十多名騎士簇擁下馳出大門,但因車窗被垂簾阻隔,看不到裡面坐的是什麼人。馬車遠去後,項龍下詢問門的衝,踏上歸途。這日天朗氣清,寒冷得來卻很舒服,項龍雖在人車爭道的熱鬧大街信步而行,心底卻到孤單寂寞。在逃亡途中,他所有神時間盡用在如何躲避敵人的思量上,反是到了臨淄,遇上這麼多新知舊友,他竟會有寂寞的覺。他溜目四顧,看著齊都的盛景,深切會到“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意境滋味。除了肖月潭外,他再無可以信任的人。最痛苦是他本無可用之兵,否則只要派人切監視韓闖,可知他會不會出賣自己。例如假設他不斷去見郭開,便可知道他對自己不忠實。三晉關係一向切,郭開的老闆娘更是韓闖的族姊韓晶,若要對付項龍,兩人必會聯合在一起。在那種況下,龍君怎敢反對。他們唯一的阻礙可能是李園,但他肯否冒開罪三晉來維護自己,恐怕仍是未知之數。
想得頭都大時,心中忽生警兆,一騎迎面而至,馬上騎士俯下來道:“這位兄臺怎麼稱呼?”
項龍愕然向對方,肯定自己從未見過此人,戒心大起道:“有什麼事呢?”
那人非常客氣,微笑道:“敝主人是清秀夫人,小人奉之命,前來請先生往會,因夫人沒有把先生的高姓大名告訴小人,不得不冒昧相詢。”
項龍恍然剛纔離開聽竹別院的是清秀夫人的座駕,暗忖若非李園曾告訴自己來了臨淄的事,就是自己的裝扮糟。於是報上沈良之名,隨騎士往見曾過婚姻創傷的。
項龍登上清秀夫人恭候道旁的馬車,這個把自己麗的玉容藏在重紗之的以一貫冰冷的聲音道:“上將軍你好!請坐到清秀旁來。”
項龍見不著的真面目,心中頗爲失,更知坐到旁的邀請,不是意要親近一點,只是方便說話,忙收攝心神,坐了下來。一兒家的芳香沁心脾,馬車開出,在繁榮的古都大道上緩緩前進。忽然間,他再不到寂寞,當因馬車搖晃使兩人的肩頭不時在一起,不由想起當年在大梁,與紀嫣然共乘一輿的人景。
清秀夫人淡淡道:“上將軍的裝扮很奧妙,若非清秀從李相爺得知上將軍來了臨淄,恐怕認不出來。”
項龍心下稍安,苦笑道:“希李相爺不會逢人便說我來了齊國吧。”
清秀夫人不悅道:“李相爺怎會是如此不知輕重的人,只因清秀乃琴太傅的至好友,所以不瞞人家吧!”
項龍衝口而出道:“我尚以爲夫人與李相爺的關係不太好哩!”
清秀夫人隔簾往窗外,默然片晌,聲道:“又下雪了,只不知牛山現在是何景,上將軍有興趣陪清秀到那一遊嗎?”
項龍想不到竟突起遊興,還邀自己相陪,訝道:“牛山?”心中涌起寵若驚的滋味。
天暗沉下來,朵朵雪花,飄無力的降下人間。
清秀夫人若有所思的凝窗外,輕輕道:“牛山春雨乃臨淄八景之首,不過近年斧斤砍伐過度,致有牛山濯濯之嘆,幸好經過一番植樹造林,據說又回覆了佳木蔥鬱、綠茵遍地的景,現在是隆冬,當然看不到這況哩!”
項龍這才知道“牛山濯濯”的出,點頭道:“夫人既有此雅興,項某敢不奉陪。”
清秀夫人發出開赴牛山的指示,以充滿緬懷的語氣道:“清秀時曾隨先父到過牛山,時值春三月,淄水湍湍,泉水從山隙間流瀉而出,潺流跌巖,水氣蒸騰,如雨似霧,之宛若霏霏煙雨,到今天仍然印象深刻。”
項龍聽言談高雅,婉轉人,不由一陣迷醉。暗忖的面紗等若牛山的煙雨,使深朦朧的迷人之。
清秀夫人續道:“清秀很怕重遊一些曾留下好印像的勝地景,因爲深怕與心中所記憶的不符。”
項龍訝道:“這次爲何重遊舊地?”
清秀夫人緩緩搖頭道:“我自己都不明白,或者是因有名震天下的項龍相陪吧!”
項龍道:“原來項某在夫人心中竟有點份量。”
清秀夫人朝他來,低聲道:“剛纔妾見上將軍隻影形單的站在府門,比對起上將軍在咸的前呼後擁,竟生出滄海桑田、事過境遷的。最後忍不住停下車來與上將軍一見,上將軍會因此笑人家嗎?”
項龍愕然道:“原來夫人竟對項某生出同之意。”
清秀夫人搖頭道:“不是同,而是憐惜,上將軍可知自己的境非常危險?”
馬車此時穿過城門,朝南馳去。
項龍苦笑道:“夫人此話必有依據,龍洗耳恭聽。”
清秀夫人淡淡道:“上將軍的灑和不在乎己安危的態度,乃清秀生平罕遇,就算不看在琴大姐臉上,清秀也要助你。”
項龍低聲音問道:“你這些侍衛靠得住嗎?”
清秀夫人道:“上將軍放心,他們是隨侍妾十多年的家將,況且他們本不會想到你是項龍哩!”湊近許,在他耳旁吐氣如蘭,臉紗一一的道:“昨天李相爺宮找我的妹子寧夫人,神困苦,在妾私下追問,說出你的事來。”
項龍一震道:“那就糟了,他還有什麼話說?”
清秀夫人道:“他哪會真的向妾傾吐,但妾可肯定他確把上將軍視爲肝膽之。問題是他爲楚相,很多時都得把個人得失惡拋在一旁,以國事大局爲重,否則何須苦惱?”
似乎有點不堪與他距離太近般,別過俏臉遙窗外,嘆了一口氣。項龍陪嘆一口氣,一時找不到說話,暗想李園初見他時真流的況過後,自會開始考慮到實際的問題,又或因韓闖的力而煩惱起來。除了肖月潭外,自己還可信誰呢?
清秀夫人一字一字地緩緩道:“若不是這等天氣,妾會趁現在把車開往城外,勸上將軍不如一走了之,乾乾淨淨。”
項龍想起到大梁時那場大病,兼之人生路不,猶有餘悸的嘆道:“我尚有些責任未完,不過縱有人要對付我,我亦不會束手就擒。唉!在夫人警告龍之前,我已想到有這種況出現的。”
清秀夫人點頭道:“事實早證明項龍是應付危險的能者,況且真正的況如何,本沒有人知道,或者妾只是白擔心吧!”
忽又欣然指著窗外遠方一山麓道:“看!那就是輔助桓公稱霸的名相管仲埋骨之。”
項龍自然挨過去,循目往外去,山野銀霜遍地,樹梢披掛雪花,素淨純得使人心靜神和。雪白的世界更似和天空連接起來,再無分彼此。不遠屹立一座大山,淄河、水兩河纏繞東西,岸旁數百年樹齡的松樹、樺樹直指空際,景緻不勝收。大山南連另一列層巖疊嶂的山巒,景使人歎爲觀止。
清秀夫人垂下頭來,輕輕道:“上將軍,你……”
項龍發覺自己口一邊肩背,尷尬地挪開一點,顧左右而言他道:“沒有舟楫渡河,恐怕不能登山遠眺!”
清秀夫人淡淡道:“我們得回去哩!若妾想找上將軍,該怎辦呢?”
項龍見語氣變得冷淡,激起傲氣,低聲道:“夫人最好不要牽涉在事件,生死有命,若老天爺不眷顧我項龍,我又有什麼法子,人算哪及天算。”
清秀夫人輕道:“人算不及天算,上將軍真看得開,妾不再多事了!”
回到聽鬆別院,項龍心中仍填滿清秀夫人的倩影,揮之不去。他不明白爲何會對自己這麼有影響,或者是因爲那種對世冷漠不關心的態度,又或因的驕傲矜持而使自己心。幸好這時的他充滿危機,趁著有空閒,仔細研究聽鬆院的形勢,以備有事發生時可迅速逃命,又把鉤索等東西取出來,系在腰間,慌虛的心落實了點兒。理了一些團中的日常事務,又探問臥榻養傷的張泉,返回房間小息,快睡著時,董淑貞來了。
項龍擁被坐起來,董淑貞坐到榻沿,吃了一驚道:“沈執事不是冷病了吧!”
項龍笑道:“老虎我都可打死兩頭,怎會有事呢?二小姐顧有何指教?”
董淑貞驚魂甫定的拍拍道:“嚇死人哩!”又橫他一眼道:“定要有什麼事纔可來找你嗎?來!讓我爲你推拿,保證你睡得好。”
項龍翻轉伏在榻上,欣然道:“讓我試試二小姐的高明手法。”
董淑貞下外,踢掉綿鞋,坐到他背上,手爲他肩,低聲道:“找到是誰把曲譜龍轉了。”
項龍想也不想的道:“小寧。”
小寧是祝秀真的侍婢。
董淑貞大樂道:“沈執事這回錯了,的人是張泉自己,小寧曾見過他在附近鬼鬼祟祟的,房後又見有些東西擺了,當時不以爲意,給秀真問起才說出來。”
項龍搖頭道:“我不信,那只是小寧諉過於人吧!噢!這得真舒服,我要睡了!”
董淑貞急道:“不要睡,你答應過人家的事有什麼下文?”
項龍知問的是菲肯否讓有獨擔一曲的事,心中苦,坦白道:“尚未有機會和說,明天告訴你好嗎?”
董淑貞伏下來,把他摟個結實,咬他耳朵道:“聽說韓闖和你是老朋友,你會不會幫他來害人家呢?”
項龍對韓闖再沒有先前的把握,苦笑道:“和他只是有點吧!那談得上是老朋友,二小姐放心好了,只要我有一口氣在,都會爲二小姐盡力。”
董淑貞一道:“沈良你爲何語調悲觀,以前有竹的定力到哪裡去了?”
項龍一個大翻,把在下,貪婪地吻的香脣,直至咿唔,放開道:“世事每每出人意表,誰可真的有竹,只是盡力而爲,所以我需要你們真心信任。”
董淑貞眼如的瞧著他,秀目出灼熱的神,啞聲道:“原來你並不只是歡喜男人的。”
項龍苦笑道:“誰說我歡喜男人呢?”
心中同時涌起慾火。自知道有可能被韓闖等出賣後,他的緒陷進難以自拔的低裡,很想找尋一些刺激,好轉移自己的神心事,而董淑貞正是送上門來的刺激。或者只有人的,可使他忘掉所有不如意的事。
董淑貞探手勾著他的脖子聲道:“空口白話有什麼用?用行來證明你是喜歡人吧!”
項龍的意志崩潰下來,低頭要再嘗地脣上的胭脂,有人在門外道:“沈爺,解子元大人來了,在大廳等你。”
項龍生出不對勁的覺,現在離黃昏尚有個多時辰,解子元爲何這麼早到?
猜你喜歡
-
完結649 章
少帥每天都在吃醋
一部少帥夫人成長史,看外科女醫生如何攻略冷麪少帥。 一個驕縱跋扈缺根筋的大小姐被害死了,21世紀外科女神醫陸早早穿越而來,她醫術高超,心靈剔透,麵對公婆不親,丈夫不愛,還有各路虎視耽耽的姨太太,僅憑一把小小手術刀在督軍府裡踩綠茶,踹心機,人生開掛所向披靡。 視她如蚊蠅的少帥丈夫夜夜爬她的床,翻她的窗,要和她做一對天長地久的美鴛鴦。 她狠狠一腳踹出去:“少帥不是要休妻嗎?” 他抱著她咬耳朵:“我確實要修理修理你。” 結果她被修理的零件重組,幾天下不了床。 玩世不恭的少主甘願做她小弟,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死皮賴臉抱著她的大腿求親親。 威鎮一方的大軍閥非她不娶,除她不要,囂張的在她家門口架起二十門大炮。 我勒個去,ABCDEFG,男人個個是極品,人生最怕的就是做選擇題。
141.5萬字8 24091 -
完結1129 章

承包大明
一名交易分析員因為一場事故,穿越到大明朝萬曆年間,成為一位大牙商的上門女婿。他原以為自己也能像穿越小說中那些主角,在古代混得風生水起,富可敵國,妻妾成群。直到他遇見了萬曆皇帝.....。「陛下,關於草民的傭金.....?」「你無須著急,朕這就戶部發給你。」「我擦!陛下,你先前讓我幫你掏空國庫,充盈內府,如今國庫隻有老鼠屎!」「這倒也是,那就這樣吧,朕將國庫承包於你。」「陛下,草民有句話不知當不當講?」「你但說無妨。」「MMP!」
334.3萬字8 17006 -
完結448 章

七零:奪回氣運,首富嬌妻躺贏了
【蘇爽甜+空間】前世林千雪氣運被奪,魂穿三年家破人亡。再睜眼,回到一切被奪前,林千雪拒當炮灰,重拳出擊奪回一切。退伍糙漢柳宗鎮八字重、火氣旺、氣血足,火速將小嬌妻叼回家。媳婦遭人覬覦,糙漢護妻奮斗成大佬,林千雪含淚血賺男人一枚。爺爺、親爹諸多靠山接踵而至,寵溺無邊,極品祭天,小可憐改拿團寵劇本,人家買房她賣房!發家致富成首富!逆襲大魔王!她就是豪門!柳大佬:媳婦勇敢飛,糙漢永相隨。柳崽崽:媽媽小乖寶替你撐腰腰!瑪卡巴卡!柳婆婆:兒媳婦太嬌弱→又被欺負了→小丑竟是我自己emo長輩首長們:我看誰敢動我...
84.1萬字8.18 82471 -
完結1631 章

王妃每天想和離
一穿越就遭遇重重殺機,差點被謀殺在新婚之夜,葉歡顏發誓,她絕不像原主一樣隱忍受辱,所有欺辱她算計她的,全都下地獄吧!就這樣,葉歡顏在虐渣渣睡美男掌大權的路上越奔越勇。后來,葉歡顏又有一個偉大的夢想,守寡!某日,一向不信佛的葉姑娘秉著心誠則靈…
295.3萬字8 124662 -
完結3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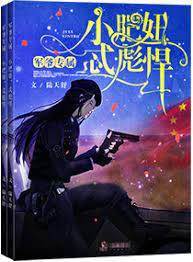
軍爺專屬:小肥妞,忒彪悍!
身為雇傭兵之王的蘇野重生了,變成一坨苦逼的大胖子!重生的第一天,被逼和某軍官大叔親熱……呃,親近!重生的第二天,被逼當眾出丑扒大叔軍褲衩,示‘愛’!重生的第三天,被逼用肥肉嘴堵軍大叔的嘴……嗶——摔!蘇野不干了!肥肉瘋長!做慣了自由自在的傭兵王,突然有一天讓她做個端端正正的軍人,蘇野想再死一死!因為一場死亡交易,蘇野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色誘……不,親近神秘部隊的軍官大叔。他是豪門世家的頂尖人物,權勢貴重,性情陰戾……一般人不敢和他靠近。那個叫蘇野的小肥妞不僅靠近了,還摸了,親了,脫了,壓了……呃...
96.9萬字8 1461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