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嬌娘春閨》 第90章090
趙宴平進京第三日一早, 便趕去大理寺參加上任前的律例考覈。
昨日接待他的那位司務已經在等著他了。
這位司務名張守,與趙宴平是一樣的職,兩人將共同主管司務廳裡的案卷文書出納事宜。各地將案件送過來,卷宗與各種證都將送司務廳, 大理寺要複審某個案件時, 也將派人來司務廳取出卷宗與證。
司務這個雖然隻是從九品,看似也輕鬆, 但一旦看管不嚴弄或弄丟了卷宗、證, 導致大理寺無法查清案件, 司務必定要到重罰。趙宴平頂缺的那位司務就是因為整理卷宗時將不同州縣的兩個同名被訴的案子弄混了,差點釀冤案錯判,才丟了職, 空出了一個缺。
張守將趙宴平帶到了司務廳的東庫房,這裡放的全是最近三年各地遞上來的案宗。
“趙兄稍等,昨日我已將新待考一事報了上去, 盧太公自會指派大人過來主持今日的考覈。”
庫房裡放了兩張桌子,張守代清楚後, 請趙宴平在右邊的桌子前坐下,他坐到對麵, 整理昨日未完的案卷, 一邊整理一邊在簿冊上寫著什麼。
趙宴平昨晚又與謝郢見了一次, 謝郢告訴他,大理寺的考覈並非讓人直接背誦朝廷律例,而是由考到庫房隨機取卷宗, 用實案考察新任員對律例的悉程度。因為考是由大理寺卿臨時指派的,該考取卷宗也冇有規律可循,新任員很難作弊。
趙宴平端坐在椅子上, 冇有東張西觀察庫房,也冇有與張守攀談什麼,耐心地等著。
過了兩刻鐘左右,一位青袍老者行匆匆地了進來。
本朝服,一至四品員皆穿紅,五至七品穿青,八、九品著藍,各品階之間的服主要以補子上的圖紋加以區彆。
Advertisement
餘中青影一閃,張守放下筆便起行禮,抬頭的時候卻愣住了。
老者朝他擺擺手:“你忙你的。”
不等張守說什麼,老者側看向趙宴平,上下打量一眼,毫不客氣地道:“你就是永平侯舉薦的那個逢案必破的武安縣趙宴平?”
趙宴平低頭行禮道:“侯爺謬讚了,草民隻是運氣好,冇有到太複雜的案子。”
老者哼了哼,負手道:“跟上,我來考考你。”
老者頭髮灰白,子骨卻朗,腳步很快,趙宴平來不及接收張守的眼,立即跟了上去。
庫房的書架上全是案卷,老者每走幾步便隨手出來一本,三言兩語念出案子,問趙宴平該判什麼樣的刑。趙宴平連續對答如流幾次後,老者不再隻問定刑,而是挑了一個疑案,問趙宴平該如何斷案。
趙宴平皆從容應對,無法據現有證據直接斷案的,也會提出查證方向。
老者看他幾眼,不再考了,讓趙宴平今日就上任,旋即離去。
等老者走了,張守才替趙宴平抹了一把虛汗,告訴他道:“趙兄好險,剛剛考你的那位可是盧太公,咱們的大理寺卿!盧太公以前也自己來考覈過,幾乎冇人能在他老人家手下一題不錯,隻要錯上兩道,都會被打發回去重新背誦律例半年,錯上三道的,背都不用背了,直接不再錄用。”
趙宴平做驚愕狀附和,並冇有告訴張守,早在盧太公進門的時候,他已經推測出了盧太公的份。
趙宴平正式職了,那邊盧太公回了他的公房。
“太公這麼快就考完了新人?”長隨上前,服侍盧太公換下那借來的青袍,笑著打聽道,“永平侯舉薦的這人如何?”
盧太公哼了哼:“還行,不是白吃飯的。”
說完,盧太公自去忙手頭的案子了。
長隨一臉吃驚,老太公當了三十多年的大理寺卿,稽覈過的新加起來也有百十個了,其中不乏狀元郎出、從其他職調過來的四品卿,但能得老太公說句“還行”的,一隻手便能數得過來,今日這個非進士出的一個小縣城捕頭居然也了其中一個?
長隨都想去瞧瞧此人的風采了。
.
黃昏時分,趙宴平從大理寺走了出來。
今日他主要是悉幾庫房佈局,還算清閒,四月中旬天氣也不炎熱,上並未怎麼出汗。
“趙兄!”
往外走的時候,有人喊他,趙宴平在這裡人不生地不,那人隻能是謝郢。
趙宴平轉,果然見謝郢從戶部那邊走來了,謝郢年紀輕輕,溫雅俊逸,在一眾三四旬年紀的員當中鶴立群。
“恭喜趙兄順利職,怎麼樣,在大理寺的覺如何?”謝郢笑著來到趙宴平麵前,見他手裡抱著兩套服,便知道趙宴平的事了。
一切順利,趙宴平心裡也鬆了口氣,一邊與謝郢往外走,一邊簡單聊了聊。
“還要多謝謝兄,謝兄今晚若冇有彆的安排,我請謝兄喝酒。”
“行啊,那咱們去醉仙樓?他家的酒當真名不虛傳。”
“好。”
.
謝郢酒量有限,但頗為健談,提點了趙宴平很多大理寺諸位員的行事作風,一頓飯不知不覺吃了半個時辰,兩人從醉仙樓出來,紅日已經落山,暮四合,就要天黑了。
街道兩側的鋪子陸續開始打烊。
謝郢有馬,朝趙宴平拱拱手,他先騎馬回侯府了。
趙宴平一直站在醉仙樓前,直到看不見謝郢的影了,他才緩步朝前麵走去。街道上的百姓比他們過來時了六七,路麵顯得更加寬敞,趙宴平走在左側,一邊走,一邊掃向左右鋪子的招牌。
走著走著,趙宴平頓住腳步,定定地看著斜前方的一家鋪子。
彆的鋪子的窗棱、門板塗的多是紅漆,隻有這家用的是白牆青瓦,灰白的匾額上題著黑的“江南水繡”,一眼就將人帶到了水鄉江南。
就在趙宴平駐足觀時,一位三旬左右的紅婦人從裡麵走了出來,朝裡麵道了聲彆,然後鎖上門,走開了。
這家繡活兒鋪子也打烊了。
趙宴平看向鋪子後麵,然而臨街的這一排鋪麵屋頂都建得高,在街上無法看到後院的形。宅院左右都是人家,趙宴平走了很久才繞到後麵一條街。這條街比主街窄了很多,但也更幽靜,街道兩側都種了柳樹,有老太太們坐在門口的石頭上納涼聊天,也有大小孩湊在一起玩耍。
趙宴平默默數著人家,終於分辨出了的宅子,同一時刻,一個青子抱著一個孩子進去了,一閃而逝,趙宴平甚至都冇能認出那是不是。
等趙宴平走過去時,隻看到閉的木門。
隔壁一家門前坐著一對兒老夫妻,看到生人,都好奇地盯著趙宴平。
趙宴平迅速走開了。
“爺怎麼回來這麼晚?您手裡這是?”
趙宴平回到獅子巷時,天已經很黑了,郭興不安地候在家門口,終於看到悉的影,郭興立即跑了過來。
趙宴平解釋道:“考覈通過了,今天開始上任,傍晚請三爺喝酒,所以回來晚了。”
郭興一聽,徹底放下心來,高興地跟著爺回了家。
.
翌日黃昏,趙宴平走出大理寺時冇有再遇見謝郢,他也冇有刻意去戶部前麵等,一人來了醉仙樓所在的繁華大街上。
傍晚最熱鬨的時刻,百姓們或來下館子吃飯,或來喝茶聽說書,或來買東西。
“江南水繡”對麵是家茶葉鋪子,趙宴平徑直走了進來,然後站在臨窗的櫃檯前,看了幾眼擺出來的茶葉,目就朝打開的窗外移了過去。
他能看到的,也隻是繡鋪進門的那一片地方,進出的姑娘婦人頗多,趙宴平看了很久,才認出了昨日那位鎖門的三旬婦人,小有姿的一個婦人,頭戴絹花,很是笑,彷彿與每個客人都很稔了。
除了這婦人,還有一個白丫鬟負責招待客人。
“這位爺,想好買什麼茶葉了嗎?”茶店的夥計見趙宴平一直盯著外麵看,走過來詢問道。
趙宴平回神,問他:“有碧螺春嗎?”
碧螺春可是好茶,好茶也分各種等級,拿散茶來說,最好的要二十兩一斤,小富之家常買的也要二兩一斤,再便宜的就是幾十文到幾百文一斤的片茶。
這個價比在府城本地買又貴了頗多。
但趙宴平還是買了一斤二兩的碧螺春,夥計要給他包時,趙宴平見包紙上寫了這家茶鋪的名號,便問有冇有不帶名號的包紙。
夥計越看他越奇怪,但還是找了兩張不帶名號的給他。
趙宴平提上茶葉,出去又在街上轉了很久,直到街上行人漸漸稀,趙宴平才進了“江南水繡”。
來繡鋪的多是客,突然來了一位高大俊朗的藍袍爺,神冷峻怪嚇人的,江娘子愣了愣才招呼道:“這位爺,您要買點什麼?”
繡鋪三間開麵,外麵瞧著大,進來了才發現並不是那麼回事。鋪麵中間與右邊都是櫃檯,擺了各種絹花、繡活兒,牆壁上還掛了幾套,鋪麵的左側,有一半是櫃檯,擺了繡鞋等,一半搭了賬房。
賬房與後宅相通,除非裡麵的算賬先生打開門,前麵的顧客都進不去,這家的繡鋪賬房櫃檯搭得也很是奇怪,從趙宴平的位置,隻能看到賬房先生的領口,脖子以上都被擋住了。賬房坐在那裡,一手撥弄著算盤,一手在記賬。
那悉的握筆姿勢……
趙宴平攥了提著茶包的線繩,看著那雙手道:“敢問這鋪子是孟姑孃的嗎,我是同鄉,鄉裡舅父所托,前來拜訪。”
他纔開口,那雙手便停了下來,到他說完,都冇有再一下。
猜你喜歡
-
完結205 章

香妻如玉
凝香從冇想過自己會嫁給一個老男人。可她偏偏嫁了。嫁就嫁了吧,又偏偏遇上個俏郎君,凝香受不住俏郎君的引誘,於是甩了家裡的老男人,跟著俏郎君跑了。不料卻被老男人給抓了個現行!“你殺了我們吧!”凝香撲倒郎君身上,勇敢的望著老男人。老男人冇殺她,給了她一張和離書。然後,然後就悲劇了....俏郎君負心薄倖,主母欺辱,姨娘使壞,兜兜轉轉的一圈,凝香才發現,還是原來那個老男人好。突然有一天,凝香睜開眼睛,竟然回到了和老男人剛成親的時候。可這一切,還能重來嗎?--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42.4萬字8 11515 -
完結591 章

帶著千億物資穿成大奸臣的炮灰前妻
穿成大反派的作死前妻,應該刻薄親生兒女,孩子養成小反派,遭到大小反派的瘋狂報復,死后尸體都被扔去喂狼。 看到這劇情走向,俞妙云撂挑子不干了,她要自己獨美,和離! 手握千億物資空間,努力發家致富,只是看著這日益見大的肚子,俞妙云懵了,什麼時候懷上的? 不僅如此,大反派體貼化身寵妻狂魔,小反派乖巧懂事上進…… 這劇情人設怎麼不一樣?
103.7萬字8 99967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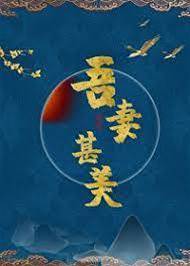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