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我千秋》 第50章 伍拾
——炎。你既說要疼我,那便要一直疼下去。倘若有一日你不再疼我了,我會要了你的命。你信麼?
——若真有那一日,我讓你來殺。我卓炎既然你,便此生不悔,亦絕不變心。
——炎。你還疼我麼?
……
戚炳靖那漠然的一笑,給他的目中添一抹。
那抹,使得他下的目愈發僵冷,微狠戾,同他如覆寒霜的面龐一道令人生畏。
仿若只要出口否認,下一刻他便會真的要了的命一般。
“你問我?”
卓炎逆著他的目,一面進前一步,一面開口。
這一步的氣勢過于咄咄人,竟令他不得不后退了一小步——
他戚炳靖,何曾后退過半步,眼下竟被卓炎的一個反問得不自地向后退卻,連帶目中的與狠戾都于一瞬間消弭無蹤。
卓炎抬頭視他:“你手中握著我的心。我還疼不疼你,你覺不出?!”
的聲音仍然是抖的。的語氣中仍然飽蘊著失與憤怒。但這一句中的失與憤怒,卻不同于此前的失與憤怒。
有一滴淚自眼中被震落。
寒風驟停。暴雪驟止。
他面龐上的寒霜被這一滴淚盡數融化。仍然站在他面前。的容清晰可見。的一顆心,仍然被他握在掌中。
他輕那顆心。
它不再熾熱,不再滾燙,但它仍在鮮活地跳著,仍在輕地挲著他掌心的皮。
戚炳靖抬起僵麻的胳膊,想要為一淚:“炎。我不該瞞你。但我不得不瞞你。”
他的聲音又低又啞,飽含著別無選擇的深深無奈。
卓炎是什麼樣的人,所信所仰的是什麼,從最初,到如今,他沒有一刻不清楚。
Advertisement
當初廢帝另立,所立者何人?是沈毓章、英嘉央之子。
沈、英二人為政治國之主張是什麼?是法大平之太祖、世宗,恢復前烈,力致太平。
新帝法之世宗,是什麼樣的人?一句“若吾可濟民,吾不所惜也”傳千古,為帝王,為了家國百姓之安寧而不惜一己之命。若無這樣的王道,大平之社稷何以至今猶在。
將大好韶華盡獻國之北疆。
在風雪之中的豫州城頭堅毅不屈、悍不畏死。
的這一骨是靠什麼在支撐,所有的堅忍、狠毅、手上沾過的,統統是為了什麼?
——安國,安民,挽大平江山于不破。
他太懂。
正是因為太懂,他才不忍、不舍,始終不愿讓知道,他與從來都不是同一類人。
卓炎卻一把格開了他過來的手。
自己輕輕抹去臉上淚珠。然后看著他,道:“炳靖。我此前從未過什麼人。我于此事毫無經驗。當初上你,是我太輕率了。”
太輕率了。
何以能因他對的這一份深深的懂得與相助,就想當然地以為他與是同一類人,他所信所仰的亦同一樣?!
他是什麼人。
他生于晉室,長于晉室,自耳濡目染皆晉室中事。
晉室是什麼樣的?當年的戚氏,靠兵武起家,憑軍功得封大平之外姓親王,不過短短四十年后,子孫即恃兵強馬壯而自稱帝,挾洶洶野心縱兵南下,鐵蹄踐踏大平疆土,二國戰火百年難止。
戚氏之晉室,何時奉忠盡義過,何時以民為先過。
他弒父,弒兄,殺朝臣,連累數萬將兵命,為的豈是安國與安民?為的豈是固戚氏之江山?
他。
因以明之姿救他于死窒黑暗之中。
他助。
因足以令他仰視,亦足以令他垂憫。
他以這與助,贏獲了的信任,使在將他徹底看個清楚明白之前,就輕率地將自己的一顆心到了他的手中。
何其諷刺。何其殘忍。
卓炎抹去淚后,又道:“我把心給了你。可你從未把心給過我。我何曾真的窺見過你的心?我何曾真的過你的心?我若不識你的心,又要如何繼續你!”
此刻,的聲音在失與憤怒之外,亦夾雜著難以消解的委屈與傷心。
的這些話,猶如鋪天蓋地的集箭陣一般,將他網殺得無完。
戚炳靖的口一陣一陣地發痛。他一把抓起的手,按到自己發痛的口,道:“炎。我的心,你來拿。只要你肯要。只要你不嫌棄。”
他還有話未說完,但他不敢說出口。
卓炎不答他的話。
沉默了一下,使勁想將手出。
但他卻死死不肯放開,不論痛與否,始終將的手地按在口。
他的心跳得極快,一下接一下地砸在的手心里。
漸漸地,不再試圖掙,因整個人都被他如此狂烈的心跳砸得抖不已,本無力再一下。
……
夜里睡覺時,戚炳靖如往常一般,將卓炎圈懷中。
沒有反抗,但僵不已。
他低下頭,想要親一下,可卻被一下子錯開。頓時,他只覺心如被鈍刃狠刮數下,盡力抑了抑,才沒出聲。
沉默半晌后,他將放開,撐起來,打算離開。
可他的手卻被勾住了。
不愿與他親昵,卻亦不愿與他分開。
何其矛盾。何其掙扎。
戚炳靖沉著眉眼重新躺下。他沒再將抱進懷里,就只輕輕地將的手握住,道了句:“睡罷。”
于黑暗中,他自己毫無睡意,一直睜著眼到三更天。
估著已睡得深了,他試著低低喚了聲:“炎?”
未聞答,他便小心地將的手松開,自己起披,借著月步出殿外。
……
月華正盛,雪夜清寒。于凝積薄霜的殿廊之間,戚炳靖不出意外地看見了文乙的影。
他不疾不徐地踱過去,了聲:“文叔。”
文乙的兩鬢掛有白霜,顯然已在此等了他許久。待聞他聲,文乙側首顧他,抱袖垂首:“王爺。”
月打在戚炳靖的側臉上,映出冷冷肅。他抬目遠眺,道:“文叔知道我今夜睡不好,故而在此等著我。”
文乙道:“該說的話,早晚都得說。王爺的不忍與不舍,又何以能夠長久地留住的心?王爺是什麼樣的人,本該更早些知道才是。”
戚炳靖沒有說話。
文乙又道:“當年王爺的母妃是因何郁郁而亡的,王爺難道忘了?王爺該引以為鑒。”
他這話說得堪算冒犯。
戚炳靖的臉驟變,角亦了一下。但他終未怒,只將文乙看了兩眼,道:“文叔替我在面前揭開舊事,此間用意,我自明曉,我不怪你。但文叔告訴的事,太多了。”
太多了。這三字被他低沉地念出齒間,是不滿,亦是斥責。
文乙卻苦笑一聲,道:“王爺有所不知。王爺舊事,小臣只對說了一半。另一半,是自己推斷出的。”
“哦?”
“王爺上的人,論才智,論機敏,確是小臣此前從未見過的。”
……
“倘若王爺是這樣一個男人,殿下仍然會像此刻這般心他麼?”
文乙的語氣寬和,然而話意卻極尖刻。
卓炎看著他,只稍稍蹙了下眉。
文乙并未從臉上看到他意想之中的大驚失,心已約升起一不安,而接下去問出口的話則更出乎他的意料:
“文總管。長寧大長公主是否曾心儀于周懌將軍?”
文乙詫而啞然無聲。他未說是,亦未說不是。
但他既未出聲否認,這態度便足以令卓炎篤定。的臉上未多一分異樣表,也仍舊沒有回答文乙的話。
頃,開口了,像是要捋順自己心的疑,亦像是要順道從文乙求證一般地,娓娓而道:
“文總管對我說的這些事,必定是真的。炳靖是什麼樣的子,若一旦得知有人在我面前傳謠,他豈能饒得了人?而文總管既然敢背著他對我說這些,必定是因為這些事并非炳靖想刻意瞞我,而是他遲遲不敢同我說。否則,他必將怪罪于總管。
“他心思縝,天地不懼,亦知我手上沾過多,他又有何故不敢同我說這些?他必定是怕我若一朝得知這些事,會不再他了。
“他殺人,不是為了安家國,不是為了振社稷。他是為了謀圖這大位。否則,他不會怕我不再他。
“可他若想要晉帝之位,何不在當年弒君父后即自登基?何必要再扶持被他殺害的亡兄之子,徒留大患?
“周將軍能為長寧大長公主痛泣,若長寧大長公主亦曾心儀于他,他二人何故不能廝守?是因公主與鄂王,周將軍只能擇其一?可公主對炳靖,至親至,周將軍又何以陷兩難之地?
“是因炳靖所謀之事,終會傷及公主。而周將軍若尚公主,則不能再助炳靖其大事。
“文總管。我說的,都對麼?”
文乙只有僵愣。
卓炎眼中如漆黑夜幕,無星無:“炳靖他要的,不是這晉室之帝位,不是這戚氏之江山——
“因他本就不姓戚。對麼?”
猜你喜歡
-
完結2579 章
蝕骨危情:爹地,媽咪又跑了
被親人設計陷害,替罪入牢,葉如兮一夕之間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監獄產子,骨肉分離,繼妹帶走孩子,頂替身份成了謝總的未婚妻。六年監獄,葉如兮恨,恨不得吃血扒肉。一朝出獄,她發現繼妹和謝總的兒子竟和自己的女兒長得一模一樣……在眾人眼中不解風情,冷漠至極的謝總某一天宣佈退婚,將神秘女人壁咚在角落裡。葉如兮掙紮低喘:“謝總,請你自重!”謝池鋮勾唇輕笑,聲音暗啞:“乖,這一次冇找錯人。”一男一女兩個萌娃:“爹地,媽咪帶著小寶寶離家出走啦!”
230.7萬字7.35 475716 -
完結787 章

閃婚密愛:我的老公是大佬
童年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總裁夫人,更不會想到這位總裁竟然是自己上司的上司。幸虧她只是個小職員,跟這位總裁沒什麼交集。要不然她跟總裁隱婚的消息遲早得露餡。不過童年想方設法的隱瞞自己的婚史,總裁倒是想方設法的證明自己結婚的事實。 “當初不是說好了對外隱婚,你巴不得讓全世界的人知道是怎麼回事?”面對童年的掐腰質問,許錦城戴上耳機看文件假裝聽不到。反正證已經領到手了,童年現在想反悔也沒用了。某人露出了深不可測的笑容。
100.6萬字8 34339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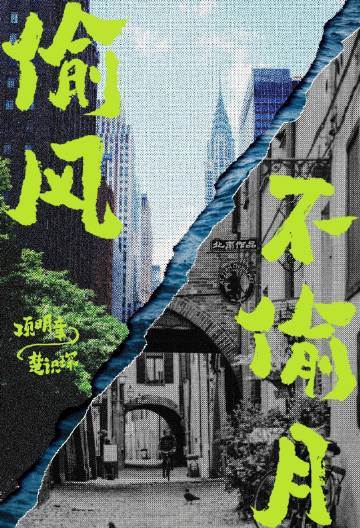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511 章

大院嬌妻純又欲,高冷硬漢破戒了
軍婚+先婚后愛一睜眼,溫淺穿成了八十年代小軍嫂。原主名聲壞、人緣差,在家屬院作天作地、人嫌狗厭,夫妻感情冷若冰山。開局就是一手爛牌!溫淺表示拿到爛牌不要慌,看她如何將一手爛牌打得精彩絕倫,做生意、拿訂單、開工廠、上大學、買房投資等升值,文工團里當大腕,一步步從聲名狼藉的小媳婦變成納稅大戶,憑著自己的一雙手打下一片天。——周時凜,全軍最強飛行員,他不喜歡這個算計了自己的妻子,不喜歡她年紀小,更不喜歡她長得嬌。初見紅顏都是禍水!后來媳婦只能禍害我!
94.6萬字8.18 108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