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你不能言》 第2024章 息事寧人?
不過所料,到了正式的畫廊,裡麵早已是高朋滿座的景象,我們這拖家帶口的,倒是顯得格外突兀了。
進門之後,慕容謹就被其他客人纏住,我們就隨便到看了看。
畫廊采用的是上世紀歐洲的建築風格,中空及頂的大堂,通過做舊的手法,為整個房間的室增添了不曆史的韻味,懸掛於壁牆之上的諸多油畫在這樣的氛圍襯托下,更有種高不可攀的神。
經過正中心的位置,沈鈺盯著牆上蒙娜麗莎的微笑,停住了腳步,微瞇著眸子揣道,“你們猜這副是真跡還是贗品?”
“真跡吧。”我想都沒想便口而出,“能來這裡的非富即貴,況且慕容謹家底殷實,不至於弄一副假的出來充門麵。”
“你怎麼看?”沈鈺又問傅慎言。
“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傅慎言淡漠道,“油畫本沒有什麼價值,而是人們的追捧造就了今時今日的熱度,某種程度上講,將作者的人生經曆和附加於作品之上,是一項十分出的營銷手段。”
Advertisement
“用不著你跟我講生意經,我是在跟你談論,這幅畫有幾分真假。”沈鈺雙手抄兜,將西裝外套往後起,突然開始較真。
傅慎言勾起角冷笑了一聲,一邊彎將安歆抱起,一邊漫不經心的說道,“有多人相信,就有多分真。”
說完,就帶著孩子去看彆的畫作去了。
剩下我和沈鈺,互相換了一下視線之後,抖肩表示無奈。
話糙理不糙,藝品這行的水的確太深,和賭石炒一樣,都是高風險投資,賠的傾家產那也是常有的事。
不過看慕容謹這樣高調的做派,顯然也是這一行裡的翹楚,也就是為數不多決定遊戲規則的人,自然是絕對的一本萬利。
名家作品大賞對我們本就沒什麼吸引力,幾分鐘後,都已經失去了剛踏這座殿堂的興。
安歆好,傅慎言索帶到外麵的山莊,看花鳥魚樹去了。
沈鈺原本是一直陪著我的,但中途國來了個電話,又不好打擾正廳的氛圍,就拿著手機到外麵的走廊去了。
站了一會兒有些累,我正準備找個地方歇歇腳,慕容謹的聲音卻好巧不巧的從旁邊傳了過來。
“大嫂認為,這畫上畫的是漲,還是退?”
我愣了一下,站直子,才發現他說的是掛在我麵前牆上的一幅畫。
油畫的意境很,海邊,,海浪高高疊起,作畫的人是以遠為視角落筆的,因此乍一看上去,既像是漲,也可以說是退。
細細揣了一陣,我給出答案,“漲,畫裡描述的顯然是落日時分,海水上漲的畫麵,看那太,雖然紅火,卻是即將湮滅與海平線的。”
慕容謹角掛著淡淡的笑意,微垂眼瞼,“我倒覺得是退,日出時分,海鷗紛飛,水落退,歸於源頭,可以想見之後的恢弘壯闊,正如人生,退一步,海闊天空。”
到底是在背後蟄伏了這麼多年的人,如此簡單的一幅畫,竟也能一語雙關。
照這句話的意思,慕容謹是想息事寧人?
bqg99。bqg99
猜你喜歡
-
完結825 章

穿到七十年代
東北梨樹村夏家人:“夏天,切記到了部隊要給我們爭光。”殷殷期盼的目光…… 到了部隊的夏天:“葉團長,我是知性婉約派!你能不能不要總是讓我陪你吃、陪你玩、陪你生孩子!” 葉伯煊:“天兒啊,無論七十年代還是二零一五年,完美人生都逃不開這幾樣。”傲嬌的站在穿衣鏡前,擦著友誼雪花膏。 夏天:你是七十年代的首長?為什麼比我一個穿越來的還不靠譜!
171.4萬字8.18 91336 -
完結942 章

楚少,夫人又在打你的臉了
得知從不近女色的楚家大少是為了一個神秘女網友回國,全城的女人都瘋了。得知楚大少不問姓名不要電話不求照片跟女網友純聊了5年,全城的男人也瘋了。【萬眾期待的大型奔現現場:】楚大少看了看眼前那個搶了他生意壞了他好事還打過他巴掌的漂亮『前女友』。楚大少:【你就是那個在小漁村賣手打魚丸的『海上霸王花』?】蘇若夏:【難道我不是嗎?】楚大少點頭:【是,你是霸王花本花。】蘇若夏看了看對麵高冷禁慾的威嚴男人,冷笑。蘇若夏:【說好的『絕世小奶狗』呢?】楚大少抱著一隻博美犬,寵溺一笑:【絕世是我,奶狗在這。】
94.7萬字8 57721 -
完結820 章

重生后我靠種田逆襲了
家里的桂花樹成精了!帶著意外身亡的梅夢珍回到了2007年。看著父母留下的3200塊錢,梅夢珍決定帶著弟弟擺脫貧窮。人家都說大隱隱于市,那她就小隱隱于菜市場。本想利用空間賺點生活費,誰知這個生活費漸漸地有些不受她的控制啊!ps:本文一切屬平行…
150.2萬字8 38882 -
完結1220 章

一睡成癮:邪性總裁太難纏
三年婚姻,在丈夫的出軌,婆婆的毒打之后面臨告終。她想要脫身,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他從天而降,救她于水火,將最好的一切捧在她的手心。她是他的獨一無二,他是她的萬里挑一。直到那一天,她看見他的身邊又站著另外一個女人………
213.2萬字8 107273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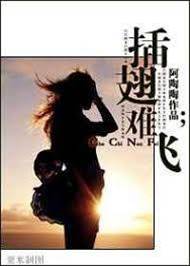
插翅難飛
美麗少女爲了逃脫人販的手心,不得不跟陰狠毒辣的陌生少年定下終生不離開他的魔鬼契約。 陰狠少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孩,卻不知道怎樣才能讓女孩全心全意的隻陪著他。 原本他只是一個瘋子,後來爲了她,他還成了一個傻子。
23.5萬字8 17235 -
完結59 章

和冷漠老公互換后的豪門生活
本書章節內容有問題,請大家在站內搜索《和冷漠老公互換后的豪門生活》觀看完整的正文與番外~ 別名:和陰鷙大佬互穿后我躺贏了,和陰郁大佬互穿后我躺贏了 豪門文里,陰鷙強大的商業帝王意外成了植物人,沒人知道他的意識清醒地困在身體里。寧懿從苦逼末世穿來成了他的炮灰妻子,因為替嫁姐姐而心態扭曲,正要虐待殘廢老公。然后,他們倆互換了身體。看著寧懿代替自己躺尸,男人滿是惡意:“這滋味,如何?”…
26萬字8 70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