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愛情以時光》 第868章 懷疑
對於夏聖一而言,所有跟路瑤沾邊的人,都不是什麼好東西。所以能夠讓湛白難堪。樂得揭穿這個。
但不知道的是,湛白是無所謂的,他從來也沒想遮掩自己是gay的‘事實’。整個夜大的人都知道。
他唯一詫異的是。這話怎麼會從夏聖一的裡說出來,而且……還一口咬定是紀貫新說的。
人看人。一看一個準,徐應嘉從夏聖一眼中看到了赤aa的敵意。即便夏聖一自以爲笑的天真爛漫。
所以不待湛白回答,徐應嘉先說話了。“誰告訴你gay只能跟男人在一起玩兒?你說的這話都讓我覺得好笑。你到底是從國外回來的,還是從地球外面回來的?”
夏聖一不是裝傻充愣嘛,徐應嘉也是笑著反問。只不過是嗤笑。
夏聖一聞言。趕忙改口道:“我沒有別的意思。你們不要生氣。”
徐應嘉剛想問到底是什麼意思,湛白卻淡笑著說:“沒關係。我對這事兒不敏,而且我跟嘉嘉也不是。”
說罷。他轉而一問:“你跟朋友來的嗎?”
夏聖一笑著回道:“跟我小叔一起來的,他之前一直沒空,今天才空出時間陪我一起吃飯。”
湛白點頭道:“那不打擾你們了,我們也去吃飯了。”
三人在走廊中聊了幾句,等到夏聖一走後,徐應嘉才皺著眉頭,低聲罵道:“沒病吧?有這麼說話的嗎?”
湛白卻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沒有馬上出聲。
徐應嘉看著湛白道:“這都馬上要畢業了,你還打算當‘gay’啊?”
其實湛白不是gay,他只是很煩邊總有各式各樣陌生的人追他,才見過一面,就突然跑過來說喜歡他。他就納悶了,喜歡他什麼?兩個互相不瞭解的人,除了長相就只能看了吧?
Advertisement
那幫的不怕被佔便宜,他還嫌心臟呢。
所以徐應嘉說湛白長了顆‘人’的心,特別潔自好,爲了杜絕那幫狂蜂浪蝶,所以他乾脆高調宣稱自己是gay,起初大家也是不信的,直到真的看見湛白跟幾個男生往過。
至於路瑤爲何會相信,這事兒說起來更讓人哭笑不得。有一次路瑤在路上見湛白,看見他牽著個男人的手,兩人一起逛街。著把這事兒跟徐應嘉說了,徐應嘉知道湛白不是gay,所以當然會問。
結果湛白說那是他表弟,因爲先天的自閉癥,所以出門在外都要有人領著。
也許這就是差錯惹的禍,路瑤真的以爲湛白是,可他並不是。徐應嘉跟湛白私底下打賭,看路瑤到底什麼時候能發現,結果一晃好幾年了,路瑤也是有夠麻木的。
徐應嘉鬧心的是別人懷疑湛白的取向,而湛白懷疑的是夏聖一剛剛說的話。說是紀貫新告訴的。
如果說路瑤告訴紀貫新他是gay,那湛白信,畢竟人家兩個是,說什麼都是理之中。可紀貫新憑什麼告訴夏聖一?
夏聖一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難不,想用這樣的方式來間接的告訴他們,在紀貫新的心裡,跟路瑤是一個位置的?
“欸,想什麼呢?”徐應嘉用手肘撞了下湛白的手臂,側頭打量著他的臉,怕他因爲剛纔的事不開心。
湛白微垂著視線,徑自嘀咕,“咱倆沒有惹過夏聖一吧?”
“啊?”徐應嘉眉頭一蹙,隨即道:“咱們總共才見過兩面,話都沒說上十句,所以我才說有病。”
湛白低聲道:“不是衝著我們,那隻能是衝著瑤瑤了。”
聽湛白一個人叨咕,徐應嘉側頭問:“你大點兒聲,想什麼呢?”
湛白側頭回視徐應嘉,認真的道:“夏聖一剛纔那話,擺明了帶刺兒,如果不是爲了刺我們,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因爲我們跟瑤瑤的關係。而能跟瑤瑤有什麼仇?還不是因爲紀貫新?我這話說的沒錯吧?”
湛白一連串的話功讓徐應嘉變了臉,剛開始只覺得夏聖一那話來的突兀又惹人嫌,但是沒往下想。湛白這麼一說,沉默數秒,然後道:“你懷疑夏聖一跟紀貫新……”
湛白出聲糾正,“不一定是‘跟’,而是‘對’。“
徐應嘉一時間有些懵,湛白直接告訴,“我不信紀貫新會跟夏聖一有什麼,不是他二嫂的親侄嗎?但夏聖一對紀貫新,可真的說不準了。”
徐應嘉眼睛一瞪,吃驚的道:“夏聖一喜歡紀貫新?!”
湛白不置可否。因爲除了這個可能,他想不到夏聖一爲何好端端的給他‘難堪’。
徐應嘉嚇得夠嗆,不由得說:“不是紀貫新小叔嘛,沾親帶故的,怎麼還能有這種想法?”
湛白不以爲意的回道:“親侄都能上親小叔,更何況還是八竿子打不著,完全沒有緣關係的兩個人?”
既然是沒什麼不可以,徐應嘉當即瞪眼道:“那瑤瑤現在不在夜城,就剩夏賤人一個人在這邊,又是這樣的心思,豈不是很危險?”
湛白道:“我只是懷疑,還沒有證據,如果現在直接跟瑤瑤說,你覺得那子,會怎麼想?”
徐應嘉學著路瑤的口吻,一臉茫然加驚詫的樣子,“不會吧?”
湛白沒笑,只是徑自道:“而且我們也不知道紀貫新心裡怎麼想的,突然打了個電話回去,萬一惹得瑤瑤跟紀貫新之間鬧矛盾,那我們什麼了?”
徐應嘉皺眉道:“但這麼大的事兒,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啊,而且我也覺得你分析的有道理,我越看越覺得那個小賤人不順眼。就算我們不明說,總得暗示一下吧?不能讓瑤瑤矇在鼓裡。”
湛白最擔心的還是路瑤,所以思忖片刻,他還是掏出手機,給路瑤打了個電話。
路瑤那頭很快就接了,心很好的說:“白公子,怎麼有空給我打電話?”
湛白脣角勾起溫的弧度,淡笑著道:“我跟嘉嘉吃飯呢,突然想起你了,給你打個電話,問問你在冬城那邊待得怎麼樣。”
路瑤輕笑著回道:“好的啊,正跟我爸商量出國去哪兒呢。”
“出國?你要跟叔叔出國嗎?”湛白擡眼看了下對面的徐應嘉,徐應嘉也在仔細聽著,聞言,眼詫。
路瑤道:“貫新非讓我帶我爸出國溜達一圈,我這不正勸著呢嘛,我爸不想去。”
湛白問:“怎麼突然你們出國?我跟嘉嘉還等著你回夜城呢。”
路瑤道:“貫新說結婚之前,讓我好好陪陪我爸,我爸也沒出過國,他讓我跟我哥陪我爸出國玩兒一趟。”
偏偏是這個當口,偏偏紀貫新路瑤出國。
聽到這話,湛白跟徐應嘉皆是一臉憂,看不懂紀貫新心裡想什麼。
湛白商很高,他不著痕跡的問道:“那紀貫新不跟你們一起去嗎?”
路瑤道:“他最近忙的,之前來冬城只待了不到兩個小時就匆匆趕回去了。對了,你們在夜城那邊,聽沒聽到什麼消息?是他公司有事兒嗎?”
一邊是路瑤焦急的問候,一邊是紀貫新在陪夏聖一吃飯。徐應嘉當即撂了臉子,險些衝口出,卻被湛白的眼給止住。
他說:“沒什麼事兒,你別擔心。你跟叔叔確定去哪玩兒告訴我們一聲,省的我們惦記,也別走得太遠去的太久,頂多待一個禮拜就回來吧,不然跟紀貫新分開這麼久,你不怕他想你,你還不想他嗎?“
徐應嘉知道湛白在暗示路瑤,可是路瑤未必知道,這覺真是熱鍋上的螞蟻,備煎熬。
路瑤聞言,先是回了幾句,隨即小聲說:“我告訴你們一個事兒,我都沒跟我爸說。”
湛白問:“什麼事兒?”
路瑤的聲音隔著手機都著難掩的喜悅,輕笑著道:“貫新跟我求婚了。”
湛白頓時一愣,徐應嘉也是瞪大眼睛。
忍不住對著手機方向道:“紀貫新跟你求婚了?什麼時候的事兒?”
路瑤道:“就是前天晚上,他來冬城,把戒指給我了,但是夜城那邊有急事兒,他就連夜趕回去了。”
這徐應嘉就看不懂了,如果說紀貫新揹著路瑤跟夏聖一有一的話,又怎麼會跟路瑤求婚?可如果他什麼事兒都沒有,又爲何要騙路瑤,讓路瑤全家出國?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徐應嘉想不通,只得迷茫的看向湛白。湛白一時間也看不,不過直覺告訴他,紀貫新對路瑤不是假的,不然他倆早就分了,何必鬧騰到現在?
如此想著,湛白先是笑著恭喜路瑤,隨即又囑咐了幾句,然後掛斷電話。
徐應嘉著急的問:“怎麼回事兒?”
湛白也難得的蹙起眉頭,半晌才說:“問題出在紀貫新這兒,我們跟瑤瑤說,知道的還沒我們多,說了只能讓更擔心。”
徐應嘉又問:“那現在怎麼辦?”
湛白也在想怎麼辦,無論如何,不能再讓路瑤傷了。那麼紀貫新,但凡有丁點兒的偏差,這輩子都完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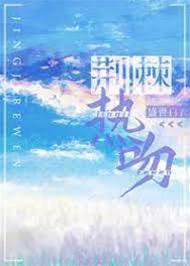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2033 章
盛世婚寵:帝少難自控
她的孩子還未出世便夭折在肚子裏!隻因她愛上的是惹下無數血債的神秘男人!傳聞,這個男人身份成謎,卻擁有滔天權勢,極其危險。傳聞,這個男人嗜他的小妻如命,已是妻奴晚期,無藥可治。他說:夏木希,這輩子你都別想從我身邊逃開!你永遠都是我的!她說:既然你不同意離婚,卻還想要個孩子,那就隨便到外麵找個女人生吧!我不會怪你。五年後她回來,發現那個男人真的那麼做了。麵對他已經五歲的孩子時,她冷冷地笑著:秋黎末,原來這就是你放棄我的原因?那時她不知道,這個男人已丟掉了一隻眼睛……而這個五歲的孩子,竟也滿身是謎!——那是夏與秋的間隔,夏的末端,是秋的開始。秋,撿到了失意孤寂地夏的尾巴。夏,許諾終生為伴,永不分離。經曆了離別與失去,到那時,秋,還能否依舊抓住夏的氣息?
566.6萬字8 14283 -
連載1657 章

雙寶媽咪是大佬顧挽情
五年前,顧挽情慘遭未婚夫和繼妹算計,與陌生男子共度一夜,母親因此自殺,父親嫌她丟人,將她驅逐出家門。五年后,顧挽情帶著龍鳳胎回歸,一手超凡醫術,引得上流社會無數人追捧。某德高望重董事長,“我孫兒年輕有為,帥氣儒雅,和你很相配,希望顧神醫可以帶著一雙兒女下嫁!”追求者1:“顧神醫,我早就仰慕你,傾心你,希望可以給我個機會,給你一雙兒女當后爸,我定視為己出。”
166萬字8 338525 -
完結442 章

把她送進監獄後,慕少追悔莫及
慕南舟的一顆糖,虜獲了薑惜之的愛,後來她才知道,原來一顆糖誰都可以。一場意外,她成了傷害他白月光的兇手,從京都最耀眼的大小姐,成了令人唾棄的勞改犯。五年牢獄,她隻想好好活著,卻背著“勞改犯”的標簽在各色各樣的人中謀得生存。再遇慕南舟,她不敢愛他,除了逃,還是想逃!慕南舟以為他最討厭的人是薑惜之。從小在他屁股後麵跑,喊著“南舟哥哥”,粘著吵著鬧著非他不嫁,有一天見到他會怕成那樣。他見她低微到塵埃,在底層掙紮吃苦,本該恨,卻想要把她藏起來。她幾乎條件反射,麵色驚恐:“放過我,我不會再愛慕南舟了!”慕南舟把她禁錮在懷中,溫柔纏綿的親她:“乖,之之,別怕,叫南舟哥哥,南舟哥哥知道錯了。”
85.7萬字8 63357 -
完結561 章
離婚后孕吐,總裁前夫追瘋了
隱婚三年,他甩來離婚協議書,理由是他的初戀回來了,要給她個交待。許之漾忍痛簽字。他與白月光領證當天,她遭遇車禍,腹中的雙胞胎沒了心跳。從此她換掉一切聯系方式,徹底離開他的世界。后來聽說,霍庭深拋下新婚妻子,滿世界尋找一個叫許之漾的女人。重逢那天,他把她堵到車里,跪著背男德,“漾漾,求你給我一次機會。”
117.1萬字8 257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