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妃天下》 第57章 人心鬼測
——老子是月票沒有來,自掛東南枝的分界線——
舒雲郡是天朝與犬戎兩國國境附近最大最繁華的郡縣,每日裡都不客商往來,但是自從犬戎發了馬瘟會傳染人之後,錦衛爲首的人帶領邊軍將兩國國境封鎖,只許出,不許進,這裡的生意便蕭條了許多。
而且最近秋日的時氣不好,總是薄雨綿綿。
城門邊,錦衛小隊的小隊長劉利走出門邊的休息小屋,擡頭看了看天,他擰起兩道眉,呸了聲:“破天氣,又要下雨了。”
另外一個錦衛廠衛也嘆息道:“就是,聽說隔壁縣裡的稻子都爛在了地裡,如今存糧不夠,又有不人因爲這樣的天氣都病了。”
劉利聞言,有點懷疑地道:“會不會是疫病傳染進來了?”
邊圍繞的幾個廠衛都嚇了一跳,互看一眼,沒有說話。
倒是劉利自己看了眼警惕地守在門外的邊軍們,自言自語地道:“應該不會吧,張來三那人比我還狠辣,守著隔壁的縣城,蒼蠅都飛不進去,怎麼會有人生病?”
其他廠衛們也紛紛點頭道:“正是。”
說話間,衆廠衛們忽然聽見外頭一陣吵鬧,劉利提著刀領著衆人過去一看究竟。
原來是四五個小小的三四歲的小娃娃,正被一個有些胖木然的男子領著,站在城門口被邊軍的人攔下了。
劉利見那胖子不但斷了右臂,而且似乎是個啞,他只會手指著城門,表示他要進城,幾個孩子怯怯的躲在他後。
那邊軍領頭的百夫長似乎很有些猶豫,看著那幾個小孩子,已經是想放人了,卻又很猶豫,忽然看見劉利過來,那百夫長立刻領著幾個邊軍過來對著他道:“劉隊長,您看這幾個孩子都壞了,他們爹方纔比劃了半天,告訴咱們他們遇到劫匪了,份路引都被了,上也沒有什麼錢財,他想帶孩子進城弄點吃食。”
Advertisement
劉利看著那胖子雖然臉慘白,右臂又斷了,但上也是乾乾淨淨的布衫,連著幾個孩子也看起來很乾淨,倒是不像壞人。
但他還是冷冷地道:“上峰有命令,是不允許任何人進城的!”
那胖子剛聽他說完話,便噗通一聲跪在了地上,眼裡淚水直流,再將幾個孩子推到了他的面前。
幾個孩子也‘嗚哇’一聲哭了起來,抱著小肚子喊。
可憐之狀讓人不忍,那百夫長看了就有些不悅地道:“劉隊長,這幾個不過是孩子,而且看著也是清白人家的,不像生病,不像行商的,更不像犬戎人,爲何不能讓他們進呢!”
雙方的商隊、探親的犬戎人,都絕對止進城。
其他的幾個邊軍士兵也頗爲生氣地道:“正是,上峰就是有令,也法理不外人,有誰會帶著小孩子來行商呢?”
邊軍士兵對於錦衛這些人向來沒有好,而且突然過來接管了指揮權,京城做派也讓這些邊軍非常不適應,但非常時期,雙方也都算通力合作,倒也沒有生出什麼事來。
劉利看著那些義憤填膺的邊軍,再看了好一會那些小孩,實在看不出什麼不對經,那些小小的孩子也極爲可憐地看著他,於是劉利心中一,不得不嘆息道:“好罷。”
說罷,他甚至從腰上取了半吊錢出來給那胖子,那胖子看著他的眼神忽然閃過一複雜,但劉利想要細看的時候,卻發現他眼睛還是那麼呆滯。
劉利聽著後那些邊軍們彷彿刮目相看的讚之詞,再看著那胖子千恩萬謝地點頭離開向城走進去的背影,他不總有些不安,或者說相當不安,卻不知道爲什麼。
那胖子領著幾個小孩兒走到了城裡一安靜小巷附近,他牽著一個三歲的孩子走進小巷的一個水井邊,他蹲了下來,拿出了一個袋子,從裡面掏出了一隻燒餅遞給那個小小的男娃娃。
小男孩兒很久沒有吃到這樣的東西了,怯怯地看了那胖子一眼,那胖子點點頭,出個笑容來,小男孩了鼓勵,立刻捧著燒餅狼吞虎嚥起來,卻沒有看見那胖子眼裡閃過一濃濃的悲傷。
雪亮的匕首伴隨著飛濺的鮮從那小小的裡同時出來,小男孩手裡的燒餅掉地,他茫然地看著自己口流淌的鮮,他還不能理解這意味著什麼。
胖子忽然臉上獰一閃,抱起小男孩的抖的直接扔進了井裡。
“噗通!”
水井很快地淹沒了那掙扎的小小的。
胖子盯著那隻掉在地上的染的燒餅,發了一會兒呆,然後撿起燒餅也扔進了水井,沒了舌頭的一開一合,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過了一會,他轉拖著沉重的腳步向外走去,領著剩下的孩子,提著剩下的燒餅,慢慢地向另外一條街道的水井所在走去。
重複著——下一個燒餅的故事。
……
一個月後
上京
太極殿東暖閣
“冀東郡守來報,冀東十二縣發現染了馬瘟疫癥狀之人!”
“報,章閣郡守來報,章閣七縣發現了馬瘟蔓延之跡象!”
“報……。”
各種關於各地疫發展與請求救援的奏章如雪片一般地飛進上京,迅速地堆滿了九千歲批閱奏章常用的案頭,乃至放不下之後堆在地上。
太醫院的上至醫正,下至尋常醫也已經全部在太極殿西暖閣住下了,每日往返於太醫院與西暖閣之間,不得回府。
張的氣氛迅速地從民間蔓延到宮中,從宮人到嬪妃,每個人的上都帶著艾草、靈香草等避穢防病的香囊。
而民間更是不用說,艾草如今爲最俏的藥材,原本一文錢一斤的艾草都漲價到了五文錢一斤還是照樣被大量的搶購。
從宮到民宅,全部都飄著燃燒著艾草的味道。
百里青瞇著魅的眸子,冷冷地睨著正在桌子前研磨藥材的老醫正,很是不耐地道:“老頭兒,你到底什麼時候有個結論,這到底是馬瘟還是人瘟!”
老醫正習慣了他這種語氣,但還是擡頭瞪了他一眼:“臭小子,再這麼沒大沒小的,就從東暖閣滾出去!”
說罷,又低頭繼續研磨自己的藥材。
連公公瞥了眼百里的臉,不由暗自苦笑,敢讓九千歲滾的人怕是隻有老醫正了。
百里青臉青了青,冷冷地嗤笑:“老頭兒,這是本座的地盤!”
老醫正也冷笑一聲:“好,那老頭子滾就是了!”
說罷,老醫正一卷手上的東西就要麻利地帶著自己提著藥箱的藥‘滾’了,百里青見著他真要走,不由又急又惱,卻拉不下臉來,只咬牙切齒:“臭老頭!”
老醫正剛走到門口就被進來的人攔住了。
一道清亮和的子聲音響起:“爺爺,您不要理會阿九那個笨蛋,他心急過頭罷了。”
老醫正看著自己面前的子,臉上的表方纔下來,卻依舊沒好氣地道:“小丫頭,你不必爲那個臭小子說話,老頭子看他是吃了火藥了!”
西涼茉拉住老醫正的手,彎著水的大眼兒笑了笑:“爺爺,咱們不理他就是了,茉兒新近發現一些奇怪的事兒,打算和您商討一番呢。”
說著,就攙著老醫正回到窗邊的凳子上坐下。
人上了年紀,就喜歡看著喜慶的東西,見著西涼茉甜和的笑,老醫正心頭舒服了許多,而且又聽說西涼茉有事兒與他商量笑瞇瞇地道:“好,咱們不理那個怪氣的臭小子,以後丫頭要是嫌棄他老牛吃草,爺爺再給你找個好的!”
怪氣?!
老牛吃草?!
百里青“咔嚓”一下將自己修長尾指上戴著的純金鑲寶石的護甲給斷。
所有人都忍不住臉怪異,努力地憋住笑,只怕上頭那位臉黑似鍋底的爺會發飆!
唯獨西涼茉警告地瞥了他一眼,然後微笑著坐在了老醫正邊:“爺爺,我想知道,如今對於馬瘟傳染人,您和太醫院的醫們可有什麼結論了麼,或者有頭緒了麼?”
說到正事,老醫正便也微微顰眉道:“這事兒其實老頭子倒是在一本無名氏著的《金針饋》上見到過,只是此事一向甚發生,而且就算有,也很難像尋常瘟疫那樣傳染得如此厲害,所以相當棘手,通常一人染,然後很快周圍的人都會染,經常是一村、一鎮甚至一縣的人快速地死去。”
西涼茉從腰上的小袋子裡拿出來一張薄如蟬翼的地圖鋪開,上面的山川河流極爲詳細,赫然是一幅天朝的詳盡地圖,上面在不地方都著一張小巧的銅紅的銅葉子。
點了點那些著銅葉子的地方,神凝重:“您看,這些都是疫病發之,茉兒覺得有些奇怪,雖然這染之地是從與犬戎界的路年縣開始蔓延,然後一路蔓延進了咱們中原陸,但是一個月的時間,不免有些太快了,按理說這種瘟疫潛伏期很短,三到五日,發病之後,就會全無力,高熱,七日之臟出而死,但是正是由於這樣短暫的病程和死亡期,纔不應該蔓延如此之快。”
老醫正一愣,隨後仔細地看向那地圖,顰眉道:“丫頭,你是說因爲染者很快就會死去,而且從邊境之城到了其他繁華市鎮始終是需要走一定的時間的,所以不應該那麼快速的蔓延開來是麼?”
西涼茉點點頭,又看向老醫正:“茉兒記得之前您說過,據各地傳來的資料來看沒,這樣的病多半是通過接傳染的,也就是說次病的病氣不會通過風來傳染,若是沒有沾染上對方的,沒有喝了被染的水源,此病是不會被傳染的。”
目前就自己有限的醫療常識來看,這種臟出而死的病,非常像前世的某種恐怖的四級出熱病毒染,但是這時代沒有流行病學調查,非常的難以確定傳染的方式與疫病對什麼藥有反應。
“正是,老頭子也覺得這病有點古怪,秋日天長,雖然容易有疫病,但也不至於如此古怪迅速,不過老頭子派出去的人如今已經在嘗試各種藥了,有些方子還是能有些效果,但是恐怕很難很快研製出最有效的藥。”老醫正太,嘆了一聲,隨後道:“咱們還是隻能從控制傳染速度上先下手。”
西涼茉微微顰眉,正要說什麼,卻忽然聽見後一道冷的聲音響起:“本座早已經派出錦衛和司禮監聽風部的探子,去截斷那些有疫病發的郡縣出行之路,但是就連錦衛的人都染了疫病!”
百里青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走到兩人的後,正睨著那張了不銅葉子的地圖。
他沉聲道:“如今長江與大運河以南尚且沒有發現病癥,我打算立刻派兵以此爲界,將兩地隔開,同時封鎖一切消息,以前與西狄仁打仗的數十萬大軍軍心不穩。”
如今參戰的一半士兵都來自長江與運河以北,若是發現後方家中出事,只怕無心應戰。
“這事兒,會不會是西狄人乾的?”老醫正忽然捋著鬍子懷疑地道。
西涼茉想了想:“這倒不是不可能,但是不管是誰幹的,阿九的對策都沒錯,但是我認爲咱們不能只一味封鎖消息,不管此事是否人爲,咱們都必須搶先一步做好準備,不若令人去通知前方士兵,咱們這裡發了大規模的風寒疫病,然後告之咱們急缺生長在西狄境的艾草,反倒是能激發士兵們的,不給有心人作的空子!”
百里青和老醫正都睨著西涼茉片刻,同時挑眉道:“你這詐的丫頭!”
西涼茉看著他們兩人,忍不輕笑:“二位連表都一模一樣啊,真不愧是‘父子’。”
老醫正和百里青兩人同時臉上都有赧,不約而同地別開頭:“誰跟他是‘父子’。”
發現自己與對方做了同樣的事,兩人各自又冷哼一聲。
西涼茉暗自搖頭,還是把話題拉回到了正事之上:“阿九,我已經讓者字訣的三分之二的醫者前往疫區,相信很快能慢慢發現更合適的藥方醫治病癥,但是首先咱們還是要把長江與運河以北的地方郡縣全部戒嚴,不管到底有發疫病的郡縣,都不允許任何人口流。”
幾人細細商定了許多的相應的政策,便令人一路快馬加鞭推行實施。
——老子是月票不見漲,小白自掛東南枝的分界線——
“雲香,你手上怎麼有那麼多紅點兒?”司制房的柳司制瞅著大宮雲香手上的紅點兒不由奇怪地道。
雲香臉原本就有些蒼白,聞言,不由一僵,隨後輕聲道:“沒事,只是被蟲兒咬了。”
兩人一路談著的影遠去,無人留意到後轉出一道頎長的影。
芳看著那宮人遠去的影,不由挑眉,上起紅點兒?
怎麼與那些瘟疫之兆如此相似?
他頓了頓,若有所思地一笑,看來,這宮裡要變天了,只是不知道那宮人的目標是誰?
猜你喜歡
-
完結159 章

嫁給奸臣沖喜后
傅瑤要嫁的是個性情陰鷙的病秧子,喜怒無常,手上沾了不知多少人的血。賜婚旨意下來后,不少人幸災樂禍,等著看這京中頗負盛名的人間富貴花落入奸臣之手,被肆意摧折。母親長姐暗自垂淚,寬慰她暫且忍耐,等到謝遲去后,想如何便如何。傅瑤嘴角微翹,低眉順眼地應了聲,好。大婚那日,謝遲興致闌珊地掀開大紅的蓋頭,原本以為會看到張愁云慘淡的臉,結果卻對上一雙滿是笑意的杏眼。鳳冠霞帔的新嫁娘一點也不怕他,抬起柔弱無骨的手,輕輕地扯了扯他的衣袖,軟聲道:“夫君。”眾人道謝遲心狠手辣,把持朝局,有不臣之心,仿佛都忘了他曾...
46.3萬字8 58850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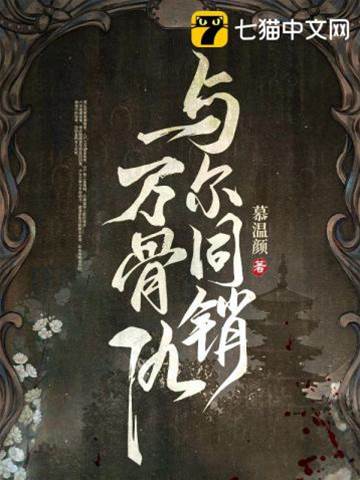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
完結191 章

妾身嬌貴
莊綰一直以為,她會嫁給才華冠蓋京城的勤王與他琴瑟和鳴,為他生兒育女。然,一夕之間,她想嫁的這個男人害她家破人亡,救下她後,又把她送給人當妾。霍時玄,揚州首富之子,惹是生非,長歪了的紈絝,爛泥扶不上牆的阿鬥。初得美妾時,霍時玄把人往院裏一扔讓她自生自滅。後來,情根已深種,偏有人來搶,霍時玄把小美人往懷裏一摟,“送給爺的人,豈有還回去的道理!”
51.9萬字8.18 18298 -
完結347 章

囚她
施家二小姐出嫁一載,以七出之罪被夫家休妻,被婆婆請出家門。 無子;不事舅姑;口舌;妒忌。 娘家一席軟轎把她帶回。 她住回了自己曾經的閨房。 夜裏,她的噩夢又至。 那人大喇喇的端坐在她閨房裏,冷笑睨她。 好妹妹,出嫁一年,連自己娘家都忘了,真是好一個媳婦。 她跪在他身前,眼眶皆紅。 他道:“不是想要活着麼?來求我?” “你只許對我笑,對我體貼,對我賣弄,對我用十分心計,藉由我拿到好處。”
56萬字8.18 32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