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定有過人之處》 第五章
這日長孫信與幽州刺史一番相見,相談甚久,半夜纔回,對於驛館裡發生的事本一概不知。
直至第二日一早,他起不久,驛丞來他客房外求見,將接到的令報了上來。
長孫信端茶正飲,還未聽完,放下茶盞就走了出去“你說封山?”
驛丞恭謹答“正是,軍所下的令。”
長孫信那張清俊斯文的臉黑了一半“他們來的是誰?”
驛丞聲小了,瞧來竟有些畏懼“是咱們幽州的團練使。”
長孫信拍一下額,這麼大的事竟沒人告訴他。
他越過驛丞就去找神容,邊走邊腹誹那姓山的莫不是故意的,專挑他不在的時候出現!
神容今日起得很早。
一隻特製的厚紋錦袋放在桌上。紫瑞將紫檀木盒裡的那捲書小心取出,放錦袋,雙手送至跟前。
接了收進懷中,攏住上剛披上的一件水青織錦披風,走出門去。
東來瘦削筆直地站在門外,一護衛裝束已經穿戴整齊。
神容看他眼角傷已結痂消腫,問“你傷都好了?”
他垂首“養了幾日已無大礙,主放心。”
正說著,長孫信匆匆而至。
神容見他這般並不奇怪“想必哥哥已知曉那令了。”
長孫信本還想問那姓山的來後都做了什麼,此時一打量模樣,就猜到了的打算“你要親自去探地風?”
神容將披風兜帽罩上,想起了昨日山宗自跟前離去時的模樣,輕笑說“是,我要瞧瞧誰能我。再說了,你不是說此地首是刺史麼?”
長孫信頓時就懂意思了。
是要去破了那令,借的正是刺史那把力。
他打消了問起山宗的念頭,餘話不多說,說走就走。
小祖宗今日親自出馬,當然要陪到底。
隻在出發前,特地打發了個護衛去請幽州刺史。
Advertisement
……
東來引路,出城後車馬一路往西北方向快行。
從平整寬闊的直道轉上顛簸的小路,視線不再開闊,漸漸顯山嶺廓。
嶺尖起伏,恰如天公一筆水墨浸染在天際下方,滲往上,又連住了雲。
約有半個時辰,車馬俱停。
東來下馬來請神容“主,已經到了。”
神容揭開門簾往外看。
秋風瑟瑟,日上正空,四周崇山峻嶺環繞,到了那日在地圖上指出來的地方。
長孫信騎著馬過來“阿容,這一帶山脈廣袤,罕有人至,越過這崇山峻嶺便是邊境之外了。”
早在地圖上看到時神容就發現了,搭著紫瑞的手臂下了車“去看看。”
山道難行,隻能騎馬或步行。
神容將披風係,提了擺,領頭走在前麵。
東來怕有危險,數次想要走前方,但往往要停下尋路,最後還是走去前麵。
神容走得順暢,一步未停,不知的還以為曾經來過。
長孫信馬早不騎了,陪在左右,最終大家都是跟著在走。
下了山道,有一條淺淺的溪流。
神容看看左右的山,又看看那條水流,轉頭北,目一凝。
一道雄偉關城赫然橫臥盤踞其間,蔓延起伏,猶如長龍遊潛。
長孫信也看到了“原來距離關口不遠。”
神容卻在想難怪那日東來會被山宗拿住了。
想到這裡,連那潛龍似的關城也白了一眼。
關城之上,一隊人剛剛巡視到此。
胡十一手搭著前額往下,裡謔一聲“怎麼又是那金!”他扭頭看旁邊,“頭兒,看到沒有?”
山宗掀了下眼。
“就那兒!”胡十一生怕他看不見,還湊過來給他指方向。
那一群人就在這片山嶺之下,當中的年輕人一襲水青披風在風裡翻掀。
胡十一嘀咕“頭兒,你說咱這幾天是怎麼了,老著那金!他們到底乾什麼來了,還往這大山裡跑,當咱們令假的?”
山宗抱刀在臂彎裡,靠著城墻往下看,果然一眼看見長孫神容。
怪實在出挑,那一抹纖挑形,雪白的側臉,浸在日下都好似敷了層,如此奪目,想不看見也難。
然後他就見神容朝另一頭的關城角樓偏了下頭。
他目力極好,發現這模樣似是冷淡地飛了一記白眼。
怎麼著,關城惹了?
他好笑地揚了角,站直了,刀鞘在城墻上一敲“管他們乾什麼,直接轟走。”
胡十一聞言心頭一,這是讓他去轟?
別了吧,他可鬥不過那金。
山宗已轉往城下走,兩眼掃過關外,收回時又往長孫神容上掠了一眼,發現正在抬頭看山。
以前怎麼不知他的前妻還是個喜邊關山川的人。
剛下城頭,忽然一聲尖銳笛嘯自遠而來,突兀地刺耳中。
山宗腳步一收,下一瞬如影“快!”
一群人跟上他,飛撲上馬,疾馳而出。
這是斥候報信,有敵時才會發出。
神容站在溪水旁,也聽見了那陣聲音,轉頭看了一圈,卻被對麵山形吸引了注意。
看過兩眼後,開口說“土山。”
在長孫家的認知中,各山是有五行屬的。
對麵這山,山頂平而山方正,這在五行中屬土。
然而它綿延出去漫長的山脈,又暗含變化。
正是這些變化相生相剋相製相化,就了此地的地理。
所以要想找到礦,就要先掌握這裡的地理,這便是探地風。
長孫信在旁點頭“這我也看出來了,可還有別的?”
神容道“去跟前探探不就知道了。”
說話時腳已邁出去,霍然一道寒芒飛至,斜斜在前溪流中,兀自震不已。
愣住纔看清那是柄細長的直刀,愕然轉頭,一隊人馬橫沖而來。
為首的人黑縱馬,直奔而至,俯一把起刀“退後!”
聲還在,人已去。神容隻看見他回頭那迅速的一眼,眼底似淵,銳如割利刃,回過頭去時馬蹄飛踏,濺起沖天水花。
隻來得及閉眼,被徹頭徹尾濺了個滿。
“主!”
“阿容!”
東來和長孫信幾乎同時跑過來護,擋著連退數步,纔不至於後麵跟著的其他人馬也冒犯到。
後麵的胡十一還跟著喊了句“聽到了沒?快走!”
神容披風浸水,鬢發狼狽地在額前。秋風吹過,冷得渾輕,咬盯著那男人離去的方向。
他居然朝擲刀?
紫瑞已看呆了,反應過來後趕人生火。
長孫信快速解了自己披風換下神容那件的,東來為擋住風。
很快,神容被扶著坐去鋪上氈布的大石上烤火,周圍豎起了護衛砍來的幾樹枝,為拉扯上布簾遮擋。
對著火緩了緩,懷間,還好裝書卷的錦袋是特製的,雖不至於刀槍不,好歹能防些水火。
外麵長孫信在走低斥“這姓山的,簡直汙了自己世家貴族的出,目中無人,簡直就是個軍流氓!地……那個詞如何說的?”
東來低低提醒“地頭蛇。”
“對!地頭蛇!”
神容知道他是在給自己出氣,瞇眼看著眼前跳躍的火簇,著發冷的手指,心說他本就不是尋常世家子,外人哪裡知道他真正麵貌。
過了許久,那尖銳笛嘯沒再響起,倒來了一陣腳步聲。
接著是長孫信與來人互相見禮的聲音。
他人前習慣端著文雅的大族姿態,也不想妹妹方纔狼狽形被人知曉,罵山宗的樣子早藏起來了。
神容聽了出來,是幽州刺史趕到了。
幽州刺史剛至中年,白麪短須,穿著袍一幅溫和文士模樣,名喚趙進鐮。
他接了長孫信的邀請,領著兩個隨從就來了,自是知道為了令一事。
其實幽州地位特殊,乃國中上州,論銜他還比長孫信高一階,不過他是寒門科舉出,毫無背景,在長孫信麵前很客氣。
趙進鐮早看見布簾,其後若若現坐了個窈窕人影,也沒多在意,隻當是眷避諱。
他對長孫通道“令之事我已知曉。二位久居長安,怕是有所不知,幽州歷來要防範關外的奚和契丹二族,山使會有此令也是不得已為之,畢竟他還擔著軍責呢。”
神容想起了山宗自大鬍子手上接走的“貨”了,不就正是奚人與契丹人。
聽得出來,這位刺史在幫山宗說話。
想來他在這幽州緣還不錯了。
忽此時,馬蹄聲傳來。
簾外趙進鐮道“山使來了。”
神容手指著布簾揭開一角,往外看,先前對逞兇的男人回來了。
跟著他的人了一半,山宗勒馬在溪水對麵。
這頭趙進鐮喚他“崇君,來見過長孫侍郎。”
山宗卻沒“不想沖撞了各位,我就不過去了。”
他朝胡十一歪了下頭,一躍下馬,在溪邊蹲下,將直刀在側一,抄水洗手。
神容坐在溪水這頭,瞥見他手下順著水流漂來一一的紅。
崇君是他的表字,很久沒聽到這個稱呼了。
簾外胡十一來了跟前,在報“刺史大人來的巧,咱剛又抓了幾個來送的,人押去大獄了。”
趙進鐮道“山使辛苦了。”
神容看出來了,山宗在洗的是他沾上的跡。
這麼短的時間他就染了回來,這得下手多快?忍不住想。
眼看著他洗完了手又洗刀,然後收刀鞘,隨意往後一坐,直一條長。
趙進鐮似是對他這模樣習慣了,也不再他過來,回頭道“長孫侍郎如何說?”
長孫信問“這樣的賊你們抓起來難否?”
胡十一答“那有何難,咱們軍所可不是吃素的。”
長孫信等的就是他這句話“既然如此又有何可憂慮的?刺史莫要忘了,我等可是攜聖旨而來的。”
趙進鐮立即認同“自然不敢忘,我方纔問你如何說,正是想說我的提議。依我看,各位必須要山,山使也必須要封山,那不如就請各位在軍所保護下山,畢竟侍郎還帶著眷。”
長孫信不做聲了。
胡十一似不樂意,小聲哼唧了句什麼。
風吹布簾,其後忽而傳出人清越的聲音“敢問這軍所上下,何人手最好?”
趙進鐮聞聲,笑道“那自然是山使本人了。”
“這樣啊……”神容說“那不如就請山使親自來護可好?”
長孫信低呼一聲“阿容?”
胡十一也冒了個聲“啊?”
溪水那頭,山宗早已聽得一清二楚,他撐刀站起,向對麵。
那道布簾微微掀開,出人朝他來的雙眼,又一下拉上。
故意的。
他定有過人之
猜你喜歡
-
完結511 章

畫堂春:夫人,侯爺他又病了
生母死因成謎,昔日無憂無慮的嬌寵貴女身懷秘辛。她冷淡、睿智、步步為營,直到某個死乞白賴的人非要娶她為妻……“堂堂的靖海小侯爺?竟這般柔弱?”看著半倚靠在自己肩上的俊逸男子,江畫意忍不住抽了抽嘴角。“娘子出手,再無敵手,只可惜為夫體虛氣弱,不…
100.2萬字8 26724 -
完結417 章

黑月光她只想奪權
[穿越重生] 《黑月光她只想奪權》作者:元余【完結】 文案 施元夕在京中聲名狼藉。 因她曾不擇手段地為自己謀取了三段婚事。 為了攀龍附鳳,她機關算盡,從花名在外的浪蕩子,到身份尊貴的侯府世子,最后還險些搭上了朝中權臣。 可到底是登高跌重,三次謀算,三次落空。 一遭被退婚,淪為了全京城的笑柄。 家中實
65萬字8 2267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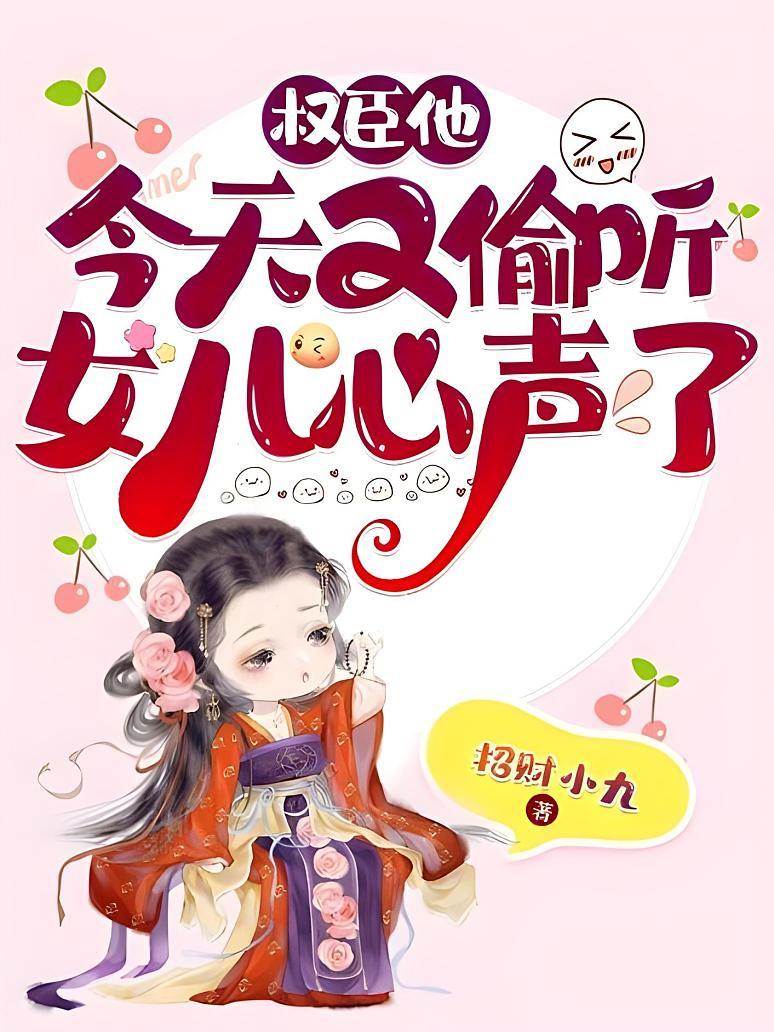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