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定有過人之處》 第二章
如今的國中,剛剛變了一番天。
先帝去冬駕崩,由他欽定的儲君繼了位。
這位新君登基不久,卻並不親近先帝手下重臣,甚至其中還陸續有人獲了罪。
長孫家世襲趙國公之位,自然也在這些重臣之列。
要命的是,先帝在世時,其家族還曾暗中參與過皇儲之爭,支援的是他人。
這事當時有可原,如今若被挖出來,那便是與新君作對了。
為世家大族,居安思危是立足之本。長孫家不能坐等秋後算賬,須得主扭轉局麵。
很快家族議定,一封奏摺上呈宮廷——
工部侍郎長孫信請求為聖人分憂,要為國中緩解近年邊疆戰事帶來的國庫虧空,特請旨外出,為國開山尋礦。
次日,聖旨下,準行。
於是長孫家有了這趟遠行。而這,便是長孫信口中說的要事。
神容再往車外出去時,離開那座道觀已有兩日。
車馬正行於一條茫茫直道上,前後都不見人煙,唯有他們隊伍行過帶出來的塵灰拖在隊尾,又被秋風吹散。
偏過頭問“到何了?”
守坐在車門外的紫瑞答“回主,早一個時辰前就聽郎君說已幽州地界了。”
正說著,長孫信從後方打馬過來了“那知觀說得不假,還真離得不遠,這不就到了。”他說著抬手往前一指。
神容順著方向去,遙遠橫擋著巍巍城門,連線城墻蜿蜒盤踞,如割開天地的一道屏障。
那頭早有一個護衛去城下探過,剛回來,向長孫信抱拳稟報,說城門眼下不開。
隻因一到秋冬季節幽州就加強戒嚴,每日都隻開幾個時辰的城門。
他們連日趕路太快,現在到得也早,要城門開還得再等上半個時辰。
長孫信聽了不免嘀咕那知觀又說對了,這還真不是個好地方,事多的很。
Advertisement
他想了想,朝車中喚道“阿容,不等城了,咱們便就此開始吧。”
神容朝他看去“這麼急?”
他溫聲笑“哪裡是急,我也是怕你趕路累了。早些開始,之後便也好你好生歇一歇了不是?”
神容一路上聽慣了這種好話,不置可否。
長孫信過窗格盯著瞧,馬騎得慢吞吞的。明明是他提的主意,卻反倒等開口決斷似的。
終於,點了下頭“那便開始吧。”
長孫信立即勒馬,擺擺手,眾人跟著停下。
“請卷。”
神容一聲喚,隊伍立時有了變化。
長孫信下了馬,站去車門邊,手一招,十幾名護衛近前,將馬車圍護在中間。
車隊後方,一名仆從取了水囊,仔仔細細澆一塊白帕,雙手捧著送過來。
紫瑞接了,擰乾,躬進車,跪呈過去。
神容起袖,接過帕子。
白的帕子覆在手上,包裹著纖長的手指,先左手,再右手,將十指細細拭了一遍。
而後放下帕子,出座旁的一隻暗格,揭開一塊薄錦,出一隻雕刻古樸紋樣的紫檀木盒。
正是先前一直抱在懷裡的那隻木盒。
神容端正跪坐,兩手平措至左前,右手左手,低頭,對著木盒行了大禮。
一旁紫瑞早已垂頭伏,不敢彈一下。
禮畢,神容坐正,捧出木盒置於膝前,開啟。
裡麵是厚厚的一捆卷軸書,以黃絹寫就。
小心展開,找到需要的那,停住,攤在膝頭細細閱覽。
無人打擾,就安安靜靜在車中看著這書卷,一邊看一邊沉思。
外麵眾人環護,雀無聲。
直到過了兩刻,頭頂日頭都升高了,才停下,將書卷小心捲起放回,蓋上木盒。
“地圖。”
紫瑞忙從懷中取出一份折疊的黃麻紙,攤開送至眼前。
是張手拓的幽州地圖。神容接過看了一圈,尤其在那邊角地帶,看了又看,最後出手指輕輕點了兩,抬頭問“東來呢?”
紫瑞轉頭揭簾出車“主傳東來。”
車外護衛中很快走出一名勁瘦年,快走兩步,跪在車邊“主。”
東來與紫瑞一樣,皆是追隨神容多年的侍從,主責人衛護。
神容隔著車簾吩咐“帶上幾人,照我在地圖上點出的地方去探一探,遇有山川河流,記下走勢流向就立即回來。”
東來領命,接了紫瑞遞出來的那張地圖,認真確認過地方,又向一旁長孫信拜過,招呼了幾人,離隊而去。
長孫信在車旁站到此時,才手揭了車簾往裡看“辛苦了,阿容。”
神容剛把木盒仔細放好,拿著帕子又了一回手“辛苦倒不至於,隻是比起以往要麻煩一些。”
他道“那哪能比,以往不過是在咱們自家采邑裡頭小打小鬧罷了,如今纔是要見真章的。”
神容嘆息“可不是麼,才探地風我就如此慎重了。”
長孫信聞言笑起來。
方纔那一番安排做探地風,若是想要找礦,這便是第一步。
以往在長孫家名下的采邑裡也發現過礦產,且皆為國之急需的銅鐵礦。
後來他們的父親趙國公長孫濟將礦產之事上奏宮廷,主給了朝廷。
雖說國律規定礦出皆為國有,可也規定國公高位有特權,凡出自名下采邑裡的礦產,可自采兩載以充府庫。
但長孫家偏就大公無私地了,且出的還不止一。
正因如此,其家族才能為先帝倚重的幾大世家之一,長孫信後來也得以年紀輕輕就被提拔進了工部。
當年先帝褒獎長孫家時,就連長安城中三歲小兒都會唱“長孫兒郎撼山川,發來金山獻聖王……”
人人都道這是他們長孫家命好,隻有長孫家的人自己明白,那是憑了他們自己的本事。
此事說來奇妙,長孫氏雖為貴胄之家,卻有項技能代代傳承,那便是對山川河澤的通。
若非如此,就沒那道主請纓的奏摺了。
然而此行如此大事,長孫信未帶其他幫手,卻獨獨帶上了神容。
隻因神容纔是他們長孫家最有造詣的。
便說剛剛翻閱的那盒中書卷,實乃他長孫家祖傳要,如今就傳到了的手上。
此行非同一般,也就非不可。
所以長孫信這一路的作為沒有毫誇張,他這個做哥哥的被底下人稱作郎君,卻能被稱一聲主,地位可見一斑。
就是個祖宗,長孫家人人寶貝的祖宗。
又一個護衛去城下探了路來,回報說時候到了,城門可算開了。
長孫信眾人各歸各位,回頭時繼續與妹妹說笑“說來也很久沒見你當眾請過捲了,我都忘了上回見這形是何時了。”
神容往後一倚“那是自然,這書卷我也封了許久了。”
長孫信並不知有過這一出,好奇道“何時封的?”
“婚時。”
的造詣對一個子而言,本沒有用武之地,婚嫁時自然要封起。
隻在如今不得不用的時候,才又派上了用場罷了。
長孫信一聽就無言,心說倒黴,怎麼又揭起這茬來?
當即轉換話頭“讓東來先探,咱們城去等。”
說完瞧見神容好像倚得不舒展,馬上吩咐紫瑞快去再取兩個墊來,好舒舒服服地城去。
神容什麼話也沒有。
所以說祖宗從沒自己要求過什麼,但有本事,大家偏就願意把供起來。
……
幽州號稱河朔雄渾之地,比不得東西二京繁華,但也不及各大邊疆都護府偏遠,自古地要沖,是防衛京畿腹地的一要道,更是北方一座重鎮商會。
比起蒼涼的城外,城中卻是相當喧鬧。
驛館,驛丞正在忙,忽聞外麵街上車馬聲沸,探頭一瞧,隻見不百姓都避在路邊,著脖子朝大街一頭著。
那所之,一隊高頭大馬的護衛引著輛華蓋寬車緩緩而來,最前方馬上之人乃一年輕貴公子,一錦溫雅之態。
他正思索這是哪來的顯貴,不知聽誰報了句“工部侍郎至”,驚得連忙就往外跑。
車馬剛停,驛丞已撲上前拜謁,眾館役也聞訊而,一通人仰馬翻,生怕怠慢了都城來的要員。
長孫信見怪不怪,下馬踱步進了驛館,左右看過一遍後道“我們隻在此暫居幾日,你們別的不用管,隻要能舍妹在此好生休息,不被打擾便好。”
驛丞躬跟著稱是,一邊在背後急切擺手,打發館役們去幫著卸車喂馬。
其實哪用得著他們做什麼,長孫信後隨從各司其職,早已了起來,甚至都已有人去接管了驛館的廚下。
所有吃喝用事,一概由他們長孫家的人自行料理伺候。
這是趙國公夫婦心疼出門太遠,怕不習慣,特地安排的。
長孫信自然照辦,這一路都是這麼過來的,力求此行在偏遠,如在故都,到回去時他妹妹就是瘦了一點半點都不行的。
神容在一片忙中下了車來,長孫信親自上前陪。
驛丞隻瞥見一抹罩在披風下的人影被護著款步而去,便知這位侍郎大人所言不是誇大,自是半分不敢懈怠。
隨即想起那院裡還有別人在,連忙趕過去安排,好給這位貴所居周圍留個清靜。
這一通忙完便到了午間。
神容確實趕路累了,在客房中用了一餐細佳肴、濃湯香茶的飯,疲乏上湧,便和躺下小歇片刻。
不知多久,外麵有吵鬧聲,翻了個,醒了,聽清那是一道嘎的男人聲音——
“什麼狗屁貴人,礙事得很,還要咱們給他們讓地兒!”
“哎呦天老爺,小聲點,那可是長安來的……”這是驛丞的聲音。
“了不起?這幽州地麵上,哥兒幾個隻認團練使,其他人都滾邊兒去提鞋!”
“行了行了,快別在這兒了!”
神容起下榻,過去一把推開窗,隻看見院角閃過幾道人影。
算他們跑得快。
止住腹誹,抬頭天,微雲若,日頭竟已偏斜。
東來這一去好幾個時辰了,居然還沒回來。
神容心想不該,他配有好馬,又隻是先行一探,怎會耗費這麼久?
門忽被敲響,紫瑞在外急急喚“主。”
神容回頭“進來。”
紫瑞推門而,屈一下就張口道“東來出事了。”
“什麼?”
紫瑞忙將事說明東來遲遲未回,便照往常一樣派人去接應,才得知他被一隊兵馬給扣下了。
話到此,有些憂慮“扣人的正要主家去贖人,可郎君安排好這裡就去城中署了,隻怕一時半會兒回不來。”
長孫信既然攜聖意而來,就肯定要去知會當地員,這是免不了的。
神容一手拉上窗,本也不想乾等著他去置。
“我去走一趟。”
他定有過人之
猜你喜歡
-
完結205 章

香妻如玉
凝香從冇想過自己會嫁給一個老男人。可她偏偏嫁了。嫁就嫁了吧,又偏偏遇上個俏郎君,凝香受不住俏郎君的引誘,於是甩了家裡的老男人,跟著俏郎君跑了。不料卻被老男人給抓了個現行!“你殺了我們吧!”凝香撲倒郎君身上,勇敢的望著老男人。老男人冇殺她,給了她一張和離書。然後,然後就悲劇了....俏郎君負心薄倖,主母欺辱,姨娘使壞,兜兜轉轉的一圈,凝香才發現,還是原來那個老男人好。突然有一天,凝香睜開眼睛,竟然回到了和老男人剛成親的時候。可這一切,還能重來嗎?--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42.4萬字8 11515 -
完結591 章

帶著千億物資穿成大奸臣的炮灰前妻
穿成大反派的作死前妻,應該刻薄親生兒女,孩子養成小反派,遭到大小反派的瘋狂報復,死后尸體都被扔去喂狼。 看到這劇情走向,俞妙云撂挑子不干了,她要自己獨美,和離! 手握千億物資空間,努力發家致富,只是看著這日益見大的肚子,俞妙云懵了,什麼時候懷上的? 不僅如此,大反派體貼化身寵妻狂魔,小反派乖巧懂事上進…… 這劇情人設怎麼不一樣?
103.7萬字8 99967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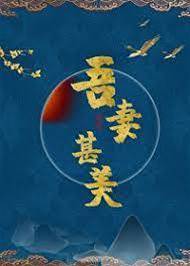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