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月無邊》 第5章 回洛陽
直到過了一會,郭允的聲音從前方傳來,“主公,大郎請人卜了卦,明後天或有雨,得從第五天開始,天才放晴,接下來的半個月天氣晴好,適宜出行。大郎還說,所有事他都會這四天理完畢,到時主公儘可以放心前往。”
劉疆低沉地問道:“他去不去?”
“大郎說,他不放心你和主母,自是會去。”
這話一出,劉疆有點惱,他沉沉地喝道:“胡說,我做事什麼時候到他不放心了?”
“大郎說,主公在這個時節前往,便是意氣之舉。”
這話噎住了劉疆。他重重的哼了一聲,這一哼,就把他的小兒子給震醒了。
果然那赴中所言,接下來兩天都有雨。而第五天,天空也確實大爲晴朗。
當下,早就做了準備的一家人,坐上馬車,朝著趕去。
此時已然冬深,一個不好,便會大雪封路。因此,這一路衆人直是快馬加鞭。
幸好,衆人運氣不錯,這般一路疾行,只是中間遇到了一場雨,天下了一點小雪,接下來都是沉沉的天氣爲主。雖然寒冷,卻不影響通行。
在新年將要近時,城的城門,出現在衆人視野中。
著那高大的,悉得不能再悉的城門,劉疆突然說道;“歇一晚,明天再進城。”他這話說得突然,而且明明城門就在眼前,只要努力一把,就可以趕在城門關閉之前進,可這個時候,劉疆卻說要在這荒野休息一晚。
好些人都看向做婦人打扮的盧縈和在劉疆面前最放鬆的郭允。
Advertisement
不過這兩人都是一陣沉默,因此。衆人不再多話地跳下馬車,開始準備紮營。
此刻夕西下,太的殘把霞雲染了金,整個大地蒼茫而又鮮亮。
劉疆負著手,靜靜地看著那遠的城門,他的影在夕下,有種說不出的孤寂。
盧縈抱起兒,緩步走到了他的後。
聽出的腳步聲,劉疆聲音沙啞地說道:“阿縈。”
“恩。”
他久久沒有說話,就在盧縈以爲他不會開口時。劉疆苦笑道:“我到了這裡,反而畏了。”
盧縈走到他邊,仰頭溫地看著他。低低地說道:“近鄉怯而已,這只是人之常。”
“是麼?”劉疆無聲的笑了笑。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低低地說道:“也不知他老了多……是不是瘦了?”
盧縈聽得出來,劉疆口中的他,便是他的父親劉秀。
知道。此刻的劉疆,只是想說說話,想跟人傾吐一番。所以沒有回話,只是靜靜地聽著。
劉疆又沉默了一會後,低聲道:“孩子們長這麼大了,他爺爺都沒有見過呢……要是他見到這三個孩子。一定會非常歡喜。”
盧縈直過了良久,才靜靜地說道:“對陛下而言,他子孫夠多了……歡不歡喜。實是難言。”
這話一出,劉疆閉上了雙眼。
良久良久,他才苦笑道:“可能是我,總是希他能歡喜。”說到這裡,他毅然轉。回頭看大眼骨碌碌。卻安靜地伏在母親懷裡一聲不吭的小兒,他出手抱著。低頭在兒的臉上親了親,劉疆聲音沙啞,“阿縈,幸好我還有你們。”
盧縈沒有回話。
這一晚,劉疆一直沒有睡著。盧縈擔心他,也一直在那裡裝睡。只是他一晚上翻了多次,嘆了多口氣,半夜起來多久,都一清二楚。
第二天轉眼就到了。
盧縈直到凌晨才睡去,整個人還迷迷糊糊之際,便聽到外面傳來了一陣歡笑聲。這些歡笑聲中,二兒子的鬧騰聲和小兒的格格笑聲最是響亮。
盧縈掙扎著爬起,喚過婢給自己梳洗過後,戴上紗帽便走了出去。
外面豔高照,一看到出來,二郎便跑了過來,笑嘻嘻地道:“母親,大夥都在等你用早餐呢。”
盧縈點了點頭,跟在他的後朝前走去。
這時,前方的道,傳來了一陣喧譁聲。
盧縈擡頭一看,只見一支百來人的隊伍也在朝城門方向駛來。那支隊伍很快便駛到了近前,看到正在用餐的盧縈等人,一個婦格格笑道:“咦,他們怎麼離城門這麼近還在野外紮營?”
也不知邊的人回答了什麼話,只見那婦了幾句,令得車隊停下後,的馬車直朝盧縈駛來。
不一會,那婦的馬車停了下來,掀開車簾好奇的朝著劉疆一家看了一眼。實在怪不得好奇,實在是這幾人全部都戴了紗帽,看起來怪怪的。
四下看了一眼後,盯向了明顯是主人的盧縈,笑道:“這位姐姐,是不是你們昨天來得太晚,到來時城門已然關閉?”不等盧縈迴答,繼續笑呵呵地說道:“前面就是城了,大家難得同路,一起進去吧?”
看到這人熱爽朗的笑容,盧縈一笑,回道:“既然夫人相邀,那就一道同行吧。”說罷,示意吃得差不多的衆人準備啓程。
那婦等了一會,在盧縈上了馬車後,的馬車靠了上來。出頭好奇地張了一眼盧縈的馬車裡面,扁了扁說道:“姐姐這馬車好普通。”
盧縈一笑,沒有回話。
這時,兩支車隊都上了道。兩隊都是百來人,這般混在一起,倒有了點聲勢。
越是靠近城門,那婦卻是安靜。目神往又說不出複雜地看著那高大的城門,直過了許久許久,才轉向盧縈說道:“我那夫君,他現在當大兒了……姐姐,我五年沒有見他了,這心裡慌的。”
盧縈看向,過了一會才說道:“自家夫君,慌什麼?”
婦勉強一笑,低聲道:“他新娶的二房妾室,那父母家世都與我相差不遠,人卻比我漂亮年輕許多。”說到這裡,似是有點失神,又怔怔地看向那高大的城牆,過了很久,盧縈才聽呢喃道:“當年新婚他就離開了,我也沒生個一兒半的。”說到這裡,看向盧縈,又看向不遠圍在劉疆馬車旁的兩個戴著紗帽的年郎,羨慕地說道:“如果我和姐姐一樣,也有二個兒子傍,便是這兒子醜一點笨一點,那也是好的。”
這些年盧縈在外四遊歷,這世間的恩怨悲歡見得太多,種種不幸或幸福,也見得太多。
看到婦那難的模樣,現在只想嘆息。
正在這時,婦先是一怔,轉眼雙眼瞪大,臉頰飛快地閃過一抹紅暈和難以言喻的歡喜張。盧縈一怔間,便聽到婦張地說道:“他來了……我夫君親自來迎接我了,真好,他親自來迎接我了……”話到最後,竟有了點哽咽。
盧縈擡頭看去。
只見前方出現了一支隊伍,一個腆著肚子,臉圓眼小的三十來歲男子,正帶著幾十人浩浩地從城門迎了過來。
衆人都走得快,轉眼間便匯合了。婦紅著臉迎上的夫君時,那男子嫌棄地看了一眼因張和喜而話也說不全的妻子,轉眼瞟向了盧縈等人。
見丈夫盯向盧縈,婦爲了找到話題,馬上樂呵呵地說道:“夫君,這位夫人是我在路上結識的,人可好著……”還沒有說完,那盯了盧縈的馬車和一行人的穿著打扮一眼的男子,便不耐煩地打斷的話頭,沒好氣地說道:“你別盡結識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你就是不聽。”一句話令得兩支隊伍的氣氛都有點僵後,他朝著妻子警告道:“呆會司馬大人的車駕會回,你到時給我安靜點。別嘰嘰歪歪讓人生厭。”然後,他又瞟了盧縈的車隊一眼,低語道:“還有,你是我的妻子,以後離這種寒酸商客遠一點。”(未完待續)
猜你喜歡
-
完結141 章

神醫娘親財迷寶
穿越被輕薄,搶了銀子帶球跑。 三年后短腿兒子揭皇榜,給親生父親治不舉。 他不舉?? 羅伊一表示可以試試讓他不舉。
34.5萬字8 10945 -
完結170 章

寵妻
一道聖旨,把尚書府的三小姐賜婚給端王做正妃,按說一個尚書之女能當上端王的正妃那還真是天大的恩寵,但是尚書府乃至整個京城都對這個聞所未聞的三小姐報以同情。 原因無他,傳聞端王兇狠殘暴,夜能止小兒啼哭,這還不算,更慘的是端王有個怪癖,那就是專吸少女之血,嚇死了好幾任端王正妃人選。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關鍵是現在端王已經臥病三個月,生死未卜,急需一個衝喜新娘。 這個人就是沈琪。
49.7萬字8.18 16975 -
完結108 章
望瑤臺
【文案】 楚懷嬋及笄那年,稀裏糊塗地被被一紙詔書指給了不良於行的西平侯世子。 傳聞那位世子四處留情,聲名狼藉,更欠了長公主獨女一樁風流債。 她想,也好,日後相看兩厭,樂得清靜。 卻不料,後來,她成了他珍之重之的心上明月。 孟璟這一生,有過年少時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的眾星拱月, 也有過後來雙腿被廢纏綿病榻、嚐遍世態炎涼的落魄之態。 他孑然一身,曆經百難,從深淵裏一步步爬起, 將自己脫胎換骨為一個無心人,對人情冷暖冷眼觀之。 卻不料,在這途中,摘到了一彎瑤臺月。
33.1萬字8 6660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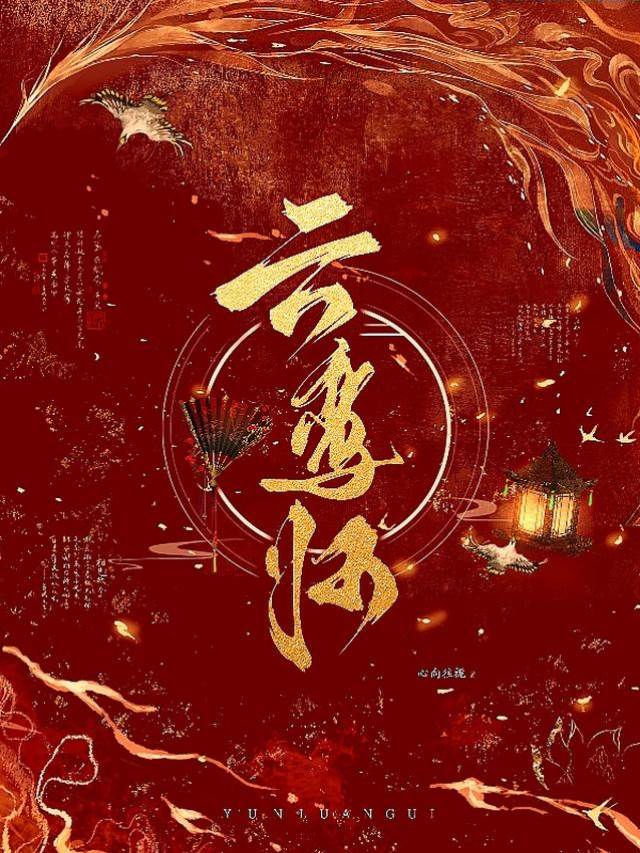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449 -
完結156 章

嫁首輔[重生]
虞雪憐原本是金陵城過得最風流快活的嬌貴女娘,然而在即將嫁爲人婦的時候,父親被處以極刑,風光幾十年的虞家也一朝落魄。 臨終前,她嚐盡了世間所有的苦楚,被仇家欺壓、被未婚夫羞辱。直到閉眼的那一刻,她總算鬆了一口氣—— 但願沒有來世。 可老天仍然是悲憫她的。 虞雪憐重生到芳華年月,孃親尚未病逝,父親尚是威風凜凜的鎮國大將軍。 虞家,還有得救。 前世吃了太多的教訓,虞雪憐把招惹的郎君全部拋棄,閉門在閨閣讀兵書,她要抓住陷害虞家的賊人。 敵在暗,她在明。 虞雪憐決定先找到當年負責處理父親叛亂一案的內閣首輔,陸雋。 她翻遍了整個金陵城,卻發現權傾朝野的首輔大人……正在一座大山的小村落,寒窗苦讀。 虞雪憐反覆捧讀《孫子兵法》,頓時心生一計。 - 花塢村最近熱鬧得不像話,陸家的倒黴書生陸雋要去做金龜婿了。 陸雋本人感到莫名其妙,荒唐之至。 那看起來神神祕祕的富貴姑娘天天給他送書送菜,臨走時還總說些讓人困惑的話: “陸雋,你要好好讀書,我相信你一定能金榜題名!” “陸雋,今日天寒,你別去客棧給人洗碗碟了。你教我寫詩作畫,我給你報酬,如何?” “陸雋、陸雋……” 虞雪憐自認爲有在堅持不懈地幫助陸雋,但萬萬沒想到,待陸雋金榜題名,待他如前世那般平步青雲—— 聘禮佔滿了虞府的正廳。 陸雋是如此求娶的:“虞姑娘對我的知遇之恩,陸某無以爲報,只好以身相許。” 在他貧瘠的、望不到光的夜晚,虞雪憐讓他嚐到了甘甜。 陸雋一直告誡自己,寒門子弟,勿要有奢求,勿要有貪念。 但看着洞房花燭下的嬌媚新妻,陸雋自嘲道:“貪點又何妨?”
24.4萬字8 64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