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嫁》 第47章
出了焦府,回到王府,一路進府裡,沒有遇見旁人,快到宅的時候卻和遠遠匆匆走來霍真到了一起,霍真遠遠看見匆匆走了過來:“嘿,我正說要到外書房去等你吶,正好遇上了,走,我帶你去見個人。”
霍真招呼了霍時英就走,霍時英只好打起神來跟上去問道:“誰啊?”
霍真回頭看一眼也沒有發現的異狀,只是道:“你還記得你在冀州的時候飛鴿傳書回來讓我給你找一個俞元皓的人嗎?找著了。”
霍時英的心口一痛,腳下頓住,霍真走出兩步才發現,轉回來問:“怎麼了?”
霍時英恍惚的問:“找到了?”
霍真定下腳步,看著道:“找到了,也虧得你說要找此人,他家原和你祖父是故,後來因爲牽扯到了一樁貪墨案,你祖父在邊關沒來的及施以援手,後來家裡就落寞了,家眷也被髮配,人也找不見了,說起來也是故人……”
霍真終於發現霍時英臉不對,停下問道:“可是有什麼緣故在裡面?”
霍時英沒有回答他,只是苦笑一下道:“你們是找不到元皓的。”霍真看著,霍時英眼裡一片黯然,他再也沒有問。
又往回走,出了月亮門,穿過中庭,來到外面的前廳,庭院外兩人緩緩走來,霍時英站在迴廊的影裡,夏夜的穿堂風吹得的衫獵獵作響,那是一對非常普通的母子,母親已過中年,布荊釵,形瘦弱,鬢間灰白,眼角脣邊皺紋深刻,滿面風霜但緩步行來,步履輕慢,眉目間帶有剛毅之,霍時英看見了的手,那是一雙常年艱苦勞作的手,瘦可見骨,皮乾枯上有細小的傷口,但指甲裡卻是乾乾淨淨的,這是一個曾經過良好的教養但又被艱辛的生活磨礪過的人。反觀那跟著的青年,弱冠之年,雖是一青布,但從頭到腳都是乾乾淨淨的,嶄新的千層底布鞋,白皙的皮,還有那雙毫無瑕疵的雙手。
Advertisement
兩人走到階下,雙雙向霍真彎腰行禮,母親腰雖彎下卻脊樑得筆直,兒子倒是把腰彎的很低,老老實實的很是恭敬樣子。
霍真兩步走下臺階,親手扶起二人說道:“大嫂快不必如此多禮,說起來我們兩家原是故,是我做的不好讓你們苦至今。”
子淡淡的說:“王爺不要這樣說,我家本就是戴罪之,怎敢怪罪王爺。”
霍真乾乾的笑了兩聲,回頭朝著影裡的霍時英道:“時英,過來見過俞大嫂,你小時候也見過的。”
三人皆轉向霍真看著的影,霍時英慢慢的走了出來,冰凍一樣的面孔,緩緩的走至正面的臺階上,居高臨下的著庭院中站著的兩人。
子帶著兒子屈膝行禮:“見過十一郡主。”霍真一臉尷尬,霍時英冷冷的看著,不出聲,最後還是霍真手把兩人扶了起來。
兩人起子一臉清冷,青年垂下頭去,霍時英慢慢走下臺階來到青年前,注視了他片刻開口道:“你是元皓?”
青年擡頭,彎腰作了一揖:“在下俞元皓。”
霍時英輕飄飄的說:“元皓死了,元奎。”
青年豁然擡頭眼裡一片驚愕,邊的子子晃了晃,霍時英又淡漠的道:“把你的手出來。”
青年有些呆滯,慢慢的把手了出來,霍時英低頭細看,果然細白無痕,唯一的一點瑕疵就是中指骨節間一點被筆磨出來的厚繭。
霍時英著青年問他:“你想要什麼?”
青年擡頭,一臉憤的向霍時英,霍時英冷漠的看著他道:“說吧你只有這次的機會,你要覺得辱,回頭再找我父親也是沒用,我答應你哥的事他說了不算,這是你哥哥用命換來的機會,這份屈辱你合該著。”
青年的眼中閃爍,臉上的表幾番變化最後一彎腰說道:“小生不求別的,只了奴籍能參加今年的鄉試。”
霍時英點頭:“可以,我贈你紋銀二百兩,若你鄉試得中來年春闈之前我再給你寫封信推薦你到到祿寺卿韓大人的門下。”
青年再次躬:“多謝郡主。”
霍時英從眼皮下看著他,看的青年忍不住拘謹的了腳,清淡的說:“我看你二十年後定是一方人。”青年擡頭,霍時英又道:“因爲你什麼都能捨得下。”說完轉就往裡走,一眼都沒看那在一旁的婦人。
穿過門廳,走過夾道,再踏上長長的迴廊,元皓啊,夜風裡,霍時英深呼吸,抑下心裡那尖銳的疼痛和酸楚。
他死了,在生命中最好的年華里,沒有人爲他流一滴眼淚,艱辛的母親,被犧牲掉的大兒子,冷漠的小兒子,能怪誰?有什麼立場去斥問他們。
元皓啊,霍時英長長的呼氣,呼出腔中的吶喊,因爲他死了,因爲他們從來沒有來得及,所以他永遠那麼純潔,如高嶺之上的一片雪花,冰冷而乾淨,瞬間即逝。
一滴水珠迎風而落,來不及細尋就已不見了蹤跡。
此後的一生霍時英再不曾見過俞家的人,二十年後,俞元奎的母親病逝,青州太守俞元奎一路扶棺回鄉安葬,守孝三年,至孝厚德被人傳頌,二十年後沒有人還記得俞元皓,俞元奎一生名聲顯赫,場風流但最終只拜青州太守,終生不得京。
接下來的日子沉靜了下來,裕王府大門閉概不迎外客,霍真閉門不出,霍時英也沒有出過門。
連著十幾日裕王府門庭蕭條,但府卻也沒冷清下來,霍真不見外客,但自己的兒子,兒,婿總是要見的,霍真共有十一個大小老婆,也正好有十一個孩子,當然不是正好一個老婆一個,除了王妃育有兩子以外一共還有庶出的四男五,除了霍時英是最小的一個外,其他的都出嫁或者分家單過去了。
五個兒三個遠嫁都不在京城,唯一留在京城的嫁給了老太太孃家一個分支的表兄家,剩下的幾個兒子霍真不管庶務,霍時嘉也沒有虧待他們,分家的時候分出去了半個王府的田產和進項,霍時嘉還託門路給五個兄弟中三個走蒙的路子,都某了一個閒差,剩下兩個也給他們多分了家產,有一份正經的營生。
按說霍真還活著霍時嘉就分了家,有些不合大家族的規矩,但霍時嘉分的公平,族裡的老人都知道他是明裡暗裡都是吃了虧的,所以這事也沒引起什麼風波。
從那天宮裡大宴之後,霍家在京的兒就都陸陸續續的回來了,今天這個明天那個拖家帶口的,始終沒有消停過,來了有要的,有哭窮的,還有給別人帶話的,霍真應酬了幾天,人被煩的不行,傷口也反反覆覆的老是長不好,最後乾脆帶著王妃躲到西山別院避暑去了。
霍真走之前也幹了幾件事,先是選了一個日子把月娘擡舉了,當晚二更霍時英親自把紅蓋頭的月娘送出了偏院,月娘從得了消息就嚎啕大哭了一場,臨出門時死死握著霍時英手,蓋頭下串的淚珠往下滾,霍時英目送一路上轎遠去,卻始終找不出一句能囑咐的話,覺得有些惆悵,也覺得就這樣吧,也算是最終有了一個自己合理的位置了,這麼安自己的同時,心裡卻又始終哽咽著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
擡舉了月娘轉天霍真就把他那些原來的十個老婆全都移了院子,王府東邊有一個大花園,和王府正堂這邊有一牆之隔,裡面亭臺樓閣,風景優,院落寬廣,住百十來個人都不問題,地方其實不錯,霍真把他的小老婆全都趕到裡面去住了,雖然一切供應照舊但也算是打冷宮了。
剩下的在外面的老婆就一個王妃和月娘了,月娘也被分了一個院子,在王府的西南角,遠離了錦繡堂和榮裝堂,也算是個偏院罷了。
接下來霍真就開始催著霍時英選院子搬出去,霍時英到外院挑了霍時嘉沒有婚之前住的秋棠院,院子裡因爲有兩棵秋海棠而得名,霍時英挑了這裡也是因爲這院子一直有人打理,直接搬進來就能住,方便,搬家那天龔氏送過來四個大丫鬟,其中一個就是原來伺候過霍時英也是龔氏陪嫁過來的懷秀,霍時英當天也給小六賜了名:懷安。一個懷秀一個懷安其實是霍時英懶來著。
府裡被霍真大刀闊斧這麼一收拾倒是也清明瞭,至格局是分明後,那些鬼鬼魅魅的事有心人要施展也了空間。等一切都安頓完了,霍真就拍拍屁走了,霍府這纔算是真正的清淨了下來。
霍真安排完放心的走了,霍家一切外事宜都在平穩中等待著過度。只是霍家人誰也沒有想到,接下來不過三日的功夫朝堂上忽然出現了一連串地山搖的事,京中朝局出現了一次大的地震,整個京城權貴都被牽扯其中,霍府了風暴的中心也是人心盪。
這一年的六月,剛一過了初八伏這一天就天氣陡然變熱,直到十五這一天氣溫一直在節節攀升,連著一月不見雨水下來,京城中有了不中了暑熱的人,二伏這一天早起就豔高照,朝堂上的一封奏摺把這種炎熱推向了最。
猜你喜歡
-
完結810 章
鳳謀天下:王爺為我造反了
「我雲傾挽發誓,有朝一日,定讓那些負我的,欺我的,辱我的,踐踏我的,淩虐我的人付出血的代價!」前世,她一身醫術生死人肉白骨,懸壺濟世安天下,可那些曾得她恩惠的,最後皆選擇了欺辱她,背叛她,淩虐她,殺害她!睜眼重回十七歲,前世神醫化身鐵血修羅,心狠手辣名滿天下。為報仇雪恨,她孤身潛回死亡之地,步步為謀扶植反派大boss。誰料,卻被反派強寵措手不及!雲傾挽:「我隻是隨手滅蟲殺害,王爺不必記在心上。」司徒霆:「那怎麼能行,本王乃性情中人,姑娘大恩無以為報,本王隻能以身相許!」
150.5萬字8 82602 -
完結1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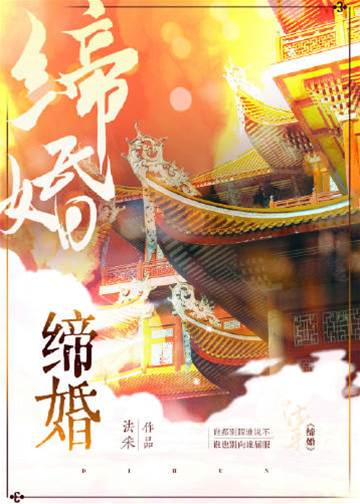
締婚
家敗落之後,項家老爹成了人人喊打的奸佞,項宜帶著幼年的弟妹無依無靠、度日艱難。 她尋來舊日與世家大族譚氏的宗子、譚廷的婚約,親自登了譚家的門。 此事一出,無人不嘲諷項家女為了算計、攀附譚家,連臉面都不要了。 連弟弟妹妹都勸她算了,就算嫁進了譚家,...
45萬字8.33 82137 -
完結136 章

重生之窈窈再愛我一次
謝令窈與江時祁十年結發夫妻,從相敬如賓到相看兩厭只用了三年,剩下七年只剩下無盡的冷漠與無視。在經歷了丈夫的背叛、兒子的疏離、婆母的苛待、忠仆的死亡后,她心如死灰,任由一汪池水帶走了自己的性命。 不想再次醒來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七歲還未來得及嫁給江時祁的那年,既然上天重新給了她一次機會,她定要選擇一條不一樣的路,不去與江時祁做兩世的怨偶! 可重來一次,她發現有好些事與她記憶中的仿佛不一樣,她以為厭她怨她的男人似乎愛她入骨。 PS:前世不長嘴的兩人,今生渾身都是嘴。
27.1萬字8 266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