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原諒,不復合,蘇小姐獨美》 第1卷 第882章 全是和睡覺相關
這聲“阿槿”,奧利弗說的是中文。
“……好,謝……謝。”
“你不用跟我說謝。”奧利弗手足無措。
桑槿卻微微一笑。
是個漂亮的姑娘,即便臉上還有可怖的傷痕,但當眉眼彎彎的時候,依然能看出那種從骨子里散發出的麗與優雅。
奧利弗瞬間心跳加速。
……
“雨眠——”
沈時宴住。
蘇雨眠下意識回頭:“哥?”
“去哪?”
“我去看看邵溫白。”
男人默然一瞬,才重新開口:“……明天我就走了,醫療隊留在島上給你用,不需要的時候再聯系鄧偉,他會上島接人離開。”
“船上的藥品我讓他們都搬下來放到儲藏室了,理論上來說是夠的,但不排除特殊況。總之,缺了什麼,給我打電話,我讓人及時送來。”
“……好。謝謝哥。”
沈時宴角上揚,眉目舒展:“你都我哥了,說什麼謝?我們之間不必如此……見外。”
……
中午,蘇雨眠去了工作區。
工作還是要繼續的。
考慮到大家心都到不同程度的傷害,蘇雨眠給大伙兒放了三天假。
三天后,覺得沒有大礙的人,可以先開始工作。
那些傷得比較重的、沒辦法工作的,可以繼續休息。
好在,三天后,大部分人都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崗位。
Advertisement
數幾個行不便或是康復況不佳的,則繼續接治療。
下午的太斜掛在天邊,灑下耀眼的金芒。
金鋪在海面上,隨著浪濤波涌,被切割得粼粼生漪。
一扇靠海的窗戶,往里看去,只見一個男人靠坐在床頭,手里拿著一本理領域的專業書籍,正低頭翻看。
從窗戶逃進去,在地面投下一片明亮的斑。
沈時宴推門進來。
邵溫白聽見靜,從書籍中抬首,朝他去。
“沈總來探病?”
“嗯,”沈時宴點頭,“看你死了沒有。”
“那真是不好意思,要讓你失了。”
沈時宴走到床邊,掃過他現在的境——
簡陋的室、陳舊的木床,墊在腰后的枕頭也灰撲撲的,本該是狼狽的場面,他卻安之若素地拿著一本書在看。
眉眼平和,神泰然。
“還有心看書?邵教授可真是……不慌不忙。”
是因為穩勝券嗎?沈時宴目中閃過自嘲。
邵溫白笑著回他:“既然慌慌張張沒用,那不如不慌不忙。至于看書……打發時間罷了,等雨眠過來,我就不看了。”
沈時宴聽他提起蘇雨眠,突然笑了一下:“雨眠過來,應該也要等工作結束之后了吧?就是這樣,工作永遠排第一,其他人和事都要靠邊站。”
“嗯,我就喜歡專注工作的樣子,很。”邵溫白說著,眼中漾開笑意。
似春水泛起漣漪。
沈時宴不笑了,可能是生就不笑。
“你打算在島上待多久?”
邵溫白實話實說:“我這次來,短時間沒想過要走。留多久,我就待多久。”
沈時宴忽然覺得很荒謬:“你以什麼份待在這里?雨眠是來讀博學習,不是跟你談說。”
邵溫白語氣淡淡:“這就不勞沈總心,我自有打算。”
他這副樣子真的很氣人,沈時宴頓覺心梗。
突然,他好似想起什麼,緩緩開口——
“我很好奇,邵教授之前信誓旦旦的‘復合’,了嗎?”
“……”
“哦,原來沒。”
“……”
沈時宴終于占了一回上風,瞬間心愉悅。
他看了眼兀自垂眸、沉默不語的邵溫白,“……我明天要走了。”
邵溫白唰一下抬頭。
沈時宴:“你這什麼眼神?”
邵溫白:“有點不太敢信。”
沈時宴被他的“直言不諱”氣笑:“你以為我想走?要不是墨爾本還有一大堆事要理……我恨不得天天守在雨眠邊,寸步不離。”
“你知道的,這沒可能。我都不一定能做到,至于你……還是算了吧。”
不是邵溫白鄙視他,而是蘇雨眠就不是那種需要人陪的孩兒,只會嫌麻煩和礙手礙腳。
沈時宴:“喂,你說話客氣點。”
雖然這是事實……
邵溫白:“你今天來,是跟我道別的?”
沈時宴:“主要還是看你死了沒。”
邵溫白:“……”
“放心,我一定長命百歲,不給你丁點兒機會。”
“……”
沈時宴走了,仿佛真的只是來探個病、道個別。
……
第二天清晨,蘇雨眠送沈時宴、鄧偉一行到海邊。
鄧偉幾人先上船,沈時宴站在岸邊,看著蘇雨眠。
“哥,你是不是有話想說?”
“嗯。”男人點頭,看的目帶著笑意,而笑意之下藏著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不舍與留。
他說,“雨眠,別輕易原諒他。”
蘇雨眠愣住。
沈時宴卻不再看的反應,而是果斷轉,朝船上走去。
……
回到基地,迎面撞上錢海峰——
“雨眠,沈總走了?”
“嗯。”
“哦,對了,我剛盤完儲藏室的藥品,發現又多了一批管控藥,沈總真是太周到了!這次也多虧有他,否則,我們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蘇雨眠照例去房間探桑槿,結果卻被告知——
“奧利弗推去海邊曬太了。”
蘇雨眠有些驚訝:“現在能下床嗎?”
“可以。醫生建議多出門,到看看,但不是很愿意出去。”
所以前幾天才一直悶在房間。
“那奧利弗怎麼說的?”
男人額頭上頓時青筋猛跳,表像遇到了什麼難以接的事,無語又迷:
“桑槿不出去,他就蹲在床邊哭,一直哭。”
蘇雨眠:“……”
不過桑槿愿意出門,終歸是件好事。
離開桑槿房間,蘇雨眠去看邵溫白。
后者仿佛知道要來,沒等蘇雨眠進門或是發出什麼響,他便似有所覺般,抬頭看過來。
四目相對,男人角率先揚起笑容。
“眠眠,你來了……”
蘇雨眠反應過來,收回視線,進門走到床前:“你……今天覺怎麼樣?”
“好的。就是……”
“?”
邵溫白認真道:“晚上睡覺的時候,你沒在邊,很難睡著。”
“??”
“今天能留下來嗎?就像那晚一樣,我保證只睡覺,其他的什麼也不干。”
男人表專注,語氣真誠,那副樣子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在邀請蘇雨眠合作什麼了不得的課題。
結果……
課題沒有,全是和睡覺相關。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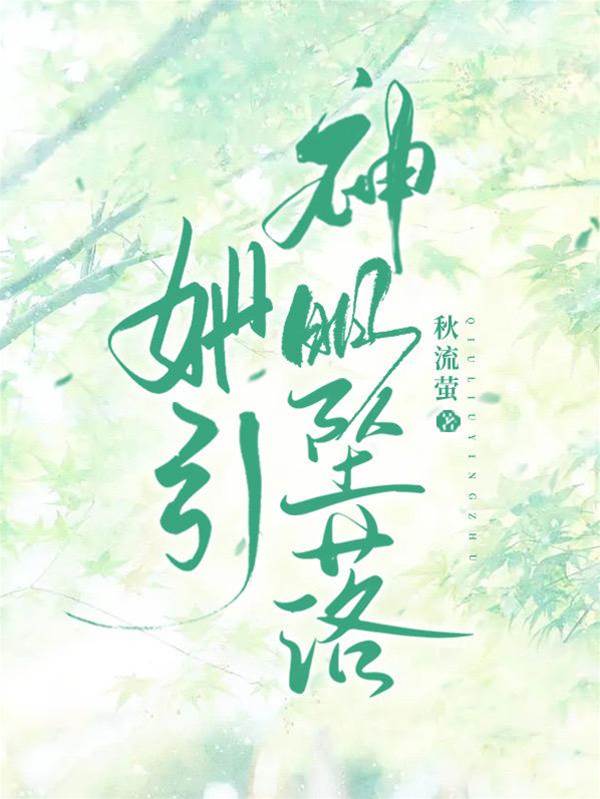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6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