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山喧》 第1卷 第145章 她的名字
酒店窗簾的遮效果很好,日夜的界線被徹底模糊,本看不出來現在的時間。
溫晚凝也不知道自己這一覺睡了有多久,只記得自己臨睡前最后看表時,都已經快五點了。
中間好像還迷迷糊糊醒了好幾次。
一是因為本來就不清醒,二是因為被折騰狠了,徹底站上了道德制高點,從小的作本盡顯。
毫不顧慮對方是夢是醒,王姿態地發號施令,了要喂水,腰酸要肚子。
未料到,睜開眼隨便,連到都膩膩的床單都被換過了。
臉稍微偏向另一側。
皺的子也已經疊好,和凌野白天時穿的衛長一起,整齊疊放在床頭。
凌野正在淺眠,呼吸聲平穩,始終將抱在懷里。
溫晚凝下意識地了,還沒等掙,對方就將手臂了,下頜著的頭發輕蹭,“姐姐醒了?”
他剛起床的聲線低啞,帶了些平常很見的懶洋洋意味。
溫晚凝輕嗯了聲,“你什麼時候回隊?”
凌野的腰向后撤一撤,“這兩天都請假了,不急著走。”
兩人還是第一次如此親近。
剛剛還好,現在凌野一醒,那種強烈到無法忽視的存在就翻倍地往上漲。
宿醉勁兒一過,許多七八糟的高清回憶重新浮現在腦海,溫晚凝臉上泛熱,努力地把那恥下去,“現在幾點了?”
Advertisement
本來想轉面對他。
結果剛了一下腰,就不知牽扯到哪里,全地酸麻,不由得倒吸了口氣。
耳垂瞬間紅了,要不是有頭發做遮掩,現在絕對已經面全無。
而凌野卻沒想這麼多。
利落地翻坐起,結實寬肩彎到這一側,擔心地觀察表,“不是說不疼嗎?”
閱讀燈被擰亮,暖黃的暈撒在他上,將男人肩頭那幾道細長的抓痕照得清清楚楚。
溫晚凝臉都要紅炸了,“能不能閉。”
凌野線抿高,垂眼看,“我看看。”
“看你個頭。”
溫晚凝從被子里出手,虛張聲勢地開他朗的下頜,有氣無力,“我了。”
“幫我個客房服務,別說話,做姐姐乖乖的啞夫,用號碼鍵輸。”
說完就閉了眼,半邊泛的臉被子里,堂而皇之裝睡。
凌野手臂撐在臉邊,反復地瞧著,對這些氣的小作看得目不轉睛,滿腔的意像是要溢出來。
那只細白的手早就落了回去,他又忍不住捧起來,在自己臉上蹭蹭,從掌親到指尖,最后又留地咬一咬。
溫晚凝要被他這個黏人的樣子麻死,但也下不了狠心趕他,只很輕地把手揚起來,在他英俊側臉上拍拍,“快去,先洗個澡再去也行,好凌野。”
浴室里很快傳來淅淅瀝瀝的聲響。
溫晚凝終于可以獨占整張床,費勁地翻轉過來,將整個酸的攤平。
倒真的沒怎麼疼。
喜歡是最強效的止痛劑,更何況,凌野對的癡迷在這種時候也不遑多讓。
只是稍微泄出了一點氣聲,他就直接俯跪了下來。
在鋪著迪士尼絨小地毯的床頭。
就像之前在東北錄節目傷那次一樣,鄭重地單膝跪在面前,冷峻的臉上全是認真,研究著該怎麼架起的,才能讓快一點離疼痛。
而不同的是,上次擔在膝彎的虎口和掌心,這次置于別。
像是最細貴的儀表盤,需要他用盡耐心和溫存,才能在連綿加劇的雨中主宰速度。
直到最后雨勢淋漓時,更需要當機立斷,握住試圖蜷的腳踝,拖回自己的邊。
但件條件放在這里,就算是準備活做得太充分,也難免會吃點苦頭。
一方面是十幾年的長跑習慣給了凌野太好的耐力,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平常的語言習慣素來直接,就算在這樣的時刻也不知收斂。
當因為全然習慣不了,也無法適應那種咬著脖子的暴力攻勢而喊他名字的時候,對方也始終不為所。
只是將的手輕輕帶到被撞到酸麻的小腹上,用力。
上頭了似的,低低地“嗯”一聲應著,“我在這。”
一向自詡年后沒哭過,也不知道為什麼一上凌野,就有這麼多的眼淚。
也許是純粹生理的,也許是被哭的。
但是一向最見不得難過的凌野卻像變了一個人,睫掛滿淚滴的樣子,像是了他潛意識深的什麼興神經。
只需要稍微看一眼,他的呼吸就會一點點變沉,抑制不住地捧起的下,重著湊過來的眼睛。
真的要瘋了。
只是稍微回想一下,溫晚凝就又覺得自己好像被那窒息勁兒纏住,渾都熱熱的不自在。
門外浴室的聲音不知什麼時候停了,電話座機被很輕地拿起,之后又放下。
把手輕響,凌野推門進來。
他沒穿酒店的浴袍,只用浴巾裹在腰間,赤著壯的上半。
剛走到溫晚凝這邊,正想低頭吻,就被輕輕推了一下。
凌野很輕地挑眉,神不解。
因為開了燈,昨晚沒看清的一切都袒于線之下,溫晚凝的注意力全被凌野腰側那個紋引走了。
黑線條,沒有任何花紋,長的一道鋸齒形。
位置不偏不倚,正好卡在實的鯊魚上,很惹眼。
不僅是紋,在他每一站F1分站大獎賽的頭盔上也有,甚至連阮佳手上的梅奔車隊聯名款手鏈也出現過這個圖案。
早就想問了,只不過到了今天才有機會,“你的紋是什麼意思?”
凌野沒立刻回答。
他濃長的睫垂了垂,才低聲道,“溫晚凝。”
溫晚凝茫然仰頭。
只以為是在突然名字,沒反應過來。
凌野頓了幾秒,好像也有幾分不自在,“你名字的寫。”
“小時候炸車禍,有一塊鋼板碎片進了側腹,留了很長的一道疤,后來遇見了你。”
后來遇見了,就把的名字紋在了傷疤上。
大寫的WWN。
這是他的合線。
猜你喜歡
-
完結86 章

不見面的男朋友
謝桃交了一個男朋友。他們從未見面。他會給她寄來很多東西,她從沒吃過的零食,一看就很貴的金銀首飾,初雪釀成的酒,梅花露水煮過的茶,還有她從未讀過的志怪趣書。她可以想象,他的生活該是怎樣的如(老)詩(干)如(部)畫。因為他,謝桃的生活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不用再打好幾份工,因為他說不允許。她的生活也不再拮據,因為他總是送來真金白銀。可她并不知道,她發給他的每一條微信,都會轉化成封好的信件,送去另一個時空。
33.7萬字8.18 24275 -
完結493 章

重生歸來,家里戶口本死絕了
前世,顏夏和顧家養女一起被綁架。無論是親生父母、五個親哥哥,還是青梅竹馬的男朋友,都選了先救養女,顏夏被撕票而死。重生歸來,和父母、渣哥斷絕關系,和青梅竹馬男朋友分手,她不伺候了。為了活命,她不得不卷遍娛樂圈。大哥是娛樂圈霸總。轉眼親妹妹開的明星工作室,居然變成了業內第一。二哥是金牌經紀人。轉眼親妹妹成了圈內的王牌經紀人。三哥是超人氣實力派歌星。轉眼親妹妹一首歌紅爆天際。四哥是知名新銳天才導演。轉眼親妹妹拍的電影票房讓他羨慕仰望。五哥是頂流小鮮肉。轉眼...
89.8萬字8.5 160248 -
完結244 章

一眼著迷
五歲那年,許織夏被遺棄在荒廢的街巷。 少年校服外套甩肩,手揣着兜路過,她怯怯扯住他,鼻音稚嫩:“哥哥,我能不能跟你回家……” 少年嗤笑:“哪兒來的小騙子?” 那天起,紀淮周多了個粉雕玉琢的妹妹。 小女孩兒溫順懂事,小尾巴似的走哪跟哪,叫起哥哥甜得像含着口蜜漿。 衆人眼看着紀家那不着調的兒子開始每天接送小姑娘上學放學,給她拎書包,排隊買糖畫,犯錯捨不得兇,還要哄她不哭。 小弟們:老大迷途知返成妹控? 十三年過去,紀淮周已是蜚聲業界的紀先生,而當初撿到的小女孩也長大,成了舞蹈學院膚白貌美的校花。 人都是貪心的,總不滿於現狀。 就像許織夏懷揣着暗戀的禁忌和背德,不再甘心只是他的妹妹。 她的告白模棱兩可,一段冗長安靜後,紀淮周當聽不懂,若無其事笑:“我們織夏長大了,都不愛叫哥哥了。” 許織夏心灰意冷,遠去國外唸書四年。 再重逢,紀淮周目睹她身邊的追求者一個接着一個,他煩躁地扯鬆領帶,心底莫名鬱着一口氣。 不做人後的某天。 陽臺水池,紀淮周叼着煙,親手在洗一條沾了不明污穢的白色舞裙。 許織夏雙腿懸空坐在洗衣臺上,咬着牛奶吸管,面頰潮紅,身上垮着男人的襯衫。 “吃我的穿我的,還要跟別人談戀愛,白疼你這麼多年。”某人突然一句秋後算賬。 許織夏心虛低頭,輕踢一下他:“快洗,明天要穿的……”
36.7萬字8 11823 -
連載332 章

禁止離婚!傅先生強寵小甜妻
認識不到兩小時,姜蔓便和傅政延領證結婚。 她爲了臨時找個地方住,他爲了應付家族聯姻。 婚後,姜蔓一心搞事業,努力賺錢,想早點買房離婚搬出去, 然而,傅先生卻對這小妻子寵上癮了, “老婆,禁止離婚!“ “我不耽誤你搞事業,你上班的時候,還可以順便搞一搞我~” 姜蔓這才知道,原來自己的閃婚老公,竟是公司的頂級大老闆! 公司傳聞:傅總裁寵妻無度,和太太天天在辦公室搞甜蜜小情趣~
58.4萬字8 3247 -
完結2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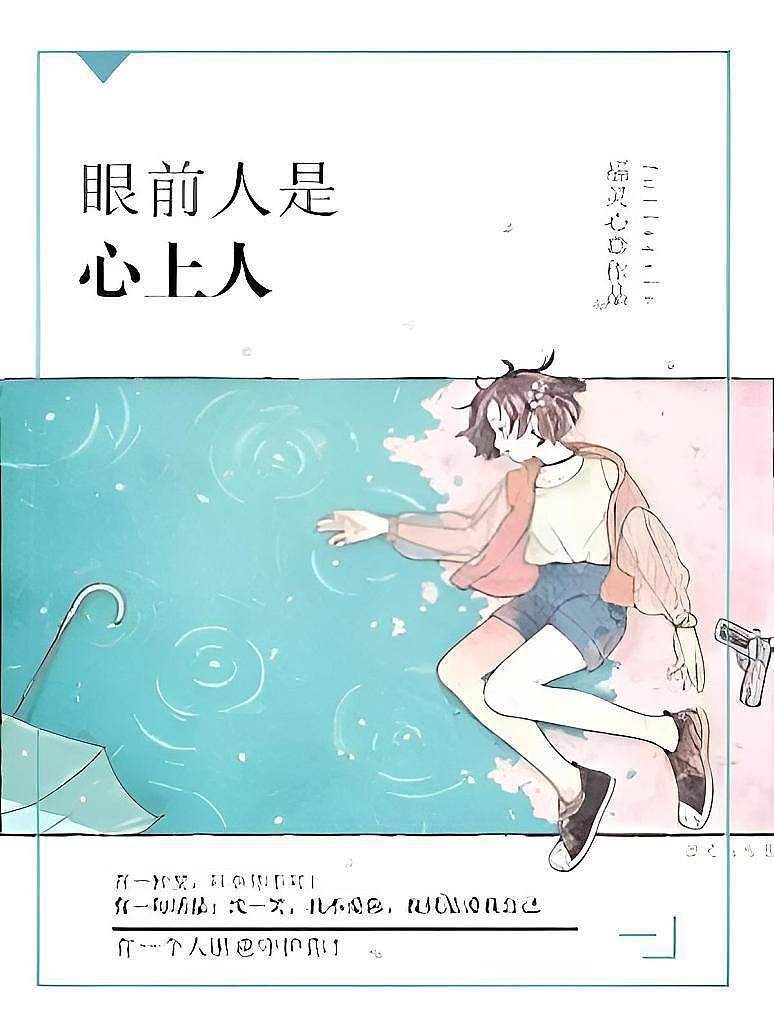
眼前人是心上人
巫名這兩個字,對于沈一笑來說,就是掃把星的代名詞。 第一次她不走運,被掃把星的尾巴碰到,所以她在高考之后,毫不猶豫的選擇了離開。 卻沒想到,這掃把星還有定位功能,竟然跟著她來到了龍城! 本來就是浮萍一般的人,好不容易落地生根,她不想逃了! 她倒要看看,這掃把星能把她怎麼著。 然而這次她還是失算了。 因為這次,掃把星想要她整個人……
25.9萬字8 1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