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失格》 第78章 番外·甜蜜日常
桑暮的被兩條健壯的手臂摟抱住,上覆上來軀。
其實早在桑暮出現在房間的那刻,就已經功了。
邢舟看著坐在床上打瞌睡的那個姑娘,心裏的悶氣消得一幹二淨。
至于方才不練的那幾次主,算是徹底攻破防線。明明喝酒的那個不是邢舟,他卻覺得自己醉得比桑暮還厲害。
他伏在桑暮上,十指牢牢蹭掌心。
全像是在酒水裏泡過,又被火星燎了大半。
夜裏,男人的目燙得如同火,躺在那裏的桑暮卻沒察覺到危險。
“你幹嘛…”桑暮不老實地了,不小心蹭到邢舟的大。
空氣裏響起聲沉啞的低哼。
原本不想承認的事,到了此刻也都不管不顧了。邢舟嚨滾了滾,視線鎖著桑暮染了幾分醉態的臉,“老子就是吃醋了。”
聞言,桑暮像是沒辦法了,哭喪著臉,“那你說怎麽辦,哄又哄不好…”
剛才這麽一折騰,桑暮的頭發淩,短袖領口歪了點,出小片雪白的。眼尾有點,卷翹的的睫下是雙略顯迷離的瞳孔。
再往下,紅潤。
邢舟俯過去,“親我。”
“剛才親過了,沒用。”桑暮認真地給他講自己的失敗史,“親了好幾下都沒用。”
“……”
“有用。”邢舟耐心道:“久一點就有用了。”
桑暮沒信,“誰告訴你的?我不信。”
“……”
“邢舟告訴我的。”
桑暮口而出,“邢舟是誰?”
Advertisement
還沒等邢舟發作,桑暮自問自答。
“哦。”突然小聲笑了笑,“我男朋友。”
醉酒的小兔子還能認得清人,沒白疼。
“那還哄不哄了?”邢舟的手指。
小兔子點頭,“哄。”
雙上,桑暮費力地仰著脖子,聽著方才邢舟的引導,更久地吮吻過去。上廝磨,不小心到口中,又條件反地了回來。
最先引導的那個到底還是沒忍住。
遲緩清淺的嘗試被打破,邢舟下去,用力吻住。
腰被托抱住,邢舟把桑暮往自己這邊按,舌頭掃著口腔的每一,肆無忌憚地侵占。
口津相渡,曖昧的聲響溢滿整個屋子。
的吻順著耳後往下,擺到了鎖骨的位置。著有些刺的寸頭刮蹭著桑暮的頸窩,讓不自覺地往旁邊躲。
空氣微涼,白皚皚的霜雪在摧殘中戰栗。好看的梅子握在掌心,又生生吞。
桑暮抱著邢舟的頭,腳跟著床單蹭。像被水浪沖打著,讓人頭暈目眩。
“邢舟…”桑暮的聲音已經發了,“你在幹嘛?”
的可憐的布料從彎下來,邢舟的手覆上去,“做能讓暮暮舒服的事。”
或許是真的被他這話吸引到,桑暮摟住他的脖子,笑盈盈說好。
說是哄人,到最後也不知道是誰哄誰。
這姑娘還醉著,邢舟不想這個時候對做些什麽。他摟著桑暮微的,用紙巾拭的手指。
可長夜還未結束。
桑暮主抱上邢舟的脖子的時候,強下去的那沖又來了。
上的已經變得褶皺不堪,桑暮的手還迷迷糊糊地。
覺到舒適,于是下意識留,桑暮裏嘟嘟囔囔的,“我不要睡覺…”
電流穿過般的麻從尾椎湧上來,邢舟嚨發,“暮暮——”
他強拉下桑暮的手,一只手掌箍住兩條細瘦的手腕往上推,翻過去,眸中的.態幾乎要溢出來,“不想睡覺是吧。”
“行。”
僅剩的幾件也沒了。
膝窩到大後側的位置被人按著,面向腹部。桑暮的頭頂幾次要磕到床頭,又被生拉拽回來。
汗水滴落在鎖骨窩上,順著平流向壑。
“暮暮。”邢舟的名字,語氣微,“說,你最喜歡邢舟。”
混沌裏的桑暮不明白他的意思。
邢舟很有耐心,低頭吻,重複了遍,“暮暮,說一聲。”
頭差點又磕到。
到威脅,桑暮本能地要阻止危險,不得已終于開了口,“最…最喜歡邢舟。”
“誰?誰最喜歡邢舟?”
“我,我喜歡…”
話落,這回是真磕上去了,不過用邢舟的手掌做了墊。
半夜三更,桑暮終于得以趴在枕頭上。可是沒幾分鐘,腰突然被人抱住,接著騰空,整個人直接掛在邢舟上。
就那樣,繼續。
邢舟抱著,走到臥室門口,關上大開的門。
前段時間,想著桑暮會偶爾過來留宿,邢舟買了個全穿鏡,就放在窗邊。
他托抱著桑暮到鏡子前,兩個人糾纏的模樣清晰可見。
彎掛著腰,腳背無力低垂。
桑暮埋頭在邢舟膛,聲音哽咽,“回去…回去。”
“回哪兒去?”邢舟笑,“換個地方。”
健碩的肩膀留下牙印,大小不一。
桑暮被放在地上,背脊著寬闊膛,腰被攬著。垂落地窗簾就在腳踝邊,流蘇蹭過來,像羽輕掃。
後半夜,屋外的蟬鳴聲歇了。
浴室的花灑響起。
窗簾流蘇滴滴答答地有水聲滾落,靠近穿鏡的那片布料要比其他地方深得多。
沒多久,邢舟從浴室出來,拆了整片窗簾,扔進洗機。
-
桑暮第二天醒來的時候,眼皮重得睜不開。尤其上一,骨頭像是被拆開重新組裝過。可約又有沉浮的暗在意識裏翻滾,讓人心舒朗。
記憶尚未回籠,桑暮有點迷糊。
周圍的擺設不陌生,灰的床單和被套,是邢舟會用的款式。
只是這太,好像有點太大了。
就在這時,眼前遮過來一只手掌。大手抵擋住大半的線,只有縷縷從指中過來,不過已然不刺目。
扭回頭,就對上邢舟的目。剛睡醒,他的眸懶散勁兒更濃。
還赤...的,和他上一樣。
條件反地被嚇了跳,桑暮猛然回神,手掌倏然往邢舟前推,“邢舟?我怎麽睡這兒了?”
邢舟玩味地低笑聲,“有人半夜趁著我洗澡跑進來,你說呢?”
“……”
空氣沉默足足有半分鐘。
如果可以,桑暮是希自己能斷片兒的。
昨天半夜纏著邢舟那個肯定不是自己,桑暮想,肯定不是。
空氣又沉默半分鐘。
直往臉頰上湧,桑暮是真慌了,扯著被子就坐起。可在下床的瞬間,視線卻不自覺地落到窗邊。
只有一半的窗簾,另一邊空空。
邢舟坐起來,手臂環住桑暮的腰,手指按,也就一掌寬。
順著桑暮的視線看過去,邢舟眼皮半斂,目停了片刻便收回來。
男人的聲音厚,語速緩慢,“今天天氣好,一會兒去天臺曬窗簾?”
“……”
如果心髒能聽見回音,可能會明白什麽震耳聾。
良久,桑暮扭回頭,腦袋低下,砸到邢舟的口。
快哭了。
“暮暮,你——”
“邢舟…”桑暮聲音低弱的幾乎要聽不到,“你別說話了。”
作者有話說:
又是深夜場=w=
暮暮梅開二度,吧嘿嘿(叉腰)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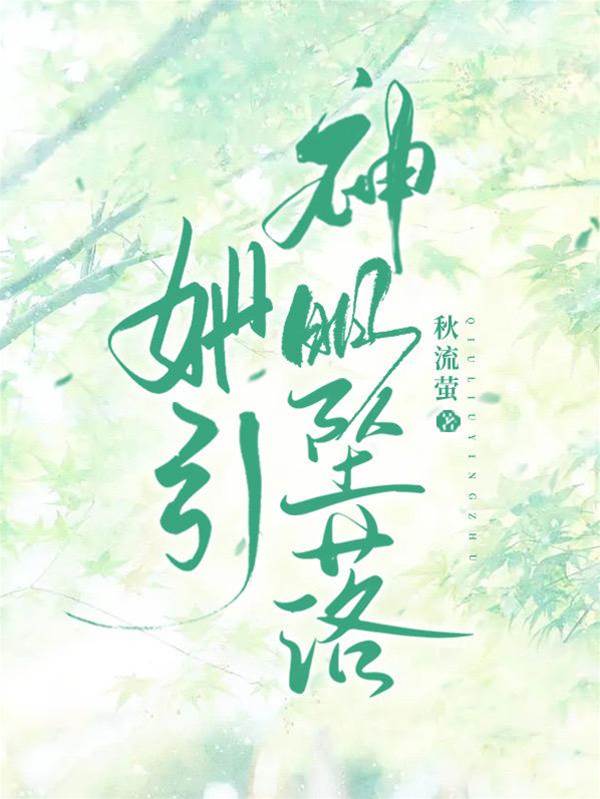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6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