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死遁后,四個夫君找上門了!》 第214章 斜上方
亥時三刻。
這確到刻滴水的時刻,仿佛是懸在所有人頭頂的鍘刀終于落下的信號。沒有預兆,沒有呼喊,武庫的方向,深沉的夜空像一塊被驟然撕裂的厚重黑布。
一團巨大、扭曲、裹挾著無盡毀滅的烈焰,裹著濃黑的煙柱,猛地撕裂了籠罩皇城的夜幕!那火焰的妖異得令人頭皮發麻,并非尋常暖紅或熾金,而是慘烈、冰冷、近乎詛咒的藍綠。這詭異的火舌瘋狂地舐著夜空,仿佛地獄的巨口貪婪地向上噬咬。它們貪婪地吞噬著武庫龐大的木質結構,發出沉悶如巨垂死咆哮的裂聲,噼啪作響。火星如同被驚飛的億萬只赤紅毒蜂,裹挾著滾燙的灰燼和燃燒的碎片,狂暴地噴濺向四面八方,將皇城西北角那片天空徹底點燃、煮沸!
空氣中瞬間彌漫開刺鼻的焦糊、硫磺和濃烈桐油燃燒的惡臭,即使相隔遙遠,這氣味也如同無形的毒爪,狠狠攫住了金鱗池邊每一個潛伏者的咽,帶來窒息般的迫。
“走!”
劉景晝的聲音從咬的牙關中迸出,短促、冰冷,如同淬火的鐵片在寒冰上刮。沒有一猶豫,他猛地向前一撲,影瞬間沒金鱗池邊緣那個僅容一人通過的幽深水。隨其后,三十條沉默的黑影如同被同一個意志驅的提線木偶,作迅捷、決絕、帶著一去無回的慘烈,一個接一個地消失在翻涌著惡臭黑水的口。
黑暗,帶著冰冷刺骨的意和令人作嘔的腐敗氣味,瞬間從四面八方過來,沉重得如同的裹尸布。池水渾濁粘稠,散發著長年累月淤積的污泥、腐爛水藻和某種難以言喻的尸混雜的濃烈惡臭。水道狹窄仄,兩壁覆蓋著膩冰冷的青苔和不知名的黏稠菌。頭頂是糙堅的石頂,低矮得幾乎著頭皮。每一次艱難的前行,都伴隨著沉重的劃水聲和狹窄空間帶來的令人牙酸的聲。
Advertisement
唯一的源,是劉景晝手中死死攥著的一顆龍眼大小的夜明珠。它散發出的微弱熒,僅能勉強照亮前方不足一臂的距離,在這吞噬一切的濃稠黑暗里,如同風中殘燭,微弱得令人絕。這點微,映照出水道壁上扭曲蠕的影,更映出每一個死士慘白繃、被絕和瘋狂徹底占據的臉龐。他們的眼睛在幽中如同瀕死野,死死盯著前方那點微,瞳孔深燃燒著孤注一擲的火焰。
時間在這里失去了刻度,只剩下無盡的劃水和重的息。渾濁的污水灌他們的口鼻,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腐爛的淤泥。沉重的甲胄和兵刃在水下了致命的負擔,每一次劃臂都牽扯著幾乎要斷裂的筋。冰冷的污水貪婪地汲取著他們上每一熱量,麻木從四肢末端開始,緩慢而堅定地向上侵蝕。
“呃……”
一聲抑到極致的、幾乎不調的悶哼,突然從隊伍中部傳來。這聲音在死寂的水道中不啻于一聲驚雷!接著是“當啷”一聲清脆銳利的金屬撞擊!
所有人的作瞬間凝固,連水流聲都仿佛在這一刻被凍結。劉景晝猛地回頭,夜明珠慘綠的暈恰好照見一張年輕得過分、此刻卻因極度恐懼而扭曲變形的臉。那死士手中的短刃手落,正砸在水底一塊凸起的上,那一聲撞擊,在死寂閉的水道里被無限放大,如同喪鐘敲響,震得每個人心臟都停止了跳!
時間仿佛被這聲脆響釘在了原地。死寂,沉重到足以碾碎靈魂的死寂,瞬間吞噬了整個水道。三十雙眼睛在幽暗的綠下驟然收,瞳孔深發出驚駭絕的寒芒。渾濁的污水似乎也停止了流,冰冷粘稠地裹住每個人的,如同墳墓里的封土。
頭頂上方,隔著那層厚重而令人窒息的石板,死一般的寂靜僅僅維持了令人發瘋的一瞬。
“嘩啦!”
一聲刺耳的水響如同驚雷般炸開!接著是沉重皮靴猛然踏在池邊石岸上的撞擊聲,碎石滾落的聲音清晰可聞。
“誰?!”一聲暴喝穿水面,帶著驚疑和警覺,如同淬毒的冰錐狠狠刺下,“下面有靜!金鱗池!快!”那聲音糲沙啞,充滿了被驚擾后的狂暴。
腳步聲!不止一雙!雜沓、沉重、帶著金屬甲葉的鏗鏘銳響,正從他們頭頂的石板邊緣急速匯集!如同沉重的鼓點,狠狠敲打在每一個死士的心尖上。那聲音近在咫尺,仿佛下一秒,那層將他們與死亡隔開的石板就會被掀開!
年輕死士的臉在幽綠的線下徹底失去了人,慘白得像一張浸了水的紙。他篩糠般抖著,牙齒咯咯作響,眼中只剩下無邊無際的、能將靈魂都凍結的恐懼,連掙扎的力氣都徹底流失。
劉景晝了!
他的作沒有任何預兆,快得超越了人眼的極限。沒有斥責,沒有猶豫,甚至沒有一多余的表。在夜明珠慘綠芒的映照下,那張棱角分明的臉如同戴上了一副冰冷的青銅面。就在那年輕死士因極致的恐懼而瞳孔渙散、徹底癱的瞬間,劉景晝的手,那只握著分水峨眉刺的手,已化作一道模糊的殘影,裹挾著粘稠冰冷的池水,準無比地向前刺出!
“噗!”
一聲極其沉悶、令人骨悚然的輕響。那是利刃穿皮、刺破臟、最終被骨骼阻擋的死亡之音。
峨眉刺冰冷銳利的尖端,毫無阻礙地從年輕死士的頸側第三、四肋骨之間的隙準刺,斜向上方,以最致命的角度,瞬間貫穿了心臟。力道之猛,甚至讓刺尖在穿后,淺淺地抵在了水道的后壁上。
年輕死士的猛地向上直,如同一條被釘在案板上的魚。他嚨深發出一聲短促到幾乎無法察覺的“嗬”聲,所有的恐懼、痛苦、甚至最后一求生的意念,都在那雙瞬間放大的、空失神的眼睛里凝固、熄滅。滾燙粘稠的鮮,如同找到了決口的堤壩,猛地從傷口和口鼻中狂涌而出,瞬間在冰冷的污水中暈開一大片濃得化不開的、妖異的暗紅。
時間,在這腥彌漫的瞬間被到了極致。劉景晝的作沒有毫停頓,仿佛只是拂去一粒塵埃。他手腕猛地一擰,干脆利落地拔出了峨眉刺。年輕死士失去支撐的尸立刻被沉重的甲胄拖拽著,無聲無息地向水底沉去,只在渾濁的水中留下一串緩緩上升的、帶著沫的氣泡,如同他剛剛消散的生命。
“走!”劉景晝的聲音得更低,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冰封的深淵里鑿出來,帶著刺骨的寒意和不容置疑的鐵。他猛地揮手,那作如同斬斷一切的利刃。隊伍在極致的死寂中再次啟,比之前更加迅捷,更加沉默,如同三十條被死亡驅趕的幽靈,無聲地過同伴尚未冷卻的尸和那仍在緩緩擴散的。冰冷的水流沖刷著他們僵的臉龐,也沖刷著那濃得令人窒息的腥。頭頂上方,守衛們雜的呼喝和腳步聲并未停止,反而更加焦躁地在池邊來回巡弋,如同嗅到腥卻找不到獵的鬣狗。
“頭兒!這鐵柵……”前方,一個材異常魁梧、綽號“石熊”的死士用氣聲嘶嘶地示意,夜明珠的微映出前方水道被一扇厚重銹蝕的鐵柵欄死死封住。如兒臂的鐵條上掛滿了膩的水藻和藤壺,隙間塞滿了不知堆積了多年的枯枝敗葉和令人作嘔的污。
劉景晝游近,手指在冰冷糙、布滿瘤狀銹蝕的鐵條上急速索,指尖傳來的只有令人絕的厚重和堅固。他猛地抬頭,夜明珠幽映照下,他的眼神銳利如鷹隼,瞬間鎖定了鐵柵上方與水道石頂之間一道狹窄得幾乎無法察覺的罅隙——那是水流常年侵蝕和柵欄銹蝕變形留下的唯一生機,寬度勉強容得一個卸下甲胄的人側過。
“卸甲!石熊先上!”命令如同冰錐鑿下。
石熊沒有毫猶豫,雙手在水中飛快地解開腰間的皮扣和肩甲系帶。沉重的鐵甲片一件件離他的,無聲地墜向漆黑的水底,如同沉無底的深淵。魁梧的軀在水中顯得異常靈活。他深吸一口氣,猛地向上蹬水,雙手死死抓住鐵柵冰冷膩的上緣,壯的手臂虬結賁張,發出令人心悸的力量。他像一頭攀爬絕壁的巨猿,將在膩的石壁上,利用肩膀和背脊的蠻力,一點一點、極其艱難地向上方的罅隙去。鐵銹和的青苔簌簌剝落,掉下方渾濁的水中。骨骼在狹窄空間里被,發出令人牙酸的輕微“咯咯”聲。終于,他那魁梧的軀猛地一掙,徹底消失在那道狹窄的死亡隙之后。
“下一個!”劉景晝的聲音如同催命的符咒。一個又一個死士卸下保命的甲胄,如同蛻去外殼的蟲豸,將自己最脆弱的暴在這致命的狹前。每一次攀爬、、穿越,都是一場與死神面共舞的賭博。罅隙邊緣糙的巖石和銹蝕的鐵條,毫不留地刮著他們的皮,留下道道痕,瞬間又被冰冷的污水沖刷得麻木。幽暗的水道中,只聽得見抑到極致的息、皮石壁的沙沙聲,以及強行過時骨骼不堪重負的。每一次功的穿越,都伴隨著一聲幾乎虛的沉重水響,那是墜柵欄另一側水中的聲音。
當最后一個死士的影消失在罅隙之后,劉景晝深吸一口氣,那冰冷的、帶著濃烈腥和腐臭的空氣仿佛鋼針般刺他的肺腑。他猛地蹬水,如同離弦之箭向上竄去。冰冷的石壁和銹鐵著他的肩膀和脊背,帶來火辣辣的劇痛。就在他即將完全穿過罅隙的剎那——
“咔嚓!”
一聲極其輕微、卻又無比清晰的脆響,從他著的石壁部傳來!仿佛是什麼支撐了千百年的東西,在重之下終于不堪重負,裂開了一道致命的隙。幾塊細小的碎石,伴隨著簌簌落下的灰泥,毫無征兆地砸落在他的頭頂和肩膀上。
劉景晝的瞬間僵住!心臟在腔里如同被一只冰冷的鐵手狠狠攥住,幾乎停止了跳。他死死屏住呼吸,全的都提升到了極致,捕捉著頭頂上方任何一可能的異。時間仿佛凝固了。
萬幸!頭頂池岸上,守衛們焦躁的腳步聲和呼喝聲依舊雜,似乎并未察覺這來自水底深的細微異響。那一聲微弱的“咔嚓”,被淹沒在了遠武庫大火燃燒的沉悶轟鳴和近守衛們不安的走聲中。
劉景晝不敢再有毫耽擱,腰腹猛地發力,如同溜的泥鰍,徹底掙了狹窄罅隙的束縛,“嘩啦”一聲輕響,落了鐵柵欄另一側更加冰冷、仿佛連靈魂都要凍結的深水之中。
水道在前方豁然開朗,卻又更加幽深莫測。水流變得更加湍急冰冷,帶著一種直達骨髓的寒意。他們像一群沉默的游魚,在絕對的黑暗和刺骨的冰寒中力潛行,只能依靠前方同伴攪水流帶來的微弱牽引辨別方向。肺部的空氣一點點耗盡,每一次試圖換氣都只能吞帶著濃重鐵銹和腥味的污水,帶來一陣陣撕心裂肺的嗆咳和灼痛。意識在冰冷和窒息的雙重夾擊下開始模糊,眼前的黑暗仿佛有了重量,不斷向中心收、。就在這瀕臨極限的絕邊緣,前方帶路的石熊猛地停了下來,巨大的軀在水中微微抖,指向斜上方——一極其微弱、如同幻覺般搖曳的昏黃線,過水面約下!
猜你喜歡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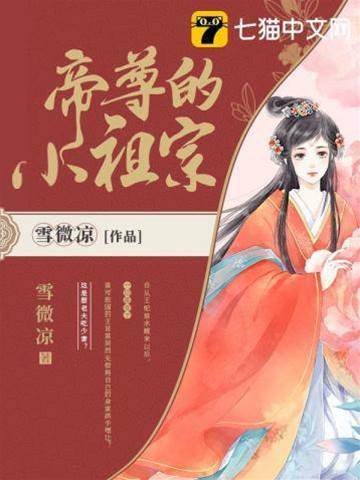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
完結506 章

媚婚之嫡女本色
陌桑穿越了,穿越到曆史上沒有記載的時空,職場上向來混得風生水起的白領精英,在這裏卻遇上讓她恨得咬牙切齒的克星,高冷男神——宮憫。 他嫌她為人太過陰詭狠毒。 她嫌他為人太過高冷孤傲。 本想無事可做時,虐虐渣女渣男,逗逗小鮮肉。 豈知一道聖旨,把兩個相互看不順眼的人捆綁在一起,組成嫌棄夫婦。 自此兩人過上相互猜測,彼此防備,暗裏算計,夜夜心驚肉跳的生活。 豈知世事難料,兩個相互嫌棄的人看著看著就順眼。 她說“你是護國賢臣,我是將門忠良,為何跟你在一起,總有種狼狽為奸的覺悟。” 他說“近墨者黑。” 陌桑點點頭,確實是如此。 隻是,到底是誰染黑誰啊? 再後來…… 她說“宮憫,你是不會笑,還是從來不笑?” 他看了她十息,展顏一笑“陌桑,若知道有一天我愛你勝過愛自己,一開始就不會浪費時間防備你、猜疑你,而是把所有的時間用來狠狠愛你,因為一輩子太短,我怕不夠愛你。” 陌桑咽著口水道“夫君,以後千萬別隨便笑,你一笑,人就變得好風騷……” 宮憫麵上黑,下一秒就露出一個魅惑眾生的笑容“娘子放心,為夫隻對你一人笑,隻對你一人風騷。” 某女瞬間流鼻血…… 【這就是一個白領精英穿越到異世古國,遇上高冷男神,被帝王捆綁在一起,相殺互撕,最後相親相愛、強強聯手、狼狽為奸的權謀愛情故事。】
187.7萬字8.18 335163 -
完結639 章

萬毒狂妃懷個寶寶來虐渣
她,本是藥王谷翹楚,卻因圣女大選而落入圈套,被族人害死。 一朝身死,靈魂易主。 楚斐然自萬毒坑中醒來,一雙狠辣的隼目,如同厲鬼蒞臨。 從此,撕白蓮,懲惡女,不是在虐渣,就是在虐渣的路上。 她醫毒雙修,活死人,肉白骨,一手精湛的醫術名動。 此生最大的志向就是搞到賢王手上的二十萬兵馬,為她浴血奮戰,血洗藥王谷! 不料某天,他將她抵在角落,“女人,你懷了本王的孩子,還想跑路?”
110.9萬字8 124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