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身為奴?紈绔夫君為我掙誥命》 第180章 一命換一命
“孤看你們誰敢走!”
就在主事將要退的時候,太子出聲了。
太子此時目沉地看向他們,聲音中帶著幾分憤怒和威脅。
主事卻是十分為難,太子和世子,這兩個人他哪個都得罪不起啊!
他和大理寺的兵面面相覷,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主事看了看太子,又看了看顧知行,最終咬了咬牙,緩緩后退。
得罪太子,太子也只會借機尋到他們錯,敲打他們。
可若是得罪了世子,那顧知行可是不管什麼三七二十一,也不管什麼份地位的,直接將人往死里整。
二者孰輕孰重,他們的心里還是有點數的。
火把的如水般向山下退去,留下一片黑暗。
“放肆!”
太子即便再怒,也無濟于事。
畢竟大理寺的人不是他的親兵,不聽他的傳喚。
他的目在人群中掃過,咬牙切齒地說道:“好,這筆賬,我記下了!”
東家盯著這一幕,眼神依舊晴不定。
刀刃仍抵在沈今棠的頸間,但已不如先前那般狠絕。
他咬牙道:“顧知行,你最好別耍花樣!”
顧知行微微瞇眼,語氣低沉而篤定:“我若想殺你們,方才就不會讓人馬撤下去。”
他的聲音中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坦,仿佛在用行證明自己的誠意。
東家沉默了片刻,終于稍稍松了力道,但刀刃仍未撤下。
他測測地笑了:“好,那你現在,去把太子給我押過來!”
顧知行的目一沉,但很快恢復了平靜。
Advertisement
他不聲地頷首:“可以。”
他的聲音中沒有一猶豫,仿佛早已做好了應對一切的準備。
夜風呼嘯,火在風中搖曳不定。
顧知行站在原地,背脊筆直如松,仿佛是一座不可撼的山峰。
他的眼底卻暗流洶涌,他知道,真正的博弈,才剛剛開始。
“葉輕舟!”顧知行頭也不回地厲聲道,聲音中帶著一不容置疑的命令,“去請太子殿下過來敘話。”
他特意咬重了“請”字,語氣中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堅定。
葉輕舟應了一聲,轉朝另一側走去。
而顧知行的目卻一直在沈今棠的上,他瞧著沈今棠因疼痛而微微抖的;看著鮮順著的鎖骨滾落,滴進領,染紅了一片;看著那痛苦的神,著實是憂心。
他抬手做了個下的作,聲音忽然放輕,語氣卻著一種不容忽視的威嚴:“刀拿穩些,你手上可是我的命。”
這句話像是燒紅的鐵,狠狠地烙在綁匪的心上,讓他手腕一抖。
東家鷙地盯著顧知行,眼神中滿是憤怒和不甘:“現在說這些屁話——”
“你求的是活路。”
顧知行冷冷打斷他,作利落地解下腰間的佩劍,隨手扔在地上,發出一聲清脆的聲響。
他的聲音沉穩而有力:“用我換。你們挾持朝廷命,比挾持個姑娘更有談判籌碼。”
“我們可以繼續我們的易。”
他往前邁了一步,月灑在他腰間的玉帶上,那代表朝廷重臣的銀魚符在夜中閃爍著冷。
山道上傳來嘈雜聲,葉輕舟反剪著太子的雙臂,將他拖了上來。
太子金冠歪斜,蟒袍上沾滿了塵土,狼狽不堪,活像一只被拔了的孔雀。
他掙扎著,卻彈不得,只能發出憤怒的低吼。
東家見狀,突然發出一陣怪笑,眼中閃爍著瘋狂的:“世子殿下好算計。”
他了干裂的,刀鋒在沈今棠頸間游走,仿佛在這種掌控生死的覺,“可老子改主意了。”
他猛地指向太子,聲音中帶著一種扭曲的興:“一命換一命——殺了他!”
“殺了太子,老子就放了你的心上人。”
夜風突然靜止,連火把燃燒的噼啪聲都變得異常清晰。
顧知行站在原地沒,月將他拔的影拉得老長,在地上投下一道凝重的影。
他的手指無意識地挲著刀柄上的紋路,每一道刻痕都像是刻在他心上。
他看向沈今棠,的臉蒼白如紙,月下幾乎明,脖頸上那道痕像一條猙獰的蜈蚣,刺得他眼睛生疼。
那雙總是倔強的眼睛此刻正靜靜著他,沒有恐懼,沒有哀求,只有一種近乎決絕的冷靜。
顧知行心頭猛地一——什麼都比不過活著。
他在心里狠狠咒罵太子這個蠢貨,若不是他突然帶兵上山,此刻沈今棠早已安全地站在他邊。
這個念頭讓他握刀的手又了幾分,指節泛出森冷的青白。
他轉過,拿起刀,一步步的朝著太子走過去。
“顧知行!”太子的聲音突然拔高,帶著明顯的抖,仿佛被驚嚇到看,“你瘋了不?你真要為個人殺我?”
他的在寬大的蟒袍下瑟瑟發抖,金冠歪斜,哪還有半點儲君的威儀。
他的哆嗦著,聲音越來越尖利:“你想想后果!你殺了孤,父皇不會放過你的!”
“你即便是殺了孤,他們真能放了沈今棠嗎?”太子的聲音愈發大了,仿佛在試圖喚起顧知行的理智。
“不可能的!”
太子的聲音在夜中回,顯得格外刺耳。
“顧知行,你冷靜一點,你這是自己把把柄給他們手上!”聲音中帶著一哀求,仿佛在試圖抓住最后一救命稻草。
顧知行的太突突直跳,仿佛有一顆心臟在那里猛烈地跳。
他當然知道這些匪徒打的是什麼主意,他們是想讓他也上了他們的賊船,是想拿住他的把柄。
可當他再次看向沈今棠,看到因失而泛白的,看到脖子上不斷滲出的鮮,一前所未有的沖幾乎要沖破理智的牢籠。
東家不耐煩地晃了晃刀,刀刃在火下閃著冷:“磨蹭什麼?再不手,我就先送這丫頭見閻王!”
說著,刀刃又朝著沈今棠頸間的皮更近了一分。
沈今棠咬下,是沒發出一聲音,但顧知行看見的睫因疼痛而劇烈地抖了一下。
顧知行的手死死按在刀柄上,骨節發白,指關節因為用力而微微發抖。
殺太子,萬劫不復;不殺,沈今棠必死。
這個兩難的選擇像一把鈍刀,正在一點點鋸著他的神經。
他從未如此進退兩難過,額頭上滲出細的汗珠,順著繃的下頜線落。
他的呼吸變得急促,眼睛盯著沈今棠,仿佛能從的眼神中找到答案。
東家顯然看穿了他的掙扎,突然咧開笑了,出一排參差不齊的黃牙。
他故意挑釁道:“顧大人,這有什麼好猶豫的?”
“殺個與你爭奪皇位的太子,換心上人活命,這買賣多劃算?”
顧知行盯著那滴珠滾進沈今棠的領,結劇烈滾了一下,仿佛有什麼東西哽在嚨里,讓他幾乎窒息。
時間仿佛在這一刻凝固,夜風呼嘯,火搖曳,一切都變得格外安靜。
顧知行站在那里,背影在火中拉得老長,仿佛一座即將崩塌的山峰。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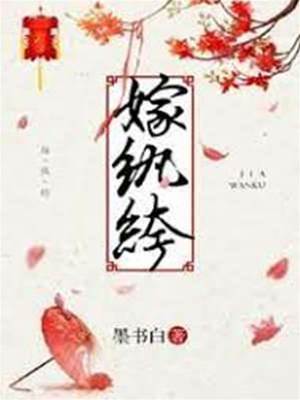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94 章

驚雀
虞錦乃靈州節度使虞家嫡女,身份尊貴,父兄疼愛,養成了個事事都要求精緻的嬌氣性子。 然而,家中一時生變,父兄征戰未歸生死未卜,繼母一改往日溫婉姿態,虞錦被逼上送往上京的聯姻花轎。 逃親途中,虞錦失足昏迷,清醒之後面對傳言中性情寡淡到女子都不敢輕易靠近的救命恩人南祁王,她思來想去,鼓起勇氣喊:「阿兄」 對上那雙寒眸,虞錦屏住呼吸,言辭懇切地胡諏道:「我頭好疼,記不得別的,只記得阿兄」 自此後,南祁王府多了個小小姐。 人在屋檐下,虞錦不得不收起往日的嬌貴做派,每日如履薄冰地單方面上演著兄妹情深。 只是演著演著,她發現沈卻好像演得比她還真。 久而久之,王府眾人驚覺,府中不像是多了個小小姐,倒像是多了個女主子。 後來,虞家父子凱旋。 虞錦聽到消息,收拾包袱欲悄聲離開。 就見候在牆側的男人淡淡道:「你想去哪兒」 虞錦嚇得崴了腳:「噢,看、看風景……」 沈卻將人抱進屋裡,俯身握住她的腳踝欲查看傷勢,虞錦連忙拒絕。 沈卻一本正經地輕飄飄說:「躲什麼,我不是你哥哥嗎」 虞錦:……TvT小劇場——節度使大人心痛不已,本以為自己那嬌滴滴的女兒必定過得凄慘無比,於是連夜快馬加鞭趕到南祁王府,卻見虞錦言行舉止間的那股子貴女做派,比之以往還要矯情。 面對節度使大人的滿臉驚疑,沈卻淡定道:「無妨,姑娘家,沒那麼多規矩」 虞父:?自幼被立了無數規矩的小外甥女:???人間不值得。 -前世今生-我一定很愛她,在那些我忘記的歲月里。 閱讀指南:*前世今生,非重生。 *人設不完美,介意慎入。 立意:初心不改,黎明總在黑夜后。
21.3萬字7.83 21942 -
完結866 章

神醫魔后
21世紀玄脈傳人,一朝穿越,成了北齊國一品將軍府四小姐夜溫言。 父親枉死,母親下堂,老夫人翻臉無情落井下石,二叔二嬸手段用盡殺人滅口。 三姐搶她夫君,辱她爲妾。堂堂夜家的魔女,北齊第一美人,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個笑話。 她穿越而來,重活一世,笑話也要變成神話。飛花爲引,美強慘颯呼風喚雨! 魔醫現世,白骨生肉起死回生!終於,人人皆知夜家四小姐踏骨歸來,容貌傾國,卻也心狠手辣,世人避之不及。 卻偏有一人毫無畏懼逆流而上!夜溫言:你到底是個什麼性格?爲何人人都怕我,你卻非要纏着我? 師離淵:本尊心性天下皆知,沒人招惹我,怎麼都行,即便殺人放火也與我無關。 可誰若招惹了我,那我必須刨他家祖墳!
228.2萬字8 394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