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戀多年后,死對頭和我表白了》 第1卷 第六十章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走到醫院外,見霍應瓷走向駕駛座,郁綏青不放心地問:“你能開嗎?”
霍應瓷勾在門把手上的指節頓住。
自己現在看上去有這麼弱嗎?
他漫不經心地甩了甩手里的車鑰匙,散漫道:“能,你歇會兒吧。”
郁綏青原本打算代駕,但既然霍應瓷說可以開,也就沒再繼續。
搶救的時候和另外幾名醫護著做了半個小時的心肺復蘇,現在手又酸又痛,沉得跟灌了鉛似的,本抬不起來,更別說開車了。
經歷了起起伏伏的一晚上,的心也跟著大起大落,松懈下來之后,如今只覺得疲力盡。
一路都很安靜。
霍應瓷的目忽然轉向,問:“你在想什麼?”
郁綏青很誠實:“在想剛剛搶救怎麼能做得更好。”
每次搶救之后,無論功與否,在郁綏青的心里的想法都是,可以更好。
很喜歡用挑剔到極致的目來審視自己,做什麼事都是。
“做得再好一點,他就可以活過來嗎?”
“或許吧。”郁綏青說。
但其實心里很清楚。第一次心梗塞后,那名患者的心臟里就已經被放了三個支架,短時間再次發作,能救活的可能微乎其微。
“別太苛責自己了。”霍應瓷很認真地安道,“他的去世是很多原因造的,你做的已經足夠多了。”
Advertisement
聽起來怎麼有些耳。
“霍機長。”郁綏青忽然很鄭重地他,接著輕哂一聲,“這話,你是不是最該對自己說?”
霍應瓷臉一凝,從間出幾個字:“這不一樣。”
聽著他逐漸減弱的語氣,郁綏青終究沒繼續說下去。
霍應安確實是他心里最大的心結,否則他也不至于聽見“憶安”兩個字,就很難控制住自己的表。
當時那麼多臨時、那麼多巧,就那麼億萬分之一的幾率,卻偏偏被他遇上了。
車廂里的氣氛幾乎跌到谷底。
他許久沒再開口,郁綏青換了個輕松點的語氣:“該我問了,你在想什麼呢?”
“我在想高中的時候怎麼沒好好學習,沒能跟郁醫生當燕大校友。”
想到聽見“燕大”兩個字時眼里的,霍應瓷不滿地撇撇。
郁綏青沒聽出話外之意,反駁道:“燕航也不差啊。”
記得霍應瓷的高考績是夠了燕大錄取分數線的,只不過為了學航空專業直接填了燕航而已。
這算什麼,凡爾賽嗎?
“是燕大校友,就能擁有郁醫生的聯系方式。”霍應瓷笑了笑,“這讓燕航怎麼比?”
只要是調侃的時候,霍應瓷就很喜歡“郁醫生”。
他這是……吃醋了?
郁綏青小聲說:“最后不還是沒加上嘛。”
想了想覺得更無語,霍應瓷戲謔地反問:“我是不是還得和你說聲謝謝?”
托你的福,今天莫名其妙認識了一個剛踏社會的書呆子,激起來還是個會朝著揮拳頭的超雄男。
“這就不必了。”郁綏青回絕。
到家后,莊姨做好的飯已經被整齊地碼在了餐桌上,只不過他們回來晚了,飯都冷了。
郁綏青把菜一道道放進微波爐里,招呼著后面進來的霍應瓷:“去洗手吃飯吧。”
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聽起來這麼平淡日常的一句話,卻在他的心里引起了軒然大波。
原來有人在等是這種覺。
洗完手,他在餐桌邊坐下,隔著玻璃門向廚房忙碌的背影,不慨:“郁醫生好賢惠啊。”
“不如霍機長之前天天做飯來得賢惠。”郁綏青拿著兩副碗筷走出來。
飯菜全部熱好之后,直接悶頭吃飯,一句天也沒和霍應瓷聊。
莊姨做起家常菜來還是駕輕就,這香味俱全的菜式,勾得本來沒什麼胃口的霍應瓷都忍不住多吃了幾口。
吃過飯,郁綏青沒事干,索在院子里陪芋圓丟球玩。
霍應瓷倚在臺邊盯著他們,眼底帶著意味不明的笑意。
一陣凜冽的寒風吹過來,霍應瓷突然開口的名字:“郁綏青。”
的視線順著這句話看過來,不輕不重,卻又足夠讓人張。
霍應瓷下意識住角:“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什麼事?”郁綏青有些好奇,帶著還沒玩夠的小狗從院子里走進來。
俯著子在換鞋,沒空對上他洶涌的目。
于是趁著這個機會,霍應瓷問:“我們以后……能不能就像一對真正的夫妻那樣?”
“砰”“砰”“砰”——
清晰地到自己加快的心跳,郁綏青明知故問:“……哪樣?”
“真正的夫妻……”
他腔調散漫,表認真地答:“舉案齊眉,琴瑟和鳴,相濡以沫,白頭偕老。”
怕郁綏青覺得是在開玩笑,又補充道:“沒有在背語,這是我真實的想法。”
在經歷反復糾結之后,霍應瓷終于決定直視自己的心。
他確實喜歡上郁綏青了。
只要一想到,心里就有一難自抑的激。
很難解釋,也很難克制。
想和擁有,想和安安穩穩地過日子,想把列到自己未來的計劃里。
他嘗試著忽視了這麼久,最后卻不得不承認,其實這就是喜歡而已。
哪有什麼原因,哪有什麼借口。
凝視了半晌,霍應瓷語氣嚴肅的像是在和陌生人談合作:“你呢,你怎麼看?”
郁綏青形容不出來自己現在的心。
這種覺像是什麼呢?
手里握著一張等待開獎的號碼,為了它付出過所有的心力,張夠了、激夠了,等到再回首的時候,終于發現自己已然穩勝券。
跟做夢一樣。
這一天其實想象很多次,有時是轟轟烈烈的,有時是浪漫的,卻唯獨沒想過,是在一個普通的冬夜。
沒有穿任何莊重的禮服,凌的頭發甚至被挽在耳后,只是在院子里逗狗,覺到一道令人安心的視線總在追隨著自己。
接著聽見霍應瓷平靜地說出這些話,平靜地鑿開心里厚重的冰封。
“我……”郁綏青激得語無倫次,剛想說什麼,就被霍應瓷的手機鈴聲打斷。
來電人是陸澤舟。
他剛想按斷,郁綏青卻擔心是有什麼要事,示意他接起來。
電話被接通,陸澤舟的聲音大咧咧從聽筒里傳過來:“好了沒?我來問一下你,別太。”
猜你喜歡
-
完結271 章

且以深情共余生
相似的聲音,相似的容貌,遇見了同一個他。兜兜轉轉,走走停停,時光不改蹉跎。如果上天再給她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一定奮不顧身愛的更加用力!
50萬字8 9205 -
完結378 章

玄門回來的假千金又在擺攤算卦了
肖梨在玄門待了一百年,同期進來的那條看門狗小黑,都已經飛升上界,她還只能守著觀門曬太陽。老祖宗顯靈告訴她,“肖梨,你本來自異界,塵緣未了,若想飛升,还得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却凡尘杂事,方可勘破天道!” 回到现代,肖梨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这一世,没有留念,两手空空跟着亲生父母离开肖家。 圈内人都在等着,肖梨在外面扛不住,回来跟肖家跪求收留。 却不想…… 肖梨被真正的豪门认回,成为白家千金,改名白梨。
64.4萬字8 60458 -
完結189 章

荒腔
沈弗崢第一次見鍾彌,在州市粵劇館,戲未開唱,臺下忙成一團,攝影師調角度,叫鍾彌往這邊看。 綠袖粉衫的背景裏,花影重重。 她就那麼眺來一眼。 旁邊有人說:“這是我們老闆的女兒,今兒拍雜誌。” 沈弗崢離開那天,州市下雨。 因爲不想被他輕易忘了,她便胡謅:“你這車牌,是我生日。” 隔茫茫雨霧,他應道:“是嗎,那鍾小姐同我有緣。” 京市再遇,她那天在門店試鞋,見他身邊有人,便放下了貴且不合腳的鞋子。 幾天後,那雙鞋被送到宿舍。 鍾彌帶着鞋去找他。 他問她那天怎麼招呼都不打。 “沈先生有佳人相伴,我怎麼好打擾。” 沈弗崢點一支菸,目光盯她,脣邊染上一點笑:“沒,佳人生氣呢。” 後來他開的車,車牌真是她生日。
28.8萬字8 17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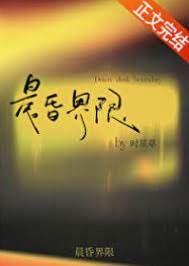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