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腰》 第4章 你吃錯藥了?
兩人坐在餐桌上各吃各的,相對無言。
肚子不是很舒服,常妤喝了幾口湯就放下了碗筷,紙了角。
很直呼費錦的名字,聲音平靜。
“費錦,我想,要不我們還是提前離了吧。”
他眉頭蹙了一下,緘默幾秒,黑的眼睛出的冷冽幾乎要凝實,目停留在常妤的臉上,不知道要看出些什麼來。
他說:“還有六個月。”
六個月后,他們三年合約婚姻到期。
常妤盯著費錦因過度用力筷泛白的指尖,蒼白的手背上青筋微微凸起,思緒回到兩年前。
常妤的是個傳統封建的事業型人,曾給常妤定了娃娃親,在一次意外中為了救年的常妤滾下山崖,得救后落下了病,在那之后子一天不如一天。
兩年前的一個晚上,老太太突然病倒在地,醫生告訴時日不多了,讓家屬提前準備。
老太太躺在病床上代后事,說想在離世前看到常妤幸福,寓意明確,就是想讓常妤履行當年的口頭定親。
常妤覺得荒謬又可笑。
經過商討,長輩們都來讓常妤去跟那個人領證,如了老太太的愿。
面對他們一句又一句的施勸說,常妤獨自躲到一哭泣。
半夜三更,天臺的風很大,是費錦手兜慢慢悠悠地走來。
給遞紙,被一把打開。
他居高臨下的說。
“哭什麼,要不我犧牲一下娶了你?”
常妤悶聲道:“別煩我。”
“嘁,隨你。”
費錦輕笑了聲轉離開。
他一走,常妤放聲大哭。
走了的人又折了回來,百般無奈。
“你到底要怎樣啊,大小姐。”
常妤想了很久,噎噎地說了句,結婚。
翌日一早,兩人辦理完結婚證去了醫院。
老太太看著常妤跟費錦手牽手,并將結婚證遞了上來,眼眸慈祥地嘆了口氣,對費錦說要好好對常妤。
Advertisement
當天晚上,老太太走了。
下葬之時,所有人都哭的撕心裂肺,只有常妤面無表的站在人群中,心中毫無波。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常妤漸漸意識到是個極度冷的人。
“常妤。”
常妤回神:“嗯?”
費錦盯著,那雙深邃莫測的瞳眸噙劃過寒冷的暗流,比往日還要深沉濃郁。
惡劣的問:“是不是任意一個男人都能和你結婚?是不是?”
是嗎?不知道,常妤的眼神有一瞬間的恍惚,隨后覺到此刻于下位者的神態。
常妤站起來俯視,明的眼目含著笑意,有挑釁意味的反問:“難道你不也是一樣嗎?”
話落,轉離開。
常妤從不認為費錦會喜歡自己,更傾向于,費錦對自己,只有征服。
而,也不會喜歡他,更不會上他。
出了云川灣,常妤沒有第一時間去公司。
到了林爾約的咖啡廳,坐在林爾對面,頗有耐心的聽林爾吐槽家里的那個禽哥哥,偶爾遞一張紙巾過去。
林爾了一把鼻涕,眼尾通紅地說道:“你都不知道他“欺負”起人來有多狠!”
面對林爾的哭訴常妤習以為常,神自若的端起咖啡喝了口:“你我來,就是來說這事?”
林爾點了下頭,又搖頭:“不是的,昨晚你對面坐的那個穿白子的人,還有印象嗎?”
白子瓜子臉大眼睛,沒什麼辨識度,不過在場的就穿的最純,常妤記得。
“怎麼了?”
“聽我哥說,這個的商渝,是費錦的初白月。”
初白月?
常妤聽著眸深了深,從初中到現在沒聽說過費錦談過什麼朋友,就連和他結婚都是越過直接領證。
常妤稍有興趣地問:“哪個時候的初?”
林爾搖搖頭:“不知道。”
“然后呢?”
林爾托腮,水靈靈的眼睛著常妤,撒般的說道:“問我要費錦的聯系方式,我這不沒有嘛,我又不敢問我哥要,你和費錦不是一起長大的嗎,應該有他的聯系方式吧?”
“有。”
“那你推給吧,商渝先前幫過我一個小忙,人還好的,就當是替我報個恩。”
“好啊,你先讓加我。”
給丈夫找妻子這種事,常妤倒是頭一次干。
如果真如林爾所說,商渝跟費錦有過一段關系,那幫助商渝靠近費錦,進而拿下他。
離婚的事就能提前了。
下午的時候,常妤通過了商渝的好友請求,把費錦的微信給對方發了過去,并發了一個云川灣的地址,說道。
Morishima:周末的時候你可以去家里看他。
對方秒回,問道“你怎麼知道他的住所”、“聽說你們兩個是對方為眼中釘,真的假的”、“你和他認識多久了”之類的閑話,常妤只看了一眼就把人刪了。
通常周末的時候常妤會回老宅去,于是準備把以后的這段時間就留給商渝跟費錦。
常妤想,應該沒有哪個妻子比更通達理了。
周六傍晚,
云川灣燈火通明,
餐桌上擺放著一些香味俱全的菜肴,廚房里白小香風套裝的人影忙碌,
聞到菜香的費錦先是詫異的走到餐廳,只一眼,他就看出里面的人不是常妤。
商渝端著最后一盤滾燙的紅燒魚走出。
“誰讓你進來的?”
男人沉冷的聲音從背后響起,商渝子一抖,盤里的湯傾道手上,輕一聲忍著火辣辣的痛把盤子放到餐桌上。
轉過,眸中帶了些喜悅怯生生的看著費錦。
緩緩開口解釋:“我……我來找你,剛好常小姐在,說是來找你取東西的,你過一會兒就回來讓我先等著,常小姐說,我要是閑著無聊,可以給你做頓晚飯。”
說著,商渝的臉不自覺的紅了起來。
“常妤人呢?”
商渝小心翼翼的看著費錦的臉,奈何看不出一緒來,低聲說道:“說有事先回家了。”
費錦氣的不輕,眼底的波濤駭浪翻涌災,扔了句出去轉上了樓。
商渝滯在原地,直到二樓的巨大關門聲把從走神中拉回現實。
幾年前,年抖著手挪開在上的木板,那一刻商渝仿佛看到了要是自己死了,費錦會瘋的樣子。
從那以后,商渝的邊就開始有了一些費錦喜歡的傳言,不然怎麼會冒著生命危險來救呢?
以往的周六常妤都是要回老宅的,今天安頓好商渝,準備開車前去時手機里突然跳出兩條宋伊嵐發來的信息。
[妤妤啊,你和阿錦都老大不小了,結婚兩年有備孕的想法沒?]
[都說做了母親之后人的格會變,你這子也該改一改了。]
常妤睨著信息,原本進去的車鑰匙又拔了出來。
無法想象回去后宋伊嵐又會怎樣嘮叨自己,總之是不想回去了。
在車里待了半個小時,常妤開車去了公司。
晚上十點時,常妤回到云川灣。
盡量做到悄無聲息的到達三樓客房,避免打擾到費錦跟白月的春宵一刻。
別墅里燈微暗,很安靜。
路過主臥時,常妤特意慢下步子試圖聽里面的靜。
嘀嗒、嘀嗒。
只聽見一樓古鐘走的聲音。
以費錦的能力,應該不會這麼快就結束,還是說帶著人去酒店了?
常妤沒多想,來到客房打開電腦開了個線上會議,會議結束后洗漱完剛躺上床不久就睡著了。
夢里,
高三上半學期,綠坪通鋪的場上,姿卓越的黑年看準時機,一躍而起接住對面打過來的排球。
嘭的一聲,排球經過他的手被高高擊起,出幾十米遠的距離。
常妤的耳邊頓時響起生們激崇拜的尖聲。
年擁有得天獨厚的外貌形,強大的家庭背景,在校桀驁不馴,在校外更是路子野玩的花。
正是這樣張揚跋扈,狂傲不羈引來無數的慕迷。
常妤是個例外,不喜歡費錦,只想把他踩在腳下。
他們都說費錦玩的很開,雖然沒見過,但是他在外面應該有很多朋友。
常妤聽了嗤之以鼻,比誰都清楚費錦從來沒有過朋友,他們口中的玩的花,玩的開也僅限于費錦把玩的“開花”。
年們打完排球,一群生爭先恐后的跑過去給費錦遞水。
常妤心不在焉地把手中的兩瓶水隨便給了兩個男生,隔著人群,看到費錦向自己時漆黑抑的眼神。
排球向砸開,常妤嚇得猛然驚醒。
看著悉的天花板,常妤大口大口的氣。
床邊站著的人與夢中年長著一模一樣的臉,常妤注意到是他后再次被嚇了一跳。
“能不能不離婚。”
昏暗之中,男人低沉的嗓音微,卑微乞求。
常妤屏住呼吸著費錦高挑的影,看不清他臉上的表,剛才的那句話險些讓以為眼前的人不是他。
費錦啊,他怎麼會以一種下位者的語態跟說話。
空氣凝凍了許久,常妤從床上撐起:“你吃錯藥了?”
下一秒,常妤纖細的脖子被費錦單手掐住,力度不大,但足以讓恐慌。
男人冷的如冰一樣,四肢百骸無不因常妤在囂,他,不是只是上的,是想讓全心的上自己,但從始至終都從未用心對待過他,他現在就像是被鎖鏈束縛的野,極力克制著自己不去傷害。
有時候被常妤氣到失控,他是真想殺了。
把囚在家里,拿鐵鏈拴住,看一看艷尊貴的大小姐還會不會一如既往地跟他對著干。
費錦以為,兩年多的時間足以讓常妤對他的態度有所容,可是他錯了,常妤的心是鐵的,暖熱了,也會漸漸變冷,縱使他周而復始的暖,的心依舊是余溫片刻,冰冷如初。
手上的力道漸漸收,費錦神蔭翳恐怖,聲音冷到了極點。
“常妤,為了離婚你就什麼都干得出來?”
常妤力不如他,掙扎無效后揚起面容,角微勾:“是啊,要麼……離婚,要麼殺了我。”
看到了他眸底的瘋狂、霾、忍。
直到快要窒息,那只手才離開了的脖子,常妤狼狽的干咳了幾聲,抬眸對著那道離去的背影笑道。
“費錦,你不會上我了吧。”
那人腳步一頓,背對著仿佛一顆孤寂的星辰。
“是啊,上你了。”
……
常妤凌晨四點才睡著,只要一閉眼,腦子里就會響起費錦的話。
是啊,上你了。
不知道該怎樣形容聽到這句話時的心,只覺得什麼都不一樣了,又好像什麼都一樣。
心臟停了一拍,然后繼續正常跳。
早該猜到了不是嗎?
覺的自己有病,同時費錦也是有病的那一個。
所以,兩個病態的人各取所需的結婚了。
那時候,常妤本沒考慮費錦會上自己。
他怎麼能上呢,他不能上。
一覺醒來,窗外天大亮。
常妤懷著種種心事去了公司,就連開會的時候也在走神。
好不容易熬到會議結束,手機里彈出一個好友申請。
是商渝。
常妤這會兒看到和費錦有關的人跟事就煩,刪除好友申請靠在辦公椅上瞇了一會兒。
睜眼給遠在他國的弟弟撥了個視頻通話。
對方正是凌晨零點,幾秒過后,視頻接通。
常慕剛殺青,臉上的妝也沒洗,一張俊臉笑嘻嘻的喊道:“姐,想我了?”
常妤冷笑一聲:“什麼時候回國?”
常慕嚎:“姐,你是想讓我英年早逝嗎?”
常慕十八歲那年不顧家里反對走上了演繹之路,跑出國差點給常譯氣死,至今不敢跟除了常妤以外的家人聯系。
常妤睨著常慕,不容抗拒道:“玩夠了就滾回來繼承家業。”
常慕聞言從躺椅上跳起來,“我靠,不帶這樣的啊姐。”
常妤態度決絕。
“給你一個月的時間,別讓我過去逮你。”
猜你喜歡
-
完結560 章
雲胡不喜
她是出身北平、長於滬上的名門閨秀, 他是留洋歸來、意氣風發的將門之後, 註定的相逢,纏繞起彼此跌宕起伏的命運。 在謊言、詭計、欺騙和試探中,時日流淌。 當纏綿抵不過真實,當浪漫衝不破利益,當歲月換不來真心…… 他們如何共同抵擋洶洶惡浪? 從邊塞烽火,到遍地狼煙, 他們是絕地重生還是湮冇情長? 一世相守,是夢、是幻、是最終難償?
133.3萬字8 6379 -
連載3902 章
女神歸來:七個寶寶超厲害
一場意外,她被家人陷害,竟發現自己懷上七胞胎! 五年後,她強勢歸來,渣,她要虐,孩子,她更要搶回來! 五個天才兒子紛紛出手,轉眼將她送上食物鏈頂端,各界大佬對她俯首稱臣! 但她冇想到,意外結識的自閉症小蘿莉,竟然送她一個難纏的大BOSS! 婚前,他拉著七個小天才,“買七送一,童叟無欺,虐渣天下無敵!” 婚後,他帶著七小隻跪榴蓮,“老婆,對不起,咱們一家子的馬甲都冇捂住……”
689.8萬字8.18 90712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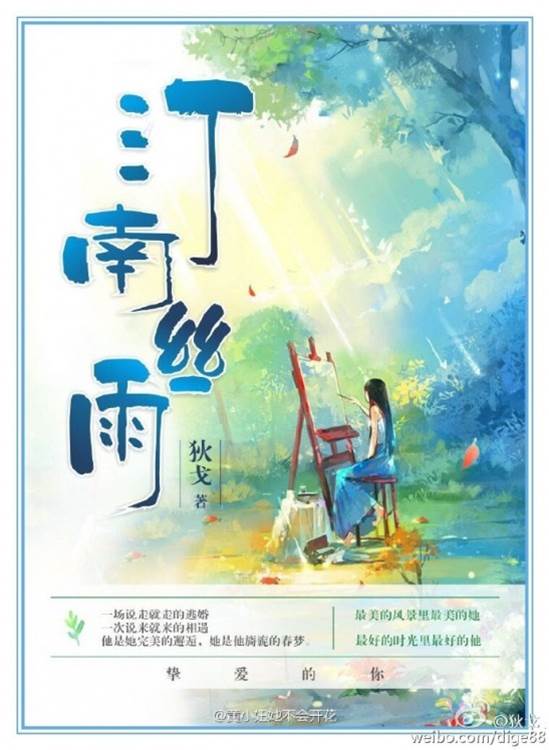
汀南絲雨
通俗文案: 故事從印象派油畫大師安潯偶遇醫學系高才生沈司羽開始。 他們互相成就了彼此的一夜成名。 初識,安潯說,可否請你當我的模特?不過我有個特殊要求…… 婚後,沈醫生拿了套護士服回家,他說,我也有個特殊要求…… 文藝文案: 最美的風景裡最美的她; 最好的時光裡最好的他。 摯愛的你。 閱讀指南: 1.無虐。 2.SC。
16.9萬字8 9132 -
完結516 章

恃寵而嬌
在愛情上,卓爾做了兩件最勇敢的事。第一件事就是義無反顧愛上鄭疏安。另一件,是嫁給他。喜歡是瞬間淪陷,而愛是一輩子深入骨髓的執念。…
89.6萬字8 5584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