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那失憶的白月光》 第82頁
他聽不到容,也只敢瞟了一眼。可那一眼,便讓他手心發涼,整晚都睡不著。
不是該在那樣的姿勢下被人著擺弄的姑娘。
那不是人之間的繾綣,那是迫、強占。
他抬眼看:“……您不愿意,對吧?”
鐘薏指尖不
自覺蜷起。
“我沒別的意思,我只是……”他嗓音低了下去,“……想著,也許您想走。”
驀地開口:“你該想清楚的。”
聲音很輕,卻冷。
“你該想的是,”嗓音輕下來,“你只是個花匠,太子若是知道……”
話未說完,已無須多言。
“你若真想幫我,”鐘薏繼續,“就當什麼都沒發生過,好好活著。別讓我再惦記一個好人會不會因我丟命。這些日子你送的東西……謝謝你,以后不要送了,我不需要。”
花匠臉白了幾分,像是要辯解,卻終究什麼都沒說。
鐘薏看著他,目澄澈:“有時候,善意也會害人。”
“我如今的日子雖然不能說好,但起碼還活著。”語氣平緩,“再怎麼不如意,也不到你來替我擔。”
說完剛想轉過,卻被他喊住。
“我師父是修繕皇宮的工匠,我知道道!”
他聲音低了幾分,眸熾熱,“我可以帶您出去!夫人,您別怕——我真能帶您走!”
“......小路在南墻后的枯井,順著井道走,五十步后能轉進一條道,盡頭是舊宮墻,那里的磚早年被換過,松得很,我可以把它撬開。”
角落里,一道黑影無聲佇立。
Advertisement
衛昭隔得遠遠的,風從枝葉間穿過,吹得耳發,卻將前方人的聲音送得分外清晰。
這段時日,他是真的在改。
鐘薏說想一個人靜一靜,他便遣走了清和院外三分之一的守衛婢,花園也不許人巡。
他想一直困著也不好,于是親自帶出去散心,在東宮各轉。
為了表示誠意,他每夜陪著睡,什麼都不做。
有時候睡得沉,呼吸在他頸窩,溫熱又輕。他卻不敢。
明明近在咫尺,只要出手就能捧住的臉,吻,住,把牢牢困在下。
可他什麼都沒做,只死死抱著。
衛昭想了很多。
他憑什麼對著退讓?
若是原本的他,大可不必為了一個人抑本。
當初他把騙到京城,本來只是想把自己喜歡的、一直試圖違背他意志的東西牢攥在手中,可后來——
后來不知從哪一刻起,蹙眉他便跟著煩躁,不吃飯他也沒了胃口。罵他,他聽著倒是平靜,可只要一紅眼眶,他就覺得心里空得發疼。
今日難得太平,他批完最后一卷奏折,想到近來神依舊郁郁。
他已學著收斂,退了一步又一步——想著若自己再低頭一點,哄一哄,抱一抱,會不會愿意看他一眼。
他沒讓人通傳,悄悄走來,只想看看一個人在做什麼。
沒想見到一幕大戲。
他的視線死死釘在那兩道影上。指尖青白,下頜繃。
鐘薏站在花圃中央,穿著他晨時親手挑的繡金薄褙子,眉眼在日下溫得仿佛能捻出水來。
站得離那賤命不過半步,聽著一字一句講如何逃、怎麼躲、哪里翻墻。
沒退。
沒拒絕。
在聽。
衛昭猛然意識到,真的還在想逃。
而且不是一個人逃,是和那個送小玩意、背地里看發呆的賤奴。
他對放在鐘薏上的每一道視線都格外敏——像是牢牢守著自己的財寶一樣守著,自然也早就留意到了這條心懷不軌的賤狗。
他什麼都知道。
只是不想說破。
他甚至忍著,想過只要不心,他便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讓那狗再看一百眼、一千眼,他也可以當作沒看見。
他已經忍到快瘋了。
可現在——
卻站在那人面前,聽著他講逃跑的路線,認真地聽著,目那麼楚楚可憐。
那人到底有什麼好?他冷冷看著他對著鐘薏出惡心的笑。
不過是條擅長賣笑的狗而已。
他站在廊下盯著他們看,目冷得像雪。
風刮過來,枝影婆娑。
“繃”的一聲,仿佛有一一直勒著他心脈的細線終于被扯斷,整個人翻涌著沉到了深淵,理智崩塌。
騙他。
一邊哭著說怕,一邊卻在背地里聽旁人教如何逃跑。
他曾經那樣低聲下氣地哀求,把姿態得那樣低,天真以為真的會給他一個機會。
結果呢?
衛昭閉了閉眼。
誰給膽子,敢拿他當笑話?
他邊的笑再也扯不出來,抿著,面寒涼得如同蛇信子過皮。
好,那就——
一個都別走了。
花匠從懷里出一張畫得極糙的舊紙卷,在袖中小心攤開。
“這是他臨終前給我的,道出來繞出冷巷,只要避過夜巡,我就能帶你出城。”
鐘薏著那張紙,心跳一滯,不知為何,忽覺四周的風都冷了幾分,好似有一寒意從腳底直往骨里鉆。
花匠還看著,眉眼間已無怯,“我知道不該想這些,可那日之后,我再也睡不著……夫人,那不是活人該過的日子!”
衛昭轉離開。
鐘薏心頭一。
他指的是哪一日,當然明白。
咬了咬,剛想開口,卻聽他接著道:“您不肯說,我也不問,可我已經親眼看到,不可能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你不要再想這些了。”努力讓聲音平穩,“我真的不需要。”
“若您哪一日真想走,只要開口——我就是拼上一條命,也要帶您出去。”
他聲音不大,卻一字不落地砸進心口。
“您別怕我被連累,我早就想清楚了!”
*
“漪漪,漪漪?”
有人在低低喚。
鐘薏睡得極沉,今夜衛昭說他不會來,樂得清閑,早早上了榻。
整個人沉進綿的被褥,夢里難得安眠,沒有尖,沒有驚恐,像是被的云朵包裹著,飄在一個遙遠的、安寧的世界里。
可悉的呼喚聲越來越近,越來越近,帶著纏人的黏意,在耳邊,一聲聲。
“醒醒,漪漪……快看看......”
蹙眉,有些不耐。
夢里都躲不掉他?
下意識翻了個,卻被人握著肩膀輕輕搖了兩下。
朦朧間睜開眼,看見衛昭倚在床頭。
他半邊子在影里,只一雙眸子亮得攝人,像是被昏黃燭火映的,沉沉地盯著看。
見醒了,衛昭俯低頭吻了吻的角。
腦中還未完全清醒,被他含糊親著,也懶得躲,直到——
一縷腥甜的味道猝不及防地竄鼻腔。
臉一下變了。
是。
現在已經對這種味道產生了本能的反應,哪怕是極淡的一,也足以讓心跳驟停。
腦中清明兩分,手推他,聲音帶著倦意與不滿:“你上什麼味道……”
一邊說,一邊坐起,下一刻才看清他。
衛昭上穿著寶藍的外袍,口大片漉漉的暗紅像是剛染上的墨跡,順著襟往下滲,目驚心。
鐘薏的心沉了一下。
原本還有些憐惜他近日眼下青黑、夜夜無眠的模樣,可這一刻,那憐惜如泡影般碎裂無痕。
“你又去殺人了?”
聲音發冷,著厭惡,“不是說過你沒沐浴不要過來?我討厭這味道!”
“不喜歡?”
衛昭被推開也不惱,低頭看自己上的跡,語氣失落,可邊詭異地牽出一抹笑來,莫名將他眉眼襯得有些妖冶。
“我還以為漪漪會高興呢。”
他聲音低低的,像是在喃喃說夢話,“你不是……一直惦記著他嗎?”
鐘薏眉頭狠狠一皺:“你在說什——”
話沒說完。
衛昭彎腰,從床邊提起一。
“啊——————!!!!!!”
鐘薏瞳孔驟,發出發出一聲撕裂肺腑的尖。
那是顆頭!!
淋淋的頭!
大腦一瞬間空白。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yanqing/18_b/bjZdC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310 章

重生有喜:皇後孃娘撩又甜
前世,鄰居家竹馬婚前背叛,花萌看著他另娶長公主家的女兒後,選擇穿著繡了兩年的大紅嫁衣自縊結束生命。可死後靈魂漂浮在這世間二十年,她才知道,竹馬悔婚皆因他偶然聽說,聖上無子,欲過繼長公主之子為嗣子。......再次睜眼,花萌回到了被退婚的那一天。自縊?不存在的!聽聞聖上要選秀,而手握可解百毒靈泉,又有祖傳好孕體質的花萌:進宮!必須進宮!生兒子,一定要改變聖上無子命運,敲碎渣男賤女的白日夢!靖安帝:生個兒子,升次位份幾年後......已生四個兒子的花皇後:皇上,臣妾又有喜了覺得臭兒子已經夠多且無位可給皇後升的靖安帝心下一顫,語氣寵溺:朕覺得,皇後該生公主了
69.4萬字8.18 60887 -
完結436 章

秀色可餐:夫君請笑納
一窮二白冇有田,帶著空間好掙錢;膚白貌美,細腰長腿的胡蔓一朝穿越竟然變成醜陋呆傻小農女。替姐嫁給大齡獵戶,缺衣少糧吃不飽,剩下都是病弱老,還好夫君條順顏高體格好,還有空間做法寶。言而總之,這就是一個現代藥理專業大學生,穿越成醜女發家致富,成為人生贏家的故事。
98.4萬字8 16809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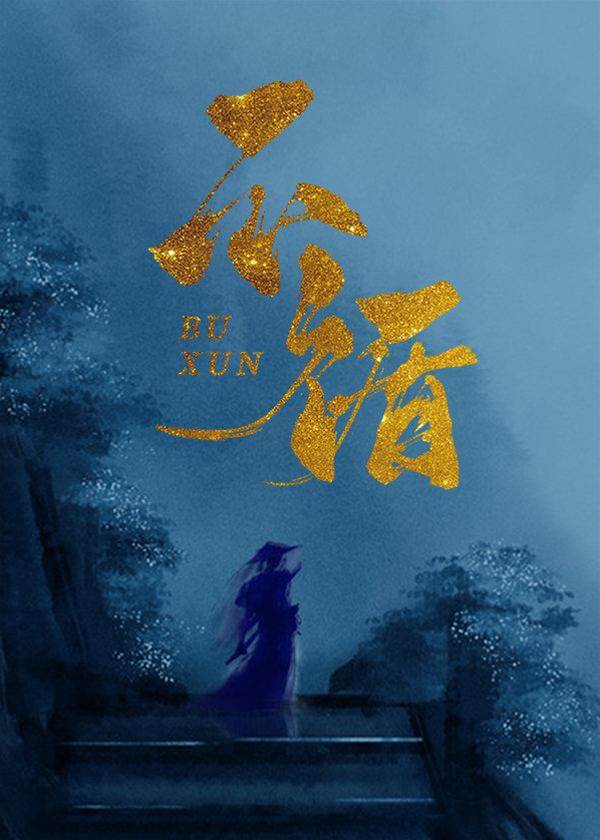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50004 -
完結194 章

曾聽舊時雨
鎮北大將軍的幺女岑聽南,是上京城各色花枝中最明豔嬌縱那株。 以至於那位傳聞中冷情冷麪的左相大人求娶上門時,並未有人覺得不妥。 所有人都認定他們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的一雙。 可岑聽南聽了卻笑,脆生生道:“世人都道他狠戾冷漠,不敢惹他。我卻只見得到他古板無趣,我纔不嫁。” 誰料後來父兄遭人陷害戰死沙場,她就這樣死在自己十八歲生辰前夕的流放路上。 再睜眼,岑聽南重回十六歲那年。 爲救滿門,她只能重新叩響左相高門。 去賭他真的爲她而來。 可過門後岑聽南才發現,什麼古板無趣,這人裝得這樣好! 她偏要撕下他的外殼,看看裏頭究竟什麼樣。 “我要再用一碗冰酥酪!現在就要!” “不可。”他拉長嗓,視線在戒尺與她身上逡巡,“手心癢了就直說。” “那我可以去外頭玩嗎?” “不可。”他散漫又玩味,“乖乖在府中等我下朝。” - 顧硯時從沒想過,那個嬌縱與豔絕之名同樣響徹上京的將軍幺女,會真的成爲他的妻子。 昔日求娶是爲分化兵權,如今各取所需,更是從未想過假戲真做。 迎娶她之前的顧硯時:平亂、百姓與民生。 迎娶她之後的顧硯時:教她、罰她……獎勵她。 他那明豔的小姑娘,勾着他的脖頸遞上戒尺向他討饒:“左相大人,我錯了,不如——你罰我?” 他握着戒尺嗤笑:“罰你?還是在獎勵你?” #如今父兄平安,天下安定。 她愛的人日日同她江南聽雨,再沒有比這更滿意的一生了。
29.9萬字8 1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