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上春漪》 第118章 118(二更) 為衆人抱薪者,不可令……
就在衆人駐足看向手中的小報時,穆蘭護著自己微微凸起的小腹,穿過人群,緩緩走上州橋。
的目在州橋下掃視了一圈,驀地揚聲道,“知微堂蘇妙漪,從商以來,謀利不忘義,廣行善舉,惠及黎民。去歲冬日,湘城破。一流之輩,孤趕赴前線,挽狂瀾于既倒……”
幾年的訟師經驗,一張口,頓時吸引了所有人的目。
萬衆矚目下,穆蘭一字一句道,“前線軍報已然嚴明,但凡援軍晚到一日,便會貽誤戰機。也就是說,若沒有蘇妙漪,湘一戰必敗!那如今的你們,難道還能在此安太平?”
李徵匆匆趕到時,就見州橋下,雀無聲,州橋上,他那懷胎數月的夫人站在最高,被不遠的燈火映照著,明眸閃爍,華灼灼。
“就是這樣一位功臣,明日卻要被押上刑場、首異……”
穆蘭也看見了橋下的李徵,目卻只停留了一瞬,便驀地移開,語調也隨之激昂,“蘇妙漪若死了,那是為誰而死?那小報上的詔令,難道是為了自己,為了的知微堂,為了蘇家的榮華富貴嗎?!是為了湘城的數萬俘囚,是為了所有百姓,更是為了大胤往後百年的國威!”
州橋下的議論聲逐漸多了起來。
穆蘭停頓了片刻,才緩緩道,“律法雖嚴,亦須順乎人。為衆人抱薪者,不可令其凍斃于風雪。明日午時,還諸位與我一起,為蘇妙漪請命……”
這番話說完,沒空再顧州橋下的那些人究竟是何反應,便扶著欄桿,一步步走了下來。
李徵回過神,快步迎了上去,一把攙住的胳膊,“……同我回府。”
穆蘭搖頭,“我還要去別……”
Advertisement
李徵加重了手掌下的力道,“這些話讓旁人去說也是一樣的,你的子不住……”
“不一樣!”
穆蘭猛地摔開他的手,冷靜了一整晚的緒在此刻有些搖搖墜,“我要自己去說,一條街一條街的說,一個人一個人的勸……蘇妙漪都要死了,我能做什麽……除了皮子,我還能做什麽?!”
說著,的眼眶便紅了,就連小腹都開始作痛,只能推開李徵,扶著路邊的磚牆一步步往前走,喃喃道,“那可是蘇妙漪……是蘇妙漪……”
忽然間,後襲來一陣風。
一個有力的臂膀橫在了後,將攬進了懷裏。接著,李徵冷冽而篤定的聲音自耳畔響起,“……好,我陪著你。”
“……”
穆蘭步子一頓,怔怔地轉頭。
李徵垂眼看,面上沒什麽波瀾,“我們去救蘇妙漪。”
這一夜,汴京城裏鬧得人喧馬嘶、風波疊起,卻沒有一點風聲傳進刑部大牢。
劉喜帶著一隊宮中衛在午夜子時趕到了刑部大牢,一刻不早、一刻不晚,驚了大牢裏昏昏睡的守夜獄卒。
“劉公公……”
獄卒們打了個激靈,“您怎麽這個時辰過來了?”
劉喜沒有理睬他們,帶著人徑直越過那些獄卒,風風火火地走向蘇妙漪的囚室。
不出劉喜所料,當他站在囚室前時,裏頭果然已經空無一人,再不見蘇妙漪的蹤影。
“死囚蘇妙漪被劫獄!你們這些廢是做什麽吃的?!”
劉喜佯怒,甚至連聽也沒聽那些獄卒解釋,便對衛下令道,“立刻搜查容府……”
“劉公公。”
一道睡意惺忪的聲打斷了劉喜。
劉喜一愣,不可置信地轉頭。
只見後的囚室裏忽然亮起了燭燈,而本該被容玠帶走的蘇妙漪此刻就坐在靠牆的床榻上,好整以暇地著他,甚至還懶洋洋地打了個哈欠。
“都這個時辰了,您還這麽興師衆地來刑部大牢?是想做什麽?”
劉喜蹙眉,終于看了一眼獄卒。
“蘇娘子說這間囚室有些異味,所以今夜特意換了一間……”
獄卒回稟道。
“我是明日便要斬首的人,他們滿足我這麽一點小心願,不算過分吧?”
蘇妙漪起從暗走了出來,隔著柵欄對劉喜笑道。
劉喜瞇著眼打量,“明日便是死期,你倒看得開。”
“人都是要死的,劉其名會死,我會死,公公你也遲早會有這麽一日。”
劉喜眼裏掠過一寒意,隨即示意獄卒將囚室的門打開。
獄卒有些遲疑,下意識看向蘇妙漪。見頷首,才拿出鑰匙,打開了囚門。
劉喜走進囚室,往桌邊一坐,給自己斟了一盞茶。
蘇妙漪挑了挑眉,在另一側坐下,“公公這是打算今夜在牢裏守著我。”
劉喜心有算,也不再遮掩,“守著你,容玠還能逃得掉麽?”
蘇妙漪眼睫微垂。
的確,今日費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勸住了容玠……
“公公與容家,究竟結了什麽仇什麽怨?此番將妙漪送上刑場,有幾分是為了劉其名,又有幾分是為了容玠?”
劉喜意味不明地看了一眼,陷沉默。
蘇妙漪嘖了一聲,“我都是將死之人了,還有什麽是聽不得的?還是說,公公就這麽忌憚我,都到了這種時候,還怕我逃出生天,壞了您的好事?”
“拿話激我。”
劉喜冷笑一聲,“咱家在宮中浸了這麽些年,若還能被你一個黃丫頭的三言兩語就哄得昏頭轉向,那也是白活了。”
蘇妙漪“哦”了一聲,既不失,也不焦心。
知道,像劉喜這種人,當年既能不聲地造出“矯詔案”,心中一定是得意至極的。可這些年,他一直埋藏著矯詔案的,無人炫耀,無人顯擺。
易地而,若是劉喜,憋了這麽些年,也該憋得夠嗆了……
“聽說去年,你們知微堂在街上支了個攤子,凡是來往的路人,一個故事便能換一盞好茶。”
也不知過了多久,劉喜果然開口了,“咱家今晚喝了你的茶,便賞你個故事。”
蘇妙漪勾,“洗耳恭聽。”
劉喜揮揮手,屏退了囚室外的所有人,然後才緩緩道,“幾十年前,汴京街頭有一對雜耍賣藝的父子。可那做爹的,并不拿自己的兒子當人,只當他是個賺錢討賞的猴兒……”
線昏昧的囚室裏,劉喜側過臉,手朝自己脖頸比劃了兩下,”他就將鎖鏈這麽捆在他兒子的脖子上,演得好了扔點殘羹剩飯,演砸了便是一頓拳腳。後來有一日,這個爹將兒子揍得奄奄一息、就剩一條命的時候,有一輛轎在他們旁邊停下了……”
燈火闌珊,映雪如晝。
轎中跳下來一個錦年,幾步沖過去,推開了那揚起拳頭的雜耍藝人,“住手!”
年護住那與他年歲相仿、卻捆著鎖鏈、遍鱗傷的伎,“你沒事吧?”
“老子教訓兒子,要你管?滾一邊去!”
那人正在氣頭上,甚至要朝年揮拳,然而下一刻,就被幾個侍衛扣住了胳膊,彈不得。
“天底下,哪個做爹的會將兒子打這幅模樣?”
錦年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轉向那伎,“他真的是你爹?”
伎的一只眼紅腫得像個撥了殼的蛋,只能用剩下的那只眼看向年,點了點頭。
“錚兒。”
一道沉穩而清越的喚聲從轎傳來。
下一刻,那名喚“錚兒”的年便攙著伎走回了轎邊,“爹,你看他都被打什麽模樣了……”
轎簾掀開,坐著一個著紫服,溫文爾雅、貴不可言的老爺。
看清轎中人的臉孔,雜耍藝人頓時嚇得都了,往雪地裏一跪,“容,容相!”
伎怔怔地看了一眼自己跪下的爹,又看了一眼轎中人,也踉蹌著跪下。
“爹……”
年的容雲錚心有不忍,央求容胥,“這孩子太可憐了,我們救救他吧……”
容胥思忖片刻,從袖中取出一個錢袋,遞給了那雜耍藝人,“天寒地凍,討生活不容易。”
那人先是震驚,接著便是狂喜,不斷地在雪地裏磕頭,“多謝容相,多謝容相!”
忽地想起什麽,他又跌跌撞撞地沖了過來,將自己的兒子一把拎起來,推向容胥的轎輦,“容相的恩德,小人無以為報……小人唯有一子,願賣給容家為奴!”
容胥和容雲錚皆是一愣。
容雲錚對上那伎黑白分明的雙眼,咬咬牙,轉頭看向容胥,“爹……”
可這一次,容胥卻沒有依從他,而是擺擺手回絕了,“容家不缺這麽一個奴仆。你拿著錢,去做些生意,往後,莫要再為難孩子了。”
“是,是……”
那人接連應聲,又拉下還傻站著的伎,“還不多謝恩人!”
伎跪下,磕頭,麻木地重複著,“多謝恩人。”
待他再直起時,容府的轎子已經離開,可容胥與容雲錚父子倆的談話聲卻被北風吹進了耳裏……
——爹爹為何不願收留那伎?他要是去了我們府上,定會過得好些。
——若換你,是更想要榮華富貴,還是更想和自己的爹在一起?
——那自然是和爹爹在一起!錚兒才不要和爹爹分開!
——做別人的兒子,總比做一家的奴才要好。
“蘇老板,你說呢?”
劉喜忽而轉向蘇妙漪,問道,“一個賤民的兒子,和容府的奴才,哪個更好些?”
他的面容在燭火映照下忽明忽暗,怪陸離。
蘇妙漪蹙眉,沒有回答劉喜的問題,反而追問,“後來呢?”
“後來……那雜耍藝人拿了錢,沒去做什麽生意,而是進了賭坊。一晚上的功夫,就輸沒了,還欠了不債。為了抵債,他把自己的兒子送進了宮,做太監……哈……哈哈哈……”
劉喜的笑聲在仄的囚室裏被拉長、壁、回響,變得格外詭瘆人。
蘇妙漪聽得不寒而栗,忍無可忍地站了起來,朝遠離他的方向退了幾步,“那做爹的是個畜生,與容胥父子有何幹系?”
“怎麽沒有?!”
劉喜的笑聲戛然而止,猛地看向蘇妙漪,眉眼猙獰而可怖,“怎麽沒有幹系?要是他們當初願意收留我,讓我去容府做個奴才,我就不會被賣進宮……不會被淨……不會變一個人人磋磨的死太監!”
他的嗓音尖利而,就好似一只張牙舞爪的怨鬼。
“憑什麽?憑什麽同樣是人,同樣是父子,他容胥和容雲錚就是父慈子孝,而有些人就只能每日挨打,被當做牲畜一樣取樂換錢?!容雲錚不是說了麽,他們父子永遠都不分開……那我便全他們,他們一同下地獄去吧!”
“……”
蘇妙漪僵在原地,表有些不可思議。
很快,劉喜便斂去了面上失控的妒意和怒火,取而代之的,卻是大仇得報的痛快。
他回到桌邊坐下,複又端起茶盞,小啜一口,輕飄飄道,“升米恩、鬥米仇,他們千不該萬不該,就是沒有將好人做到底,把我帶去容府……”
猜你喜歡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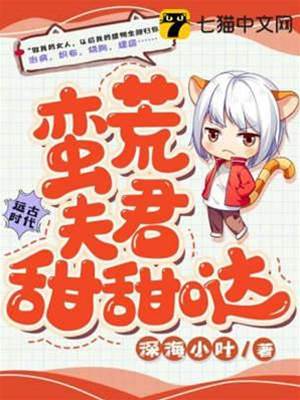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8714 -
完結195 章

我見貴妃多嫵媚
前世,蘇輕窈不受寵,光靠身體硬朗熬死了兩任帝王,做了皇貴太妃。 結果眼一閉一睜,她又回到剛進宮的那一年。 蘇輕窈:???當慣了皇貴太妃,現在的生活她不適應了! 她想要提前上崗! 一開始——陛下(皺眉):走開,休想引起朕的注意。 到後來——陛下:真香。 雙初戀小甜餅,1VS1,真香警告,架空不考據無邏輯=V=求收藏求評論~我的微博:@鵲上心頭呀歡迎關注~我的文~:古言甜寵已完結~《貴妃如此多嬌》宮斗小甜餅《宮女為後》宮斗小甜餅《農女為後》種田小甜餅接檔文求收藏~《你是我第十顆星》現言甜寵正在存稿《沖喜小皇后》古言甜寵正在存稿
59.5萬字8 7523 -
完結303 章

福寶小嬌妾/嬌養王府癡妾/糯嘰嘰小寵妾
湯幼寧是個笨蛋美人,反應慢,不聰明。 父親摔馬過世後,嫡母瞅着她這一身雪膚玉肌,獻予王府做妾室,替兒子謀個前程。 王府金山銀山,只要她安分乖順,這輩子穩了。 薄時衍受先帝臨終託付,成爲攝政王,權勢滔天,二十好幾無妻無子,還患有頭疾。 王府後院養了一眾美人做擺設,他幾乎從不踏入。 直到某天發現,滿庭的鶯鶯燕燕中混了一個小白鴿,又白又軟又乖。 在她床上,徹夜安眠;埋首懷裏吸一口,頭疾不治而愈;更甚者,她沾手的印章頒佈政令,通通好運加持。 湯幼寧很有自知之明,所求不過是養老。 不料——先是被強佔了一半床位,而後夜裏睡眠時間大幅度縮減。 被欺得狠了,她感覺好累,誰知這人高馬大的男子,語氣比她還可憐: “一把年紀尚未當爹,圓圓憐惜憐惜我……” “小世子孤零零的,是不是想要妹妹了?” 薄時衍:他的圓圓太好哄了。 這一哄,就是一世。
48.3萬字8.53 25914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