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葡萄熟透》 第1卷 第64章 她只舍得討厭他這一分鐘
車里徹底靜了下來。
江黎愣了好一會,沒想到是這個回答,回過神,心底不知什麼緒,只能著平淡的嗓音道一句“節哀”。
江明軒搖了搖頭,手指一下一下輕捻著:“他就是年紀大了,到時候了,沒什麼罪,我看得開。”
江明軒從車里撈過一個牛皮紙袋信封,里面是一份文件和厚厚一沓洗好的照片。
他翻開來,一張張出又墊在下面。
“這些都是你上了高中以后,我讓人去拍的照片,老爺子拉不下臉面,著不肯說想你,彌留之際的時候又總是一張張翻著看,邊看邊說你長得有多像我哥。”
“老爺子這樣的人到死了都是的,他問你后不后悔,結果到了后悔的人是他自己。”
江黎一愣,目順著車窗看向不遠在咖啡廳排著隊的白領。
所以那時經常看到,是因為在拍的照片。
“江家這一輩除了你以外,再沒有別人了。走之前,他把江家的產都分了,連帶著留給你父親的百分之五十他沒,還多勻了百分之十五給你。”
江明軒把那份文件拿出來遞到江黎面前。
“委托做資產證明的律師已經找好了,只要你在囑上面簽個字,江家大部份的產業就都留給你了。”
江黎看著江明軒手中的囑繼承文件沒接。
Advertisement
抬頭看著江明軒,男人神溫和,年近五十的年紀眼底生出皺紋,眉眼中帶著滄桑,其中夾雜著一頹然。
“謝謝江先生好意了,但我不能收。”
江黎的話他似乎早就猜到。
“你子一直是這樣,好像從別人那里得到了什麼就虧欠了什麼。阿黎,世界上哪有那麼多拎得清的事?”
江明軒靠在椅背上,有些疲累。
“我很多年不回京北了,我知道你不會收江家留給你的東西,但我就抱著僥幸的心思想著萬一呢。”
他抵著額頭藏住眼里的緒:“你爺爺臨走前,整夜整夜的做夢夢見我哥,夢見他那麼好脾氣的人一次次和你爺爺發脾氣,氣他沒有照顧好他最寶貝的兒。他醒了不認人,只知道喊我哥的名字,說他知道錯了,是他固執了……”
江明軒明顯紅了眼,他撇過頭遮掩這種緒。
“阿黎,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哭,他那麼剛強固執的一個人,我第一次聽到他承認他錯了。”
江黎的呼吸有些沉,口的難,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對那一位只見過一面的固執老頭沒有什麼印象,在記憶里,甚至記不清長什麼樣子。
但江明軒提起,提起老爺子,提起父親,又不免有些難過。
人真奇怪,緣也真奇怪。
江明軒抹了一把眼睛,將眼淚含下去:“說得多了,知道你不聽。我就是憋了太久沒人說說話了,見見你,和你聊聊天就怎麼都好了。東西我留著,不管你怎麼想,只要你有一天想要,就算是再多我都愿意給你。”
“阿黎,我是你叔叔,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向你爸爸對你一樣。”
江明軒一輩子沒結婚,江明恩死了,江家所有的事都落在了他肩上。
他被迫從那個吊兒郎當的刺頭青變扛起家族的頂梁柱。
江老爺子去了,整個江家就剩下他自己了。
江黎不認他,和他說說話也是好的。
他知足了。
江黎看懂了江明軒的緒。
下車前,回頭看了一眼江明軒,謝過他的好意。
說:“我懂你,你跟我一樣,只是想爸爸了而已。”
江明軒愣了好一會,突然笑紅了眼。
“對,都一樣。”
他了西裝口袋,突然拿出一張褶皺發舊的紅鈔票。
“叔叔來見你沒有空手的道理,江家的東西你不要。這個,能收下嗎?”
江黎看著他指尖夾著的那張紅鈔票,明明隔著近二十年的緒,突然穿過歲月,流轉到了現在。
那時很開心才對。
江黎接過那張紙幣:“謝謝。”
-
京北就快了夏,最后一枝玉蘭樹就快要凋落干凈,白的花瓣隨著風飄零,就像是下了一場春雪。
江黎的手蜷在外套里著那張紅鈔票,羅靳延的電話打過來時,吞吐了好幾次氣息才接通。
“羅靳延。”江黎的語氣有些不對勁。
電話那頭的男人停頓一秒:“你在哪?”
江黎仰起頭看著花枝,花瓣零落的一瞬間,飄飄然蓋住的眼。
“我在一棵樹下,”江黎說,“玉蘭樹。”
說這句話時幾乎要哭了。
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哭什麼。
是哭自己吃了多苦,熬了半輩子熬出了頭,突然有人說;還是哭因為那一點緣牽絆在糊里糊涂和倔強中被消磨。
什麼時候變得這麼了?
人真奇怪,真奇怪。
羅靳延蹙著眉,捕捉到的哽咽。
“不開心?”
江黎回答的十分坦誠:“是啊,不開心。”
“為什麼?”
踩著腳下那一株玉蘭花,它被早雨打進泥土里,臟了,破了。
“羅靳延,我討厭這種一直見不到你的覺。”
藏了兩個月的思念在這一刻傾瀉,藏不住了,也不想藏了。
羅靳延聽出此刻是真的難過,他溫聲問,語氣放的了些。
“有多討厭?”
就這一句,江黎就忍不住紅了眼。
眼淚模糊了視線,只看得到玉蘭花的白。
沒出息,怎麼就這一句,就鼻也酸心也酸。
“很討厭很討厭。”
江黎說:“但這對我來說好像很難,羅靳延,我只舍得討厭你這一分鐘。”
就一分鐘的時間,留給對他的埋怨。
羅靳延輕笑一聲。
小孩子一個。
他說:“好,我給你這一分鐘,就只有這一分鐘。”
羅靳延默默數著。
江黎眼底的淚蓄起,還是太倔強,不想哭。
他騙,明明說好了會盡快,卻生生等了兩個月。
他分明知道不喜歡等。
他怎麼舍得等。
電話那頭傳來低沉的聲音:“一分鐘到了。”
江黎錯愕,眼淚還沒來得及落下。
“這麼快?”
“不快,我一直在等這一分鐘度過。”
江黎含著淚,聽著聲音穿過聽筒,走進風聲。
羅靳延說:“回頭,我在你后。”
猜你喜歡
-
完結2426 章

總裁的嬌寵妻
她本是名門千金,卻一生顛沛流離,被親人找回,卻慘遭毀容,最終被囚禁地下室,受盡折磨,恨極而亡。 夾著滿腔怨恨,重生歸來,鳳凰浴火,涅槃重生。 神秘鑰匙打開異能空間,這一世,她依舊慘遭遺棄,然置之死地而后生,她不會再重蹈覆撤,她要讓那些曾經踐踏過她的人,付出代價。從此以后,醫學界多了一個神秘的少女神醫,商界多了一個神秘鬼才....
243.7萬字8 214071 -
完結303 章

豪門盛寵之陸總寵上癮
他是海城最尊貴的男人,翻手可顛覆海城風雨,卻獨寵她一人。 “陸總,許小姐又有緋聞傳出。” 男人眼睛未抬半分,落下兩字“封殺。” “陸總,許小姐想自己當導演拍新戲。” “投資,她想要天下的星星也給她摘下來。” “陸總,許小姐不愿意結婚。” 男人挑眉抬頭,將女人強行連哄帶騙押到了民政局“女人,玩夠了娛樂圈就乖乖和我結婚,我寵你一世。”
67.5萬字8 27643 -
完結388 章

愛你日久彌深
叢歡只是想找個薪水豐厚一點的兼職,才去當禮儀小姐,不料竟撞見了自家男人陸繹的相親現場。叢歡:陸先生,你這樣追女人是不行的。陸繹謔笑冷諷:比不上你,像你這樣倒追男人的女人,只會讓人看不起。雙份工資打給你,立刻離開,別在這礙眼。叢歡:好好好,我這就走,祝你成功追美、永結同心。陸繹:就這麼將自己心愛的男人拱手讓人,你所謂的愛果然都是假的。叢歡忍無可忍:狗男人,到底想怎樣!
74.5萬字8 578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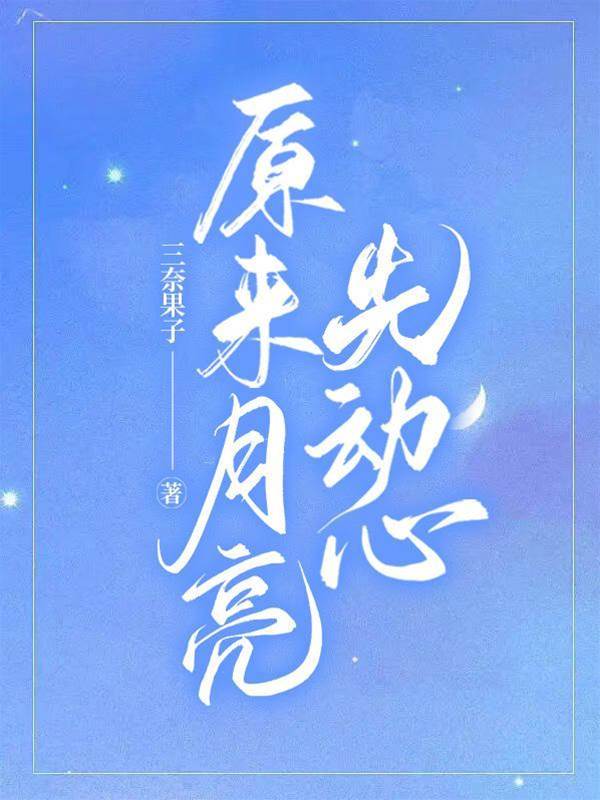
原來月亮先動心
【已簽約出版】原名:《喝醉後,我錯撩了閨蜜的小叔》【蘇撩 甜寵 教授 七歲年齡差 校園 救贖】【蘇撩腹黑小叔X古靈精怪少女】江落是十足的手控,為了一張手照,搭訕了一位帥哥,不料事後發現,對方居然是她閨蜜的小叔!江落腰板挺直,站姿乖巧:“小、小叔好。”……多年後,南大突然傳出生物學係的高嶺之花傅教授已經結婚的謠言。同事:“傅教授,這些謠言都是空穴來風,你別信……”“澄清一下,這不是謠言,”傅紀行冷靜補充,“我確實結婚了。”!!!江落跟傅紀行扯證時,她正讀大四。扯完證回去的路上,男人手裏拿著小本子,溫聲提醒:“喊了我這麼多年的小叔,是不是該換一下稱呼了?”“什、什麼稱呼?”“比如……”男人的吻落在她唇上——“老公。”
21.2萬字8 8278 -
完結506 章

離婚止損
兩人的娃娃親在景嶢這裏根本沒當回事,上學時談了一段張揚且無疾而終的戀愛,迫於家人的壓力,最後還是跟褚汐提了結婚。兩人結婚之後像普通人一樣結婚生女。外人看來雙方感情穩定,家庭和睦,朋友中間的模範夫妻。兩人婚姻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褚汐打小性格溫柔,品學兼優,自從知道自己跟景嶢有娃娃親的時候,就滿心歡喜的等著兩人結婚,總以為兩人一輩子都會這樣在一起。偶然的一天,聽到景嶢用一種意氣風發且張揚的聲音跟自己的母親說他談戀愛了,有喜歡的人,絕對不會娶她。此後再見麵,褚汐保持合適的距離,遇見了合適的人也開始了一段戀愛。兩個人的戀愛結果均以失敗告終,景嶢問她要不要結婚,衝動之下褚汐同意了。衝動之下的婚姻,意外來臨的孩子,丈夫白月光的挑釁,都讓她筋疲力盡。心灰意冷之後提出離婚,再遭拒絕,曆經波折之後達到目的,她以為兩人這輩子的牽掛就剩孩子了。離婚後的景嶢不似她以為的終於能跟白月光再續前緣,而是開始不停的在她麵前找存在感!
99.2萬字8.18 228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