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哭那個小呆子》 第一百三十八章
許秦烈看著那只麻雀就想起招財。
他拿著服去浴室洗了個澡,把頭發吹干后躺在床上。
迷迷糊糊睡了一覺,醒來發現外面天都黑了,就這樣又度過了一天。
明天要上課了,許秦烈在床上賴了一個小時,才慢慢從床上爬起來,去客廳倒了杯水喝,門鈴響了起來。
他走過去開門,唐文俊站在門外,手上拎著一袋東西。
“我去,你這頭發,剛睡醒?”唐文俊問。
許秦烈抬手在頭上抓了抓,吹干頭發就去睡覺睡變形了。
他敷衍地嗯了一聲,側讓他進來。
唐文俊在鞋柜那里換了雙一次拖鞋,這拖鞋是上一戶租客留下的,這屋里除了許秦烈一個人的拖鞋沒了。
“我買了點燒臘,還有啤酒,喝點不?”唐文俊說:“我剛從家里躲出來,你可不能再讓我回去了。”
經過一年多的相,他和許秦烈比之前更了點,偶爾會來串個門一起吃個飯。
許秦烈繞到臥室里拿了包煙和打火機出來,坐到桌子上邊煙看唐文俊把袋子里的東西拿出來擺上。
鴨脖、燒鵝、架,還有一些鴨鵝的其他部位,他說不上來。
許秦烈盯著看了半晌,一煙完他想吐了,“噌”地從椅子上上起來沖進廁所里吐。
唐文俊傻眼了,“我去!”他趕撂下筷子跑到廁所里,“不是吧,你丫懷孕啊,反應這麼大。”
Advertisement
許秦烈吐了好一會兒,閉著眼睛把那些嘔吐全部沖掉,唐文俊給他包紙巾遞過去。
他胡抹著,拿著洗漱杯刷牙,把里面的異味刷走。
重新回到回到桌旁坐著。
唐文俊看他的臉有些擔心,“要不要上醫院看看啊,臉很白。”
許秦烈虛弱的搖搖頭,“不用,老病了。”
以前的鋼鐵胃現在也變得無比脆弱,他想不起來什麼把胃搞壞的,好像是從學校搬出來之后,經常熬夜研究游戲,
一熬就是通宵,在滴水未進的況下,嗓子都頂不住冒煙了,更別提胃了。
唐文俊已經把桌上的東西全部收起來了,拿著鑰匙招呼他,“走,咱出去吃。”
許秦烈剛想拒絕,被唐文俊連拖帶拽地走了。
出了門,許秦烈才想起來手機什麼的都沒帶,著眼皮罵了唐文俊一路。
唐文俊被他念得頭疼,從兜里拿了顆棒棒糖拆開塞進他里,“別叨叨了,到地兒了。”
下車之后唐文俊領著他去了一家蒼蠅館,店面很小,好在沒什麼人。
許秦烈含著糖抬頭看了看,招牌上寫了倆字:鄭記。
什麼破店,也沒寫吃什麼的,走進去才知道是吃火鍋的。
這個天氣不冷不熱的,神經病才吃火鍋,許秦烈轉想走,唐文俊預判了他的預判,快速勾住他的手臂飛似的沖進店里。
許秦烈想跑都來不及,認命地坐下去。
唐文俊拿著菜單一通點,也沒問許秦烈要吃什麼。
“這地兒我經常來,味道很不錯。”唐文俊說:“我點的清湯,你胃不好不能吃辣。”
許秦烈哦了一聲,沒手機玩只能無聊的撐著臉四看。
這店的衛生還是好的,就三桌人在吃,還有一兩個服務員在走來走去。
“對了,那個比賽的事兒你怎麼打算的?”唐文俊問。
許秦烈收回視線,落到他臉上,“什麼怎麼打算?”
“就導員說的啊。”唐文俊倒了兩杯熱茶,“咱宿舍就挑了你和楊柯,你不去的話誰去?”
許秦烈想起來這回事兒了,他學的游戲設計專業,這個專業還是老媽去和許國勛商量,不是商量,
可以說是請求了,磨了一個月許國勛才答應的。
過段時間有個比賽,因為從小接游戲方面,導員也看出了他多有點天賦,問他下個月有沒有興趣參加比賽。
因為比賽需要兩兩一組,就挑了同宿舍的楊柯,許秦烈沒答應,也不是很想去。
“再說吧。”許秦烈回答。
這幾天楊柯確實也有找過他幾次,不過他都以在忙空了再說為由拒絕。
這種比賽是很多學院一起聯合辦的,榮譽獎可能也只是個學校弄的獎杯,沒什麼含金量,他不是很在意。
唐文俊見他一副懶懶散散的樣子便沒再問了。
服務員上菜快的,鍋底早就端上來了,唐文俊手把比較難的菜先倒進去燙。
許秦烈趁他還沒下菜之前先舀了一碗湯出來喝,湯還冒著熱氣兒,一碗下去胃好了。
他拿著筷子開始吃,唐文俊邊燙邊吃。
兩人都沉默的,許秦烈和唐文俊也就比另外兩個舍友一些,但也不是每次都能聊得上話題的。
吃到一半,門外又有人進來了,服務員熱地迎過去,“幾位,吃點什麼鍋?”
許秦烈沒轉過頭,背對著門聽到一道聲音,“你們這兒的招牌是什麼?”
許秦烈愣了一下,撂下筷子看過去,正好那人看了過來。
“臥槽!”那人發出一聲尖銳的鳴聲,隨后在眾人都還沒反應的況下沖向許秦烈。
“臥槽,哥!”這瘦不拉幾的猴子,頭上還戴著一頂洋不洋,中不中的土帽,赫然是王培!
王培激得差點蹦上他們那一桌的桌子,“哥,是我啊,王培!”
許秦烈也是頗為意外了,拉住他的手不讓他蹦,“我知道我知道。”
王培臉都紅了,手把頭上那頂丑帽子拽下來,出一整張臉。
沒什麼變化,不過氣比之前稍微好點了,貌似長胖了一點。
王培抱住許秦烈,難得的有些哽咽,“哥,沒想到在這兒遇到你。”
許秦烈拍拍他的肩膀,示意他松開,“咱坐下聊。”
王培點頭,“你等我一下,我過去跟幾個朋友說兩聲。”
他轉往剛才站在他后的那幾個人說了一會兒。
唐文俊看了王培一眼,又扭臉看許秦烈,表非常疑,“你弟弟?”
許秦烈一口水嗆在中,咳了好幾聲回他,“不是。”
“那他一個勁兒的喊他哥哥!哥哥哥哥!”唐文俊著嗓子說。
許秦烈笑罵了一聲:“滾。”他頓了頓,“是朋友,習慣這麼了。”
王培一直都是這麼他的好像,想起一開始還是抗拒的,后面是聽習慣了。
王培說完就走了過來,拉了把椅子坐到許秦烈右手邊,剛坐下就說:“知道你在這里我就早點過來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71 章

且以深情共余生
相似的聲音,相似的容貌,遇見了同一個他。兜兜轉轉,走走停停,時光不改蹉跎。如果上天再給她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一定奮不顧身愛的更加用力!
50萬字8 9205 -
完結378 章

玄門回來的假千金又在擺攤算卦了
肖梨在玄門待了一百年,同期進來的那條看門狗小黑,都已經飛升上界,她還只能守著觀門曬太陽。老祖宗顯靈告訴她,“肖梨,你本來自異界,塵緣未了,若想飛升,还得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却凡尘杂事,方可勘破天道!” 回到现代,肖梨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这一世,没有留念,两手空空跟着亲生父母离开肖家。 圈内人都在等着,肖梨在外面扛不住,回来跟肖家跪求收留。 却不想…… 肖梨被真正的豪门认回,成为白家千金,改名白梨。
64.4萬字8 60458 -
完結189 章

荒腔
沈弗崢第一次見鍾彌,在州市粵劇館,戲未開唱,臺下忙成一團,攝影師調角度,叫鍾彌往這邊看。 綠袖粉衫的背景裏,花影重重。 她就那麼眺來一眼。 旁邊有人說:“這是我們老闆的女兒,今兒拍雜誌。” 沈弗崢離開那天,州市下雨。 因爲不想被他輕易忘了,她便胡謅:“你這車牌,是我生日。” 隔茫茫雨霧,他應道:“是嗎,那鍾小姐同我有緣。” 京市再遇,她那天在門店試鞋,見他身邊有人,便放下了貴且不合腳的鞋子。 幾天後,那雙鞋被送到宿舍。 鍾彌帶着鞋去找他。 他問她那天怎麼招呼都不打。 “沈先生有佳人相伴,我怎麼好打擾。” 沈弗崢點一支菸,目光盯她,脣邊染上一點笑:“沒,佳人生氣呢。” 後來他開的車,車牌真是她生日。
28.8萬字8 17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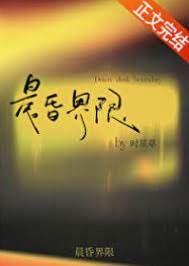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