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情泰蘭德》 第1卷 第51章 約會
覺得下一秒肯定有事發生,實在抑制不住好奇,在屋子里躊躇一陣,在書進門那刻就邁了出去,書給端來了熱茶,謊稱自己要去廁所。
路過那間會議室,百葉窗從里面被封得死死的,門也關得牢,幾乎沒辦法聽。
觀察到和茶水間相鄰有一塊臨窗的蔽角落,那里側對會議室的玻璃有一塊百葉窗折了半塊,環視四下無人,便假裝在那里欣賞樓下風景。
這里簡直是天然的窺場所,甚至懷疑是之前有人故意做的手腳。
這層樓普通員工不多,又已經七點多,幾乎沒人還在辦公室,這讓心里放松不。
里面寬闊锃亮的大理石磚上跪著一個男人,背上的服有兩條痕,顯然已經被那不起眼的高爾夫球下了手。
那人背對著,看不清長相,但此時瑟瑟發抖,里一直說著不知。
昂威站在面朝大街的落地窗前,手里握著那帶的高爾夫球桿,還有一支煙裊裊燃在他指間。
坤達又上去踹了一腳,脖子上的鏈子晃擺,那人倒在地上又迅速地爬起來跪好。
坤達跪下來,手指抬起男人下,牙齒間含笑,“再問你最后一次,那晚在華欣半路襲擊我們的人到底是誰,當天的行蹤只有這麼幾個人知道,給你機會你不要是吧,這麼著急去黃泉路喝孟婆湯,我可以全你。”
男人瘋狂搖頭,臉上的水四濺落,“達哥,那晚爺的行蹤真的不是我泄出去的,我跟了你一年多,我什麼人你還不了解,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求你明察。”
Advertisement
這人字字懇切,看起來確實不像撒謊的樣子,但是哪個人會掛在上說我是叛徒呢,大家都不傻。
坤達顯然不信,他站起罵了一句臟話,對那人又是踢又是踹,打得地上的人抱頭大喊。
昂威立在窗邊煙,側頭平靜地讓坤達住手,他將煙丟到旁邊的茶杯中,頓時滋滋冒響。
他坐回面對地上那人的一把椅子,了發倦的眉心,“諾執,這事兒你怎麼看?你覺得是誰的人。”
他突然的發問讓坤達和諾執都不著頭腦,諾執一愣,說我也不好說,覺不知道是哪個野幫的,也許趁機想搞出點大名堂來,但消息不知道是怎麼放出去的。
坤達擼了擼袖子,“要我說啊,肯定是他娘的德賽找的人,又不敢來的,所以找的臉生的雇傭兵,因為那幾個場子的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想對爺下手。”
昂威向后倒靠,眼底發沉,他慢悠悠地翹起二郎,說了一句都不是,我猜是他老子上面那位。
坤達一臉震驚,“賽欽背后的老板?你的意思是軍方的人。”
昂威玩弄手里那鈦合金球桿,似乎對自己的猜想十拿九穩,“他上面那位老板的確和軍方有關系,但是不是軍方的人,還說不清。”
“爺,你心里已經有了打算?”坤達問。
他將球桿豎起,手將上面順流而下的抹凈,惻惻地笑,“有人坐不住了,親自下場,好戲才剛開始。”
聽到這里,黛羚包里的手機響起,慌之中趕劃掉,也不敢再聽下去,慌忙去洗手間繞了一圈,然后回了辦公室,昂威進來的時候,已經平復了起伏的心,裝作一臉不知。
他手里那球桿嶄新,似乎剛才只是一場夢,他反手關了門,將它重新進高爾夫球包之中,向走過來的每一步都讓為之一。
“了嗎,陪我去吃飯。”
他笑得溫,將拉到懷里,似乎沒注意到冰冷發僵的。
去酒店的路途十分鐘,在停車場,他著在車里磨了接近一個小時,出來時的口紅幾乎都到了他的上,一眾手下懂規矩,包圍四周,不出一隙。
包廂吃到半途,一個人著高腳杯敲了敲門,黛羚抬頭,是孟季惟,短發清爽,斜斜倚在門邊瞧著屋兩人,晃著手里的酒。
“一起喝一杯,介意麼。”
說完泰然自若地走進包廂,眼睛在兩人之間梭巡,此時昂威正夾菜給黛羚,他掀眼皮看清來人,不聲放下筷子。
“在外面看到你的車,我就知道你在,看來我猜對了。”
孟季惟一只手倚在椅子上,致的臉上帶著八卦之意,握著酒杯那只手出一手指,瞇眼看黛羚,“我們見過?”
黛羚放下筷子,心里盤算著那天在悅椿莊應該沒有注意到,正準備回答的問題,手卻被旁邊那人過去握住,他渾厚的嗓音不不慢開腔,“怎麼,孟老板在這公辦?”
孟季惟看著兩人握的手發笑,說在隔壁有應酬,看到門口的保鏢就知道你在這,說話之間眼神一直朝黛羚臉上瞟。
拉開椅子坐下來,朝昂威眼,“早知道你在約會,就不來打擾你了。”
昂威不理,攥手攥得發。
孟季惟打趣,“小姐貴姓。”
黛羚答,姓黛名羚,上次在你的回國派對多有打擾,算是見過一面。
孟季惟說我想起來了,你和我表弟一起來的。
說完這句話,兩人眼都瞧了瞧旁邊的男人,不一樣的是孟季惟是故意的,而黛羚是用余瞟他。
昂威臉上沒什麼表,似乎并不在意。
孟季惟為人很爽朗,幾句話就逗得黛羚發笑,答應說下次一起吃飯。
這時,門口臉生的保鏢敲了敲門,昂威讓他進,那人附在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男人挑了挑眉,說在哪,保鏢回在大堂,正要走。
昂威問黛羚吃好了嗎,點了點頭。
“你不舒服,再吃些想吃的,就早點回去休息,回別墅還是回公寓,跟司機說一聲,你做主。”他耐心地拍了拍的背,說他去忙點事。
說完,他眼神掃過孟季惟,互相的默契不用多說,起一同出了門,讓那個保鏢留在門口候著。
臨走前,孟季惟還說了一句,怎麼把你朋友一個人留在這里,多不紳士。
昂威只是使勁兒推了一把,隨手關上了門。
黛羚問那個保鏢他們去見什麼人,那人知道什麼份,也不敢多,就說爺的一個人。
吃完拿起潔白的餐布了,跟保鏢說想回家,那人領著出了門,在大堂環視搜尋沒有見到昂威他們,想著應該是換了地方。
出門,保鏢為開了車門,目送一輛遠去的黑轎車,后座垂出男人戴著指環那只手。
后面一輛車,門為孟季惟擋住車頂,扔了煙也鉆了進去,這輛車迅速跟上前面昂威的車,消失在了霓虹夜之中。
黛羚看了神,保鏢提醒才回過神來,跟船叔說回自己的公寓,這幾天不舒服,昂威看來也有別的要忙的事,可以幾天氣,回自己的公寓自然自在些。
猜你喜歡
-
完結3579 章

韓先生情謀已久
“收留我,讓我做什麼都行!”前世她被繼妹和渣男陷害入獄,出獄後留給她的隻剩親生母親的墓碑。看著渣男賤女和親爹後媽一家團圓,她一把大火與渣男和繼妹同歸於盡。再醒來,重新回到被陷害的那天,她果斷跳窗爬到隔壁,抱緊隔壁男人的大長腿。卻沒想到,大長腿的主人竟是上一世那讓她遙不可及的絕色男神。這一次,她一定擦亮眼睛,讓 韓先生情謀已久,恍若晨曦,
354.7萬字8 57206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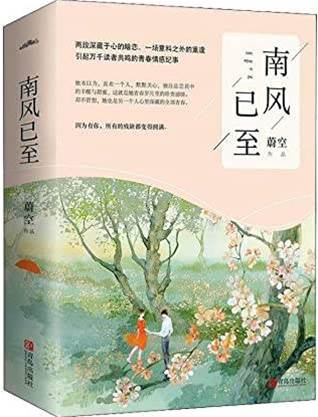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491 章

裴教授,你行不行啊
絕世小甜文,年齡差,先婚后愛,1v1雙潔,斯文敗類教授X古靈精怪富家女。劇情一:葉允澄可憐巴巴的看著裴修言:“老公,我作業沒寫完,你跟我們導員熟,你跟她說一聲讓她別檢查作業了好不好。”裴修言抿唇不說話。結果第二天,導員只檢查了葉允澄一個人的作業...下班回家的裴修言發現家空了一大半,葉允澄不見了...
97萬字8 44785 -
完結183 章

乖吝
【甜寵&雙暗戀&校園到婚紗&雙潔&救贖】(低調清冷富家大小姐&痞壞不羈深情男)高三那年,轉學至魔都的溫歲晚喜歡上了同桌校霸沈熾。所有人都說沈熾是個混不吝,打架斗毆混跡市井,只有溫歲晚知道,那個渾身是刺的少年骨子里有多溫柔。他們約好上同一所大學,在高考那天她卻食言了。再次相見,他是帝都美術學院的天才畫手,是接她入學的大二學長。所有人都說學生會副會長沈熾為人冷漠,高不可攀。卻在某天看到那個矜貴如神袛的天才少年將一個精致瓷娃娃抵在墻角,紅著眼眶輕哄:“晚晚乖,跟哥哥在一起,命都給你~”【你往前走,我在身后...
32.4萬字8 9635 -
完結872 章

誘捕玫瑰
五年前,溫棉被人戳着脊樑骨,背上爬養兄牀的罵名。 所有人都說她是個白眼狼,不懂得感激裴家賜她新生,反而恩將仇報。 只有她自己知道,這所謂的恩賜,只是一場深不見底的人間煉獄。 五年的磋磨,溫棉險些死在國外。 重新回來時,她煥然一新,發誓要讓裴家的所有人付出代價。 本以爲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死局。 卻沒想到,這個將她送到國外的養兄,卻跟個甩不掉的牛皮糖一樣跟在身後。 她殺人,他遞刀,她報仇,他滅口。 終於,溫棉忍不住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而那隱忍多年的男人終於露出了尾巴:“看不出來嗎?我都是爲了你。”
84.4萬字8 21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