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太子寵妾之後》 第49章小心機小心機
第49章 小心機 小心機
屋中燭影搖, 曖昧,旖旎,靜也是極為的大。
蕭玨可謂暴殄天, 適才還毫無作為, 此時判若兩然。
********************
廂房中的喜兒今日早早地便被退下了。
幾近每日都是如此,巧雲不大讓做那顧簌簌的近之事。
自然是顧簌簌吩咐的。
們防著也正常。
太子妃就是特意安置在顧簌簌邊兒惡心, 監視的!
顧簌簌明知道又怎樣?
份差別如此之大,一個小昭訓能怎麽?
還敢待太子妃送的一等侍?
笑話, 就得忍著!
喜兒很是輕蔑地一聲笑。
人不讓伺候, 就回了房歇著了。
一等侍大多倆倆一間房, 這玉香居就三個一等侍, 巧雲和冬兒一間,便自己獨房了, 房間雖然不大,但極為方便。
回了房後很悠閑,想起適才太子來時, 那顧昭訓看到太子就好像恨不得了似的樣子,撇了撇。
可真是-!
就沒見過這樣的子, 這般正想著, 屋外傳來敲門聲, 有侍端著木盆, 給送來了洗腳水。
“放那吧。”
每日睡前皆是如此, 適才回來前吩咐人送的。
那三等侍應了聲, 放下木盆出了去。
不時, 喜兒便一面悠閑的泡腳,一面心裏不屑,詬病那簌簌。
這般好一陣子, 腳也洗完了,外邊傳來敲門聲,是巧雲的聲音。
喜兒起蠻不願地給開了門。
巧雲來到房中找,還是初次,這事兒還蠻新鮮,喜兒頗為好奇,但也沒什麽好態度,皮笑不笑的。
“呦,什麽風把巧雲姐姐吹來了,找我何事?”
巧雲一改往常,態度謙和友好,笑著,語聲中甚至帶著幾分央求,說道:
Advertisement
“我與冬兒皆是肚子甚痛,想來是晚上那會兒貪,吃壞了東西,難的很,昭訓那邊,喜兒可否替我二人一會兒?”
那喜兒一聽角一,更是不屑。
“呦,怎地還信著我了,適才不是剛攆了我?”
巧雲笑的尷尬,語聲更親近了些。
“哪的話?大家同是伺候昭訓的,怎說什麽信任不信任。”
“呵.........”
喜兒笑的更輕蔑,知道們是怕在太子面前失態。
“行吧。你瞧,這不用上我了。大家一個居裏伺候著,保不齊誰什麽時候就會用上誰,所以別一天天的總拉著張臉,好像我欠你的一樣。”
巧雲朝堆笑,“是呢,你說的對。”
喜兒瞟一眼,又看了看自己剛才用過的洗腳水,明顯的難為,“那你,替我把那水倒了吧。”
巧雲瞅了眼地上的木盆,而後竟是笑著,很好說話的答應了。
喜兒眼睛瞧著給的洗腳水端了出去,一聲得意的笑,接著複穿了鞋,但這般剛穿完,眉頭一蹙,鼻息間嗅到一不知哪飄來的不大好聞的味道。
瞅了瞅窗子,此時已冬,窗子當然是閉的,後也沒多想,畢竟那邊兒不能沒人候著,便趕去了。
進了東暖閣後,喜兒很是謹慎,饒是和巧雲那般態度,心裏地詬病顧昭訓,也敢在太子妃面前加以詆毀那顧昭訓,但主子就是主子,還是一個寵的主子,面上當然不敢怠慢,更何況那天潢貴胄在呢!
一想到太子,喜兒戰戰兢兢的,極為小心。
太子在寵幸那顧昭訓,和幾個二等侍一樣,候在了前堂,與那顧昭訓伺候的臥房隔著個東暖閣。
那顧昭訓份低,也沒從娘家帶來什麽人,這玉香居的侍是不多,外頭有兩個不能進屋的三等侍,屋中有兩個能進這前堂,卻也不能進主子臥房的二等侍,加之與巧雲冬兒三人和一個小太監,也就這些人伺候了。
喜兒在那前堂候了一會兒便又嗅到了一難聞的味道,且好像那味道更濃了。
蹙眉瞅了瞅屋中那兩個二等侍,眼神詢問,但見其二人的樣子,明顯是也聞到了,且都在看。
“看我做什麽?哪裏味兒?”
冷著臉,聲音極小,還覺得是們上的呢!
那倆侍相視一眼,皆是搖頭,只道不知。
喜兒白了們兩下,很是不悅,指了指門,讓人出去。
那倆人皆是蠻委屈,但自然是出去了。
然們出去了後,那味道竟是還未被帶走,喜兒眉頭蹙的更,更是厭惡和不悅,但這時,臥房之中響起了太子慵懶深沉的聲音。
“來人。”
那聲音雖然有些懶散之,但肅穆與威嚴不減,很深邃,只消聽著聲音便讓人心一激靈。
自然是趕便去了,停在了東暖閣與臥房之間的珠簾前應聲。
“奴婢在。”
但聽太子沉聲道:“倒杯水來。”
“是。”
喜兒立馬去了,一冷汗地到桌前倒了溫水,雙手微地捧著,而後急急地送去。
這沿途一路,那難聞的味道竟然一直都有,且還好像越來越大了似的。
這般,進了臥房便愈發的拘謹,心裏頭也不知這是自己的錯覺還是怎麽,這到底哪來的味道?此時甚至有些懷疑,難道臭味是自己上發出的?
可是從小也沒有什麽特殊的味啊!況且昨日才洗過澡!白日裏也沒有,還能突然間就有了?
********************
屋中散著一頹靡之氣,那男人弄得狠,小簌簌汗著小臉兒,猶在發,但人已經進了被窩,小手提著香衾,把自己捂得極為嚴實,只個小腦袋,注意著外頭的靜。
男人半倚在床頭,披著服,肩膀寬闊,很白,膀臂與手臂之上皆是理致,-著健碩的-膛,下邊兒搭著個薄被子,單膝曲起,深邃的桃花眸半睜不睜,薄輕抿,神很是慵懶,甚至還有那麽點頹廢之,一看便是剛剛得到饜足,但那慵懶與頹廢之中卻是也著驕矜和尊貴,讓人而生畏,也陌生難近。
簌簌和他分開了便覺得他又陌生了。
但小姑娘此時的注意力不在他上,卻是在旁的上。
適才,聽見了珠簾後的聲音是那喜兒的,也聽出了那聲音有點,此時全神貫注地靜等著端水過來。
不時,腳步聲來了........
小簌簌面上無異,但水靈靈的眸子緩緩地轉了轉,攥著香衾的小手也不知不覺地了,接著那喜兒的聲音便更近地傳來,繼而也跟著飄來一難聞的味道........
紗簾被掀起的一瞬,那味道無異更大,也更明顯了。
“殿下,水。”
侍的聲音剛一響起,水杯也剛一遞過來,簌簌便聽到蕭玨懶而不耐,且極為不悅的聲音,“什麽味道?”
“啊!殿下......”
那喜兒好像頓時慌了,一下子就跪了下去,語聲了,杯蓋與杯子之間響著碎碎的撞聲,可見那手不是一般的抖。
“奴婢,奴婢.......”
這屋中的氣氛頓時變了。
小簌簌心口狂跳,但這一次卻不是因為害怕,而是.......
緩緩地提了被子,慢慢地擋住了口鼻,但卻在被窩之中再也忍耐不住,呲著兩排潔白整齊,仿若磨過的小牙,“嗤”地一下,咧便笑了,的子在被窩中輕。
無聲,但自然是無聲。
喜兒的腦中可謂是“轟”地一聲,臉慘白,人徹底懵了,但也徹底地明白,那臭味就是從上發出了,一時間傻了一般,跪下連連地要解釋,“奴婢......奴婢.......”
但奴婢了幾句什麽也說不出來。
蕭玨哪有耐心,更沒好心,張口便嫌惡,不耐煩地揚聲喚人,“曹英賢!”
那太監的耳朵也是極靈極靈的。
大老遠的在外頭,也聽到了太子的喚聲,沒一會兒便冷白著臉,急匆匆地趕來,立在臥房珠簾之外,“殿下!”
只聽太子厭煩地下了令,“把拖出去,發配了!”
“是是。”
“啊,殿下,殿下。”
那喜兒睜圓了眼睛,人被嚇的,猶傻的腦中“嗡嗡”直響。
曹英賢立刻便讓外頭的侍去把人拖了出來!
這般一聞,好家夥,如此失儀,也敢到太子邊兒去!
那喜兒被拽出去,直到出了門看到了巧雲和冬兒倆人急匆匆地奔來,方才一下子明白!
是們,是那盆洗腳水被人做了手腳,自己被們算計了!
是被們算計了!
說來此主意還是簌簌出的。
簌簌前世魂附玉中,倒也不是白活的。
早想把這喜兒弄走,但太子妃賞賜的,一個小昭訓,哪敢明著做什麽?唯能借蕭玨把弄走。
是以,想了好久辦法,直到那天突然記起往昔魂附玉中時,聽得那小姐的丫鬟與閑聊,當笑話說起過哪家小妾之間爭寵,還給敵用過這種臭腳,讓人啼笑皆非的事兒。
簌簌眼睛轉了轉,便活心了!
蕭玨是什麽人,那可是高貴的太子!
那男人特別幹淨,也特別幹淨,上始終有淡淡的香氣,穿的服向來都是連一個褶都沒有,哪有人敢帶著難聞的味道往他邊兒湊,料定蕭玨肯定不悅,肯定得把人攆走!
但自然,那實則也不是什麽多烈的東西,最多一天,味道也就散了。
但別說是一天,一個時辰對簌簌來說也是足矣。
喜兒終究就是一個侍,就算第二日不臭了,也不可能再回來了。
小簌簌在被窩之中笑完了後,恢複了常態,擡頭瞅向那男人,一臉無辜,更一臉困地緩緩鑽進了他的懷中,綿綿的小嗓音,安道:“殿下別生氣.......”
蕭玨可不是什麽好脾氣,轉瞬小簌簌的過來,又聞到了這個香的,心倒是好了那麽一點.......
*****************************
喜兒大半夜地被趕出了玉香居,發配浣房;玉香居又添置了兩個一等侍和兩個三等侍,這兩個消息第二日一早就傳到了程妤耳中。
太子妃無疑暴怒!
姜嬤嬤已經見過了那喜兒,知道了事的原委。
程妤狠狠地攥上了手。
“顧簌簌那個賤人!”
耍心機,有意算計,自己不能怎麽了送的人,便借著太子,把賞的侍弄走,這是顯而易見!
“,給本宮等著!”
猜你喜歡
-
完結232 章
腹黑郡王妃
一覺睡醒,狡詐,腹黑的沈璃雪莫名其妙魂穿成相府千金.嫡女?不受寵?無妨,她向來隨遇而安.可週圍的親人居然個個心狠手辣,時時暗算她. 她向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別人自動送上門來討打,休怪她手下不留人:姨娘狠毒刁難,送她去逛黃泉.繼母心狠手辣,讓她腦袋開花.庶妹設計陷害,讓她沒臉見人.嫡妹要搶未婚夫,妙計讓她成怨婦.這廂處理著敵人,那廂又冒出事情煩心.昔日的花花公子對天許諾,願捨棄大片森林,溺水三千,只取她這一瓢飲.往日的敵人表白,他終於看清了自己的心,她纔是他最愛的人…
155.2萬字5 59507 -
完結752 章

盛世凰歌
擁有精神力異能的末世神醫鳳青梧,一朝穿越亂葬崗。 開局一根針,存活全靠拼。 欺她癡傻要她命,孩子喂狗薄席裹屍?鳳青梧雙眸微瞇,左手金針右手異能,勢要將這天踏破! 風華絕代、步步生蓮,曾經的傻子一朝翻身,天下都要為她而傾倒。 從棺材里鑽出來的男人懷抱乖巧奶娃,倚牆邪魅一笑:「王妃救人我遞針,王妃坑人我挖坑,王妃殺人我埋屍」 「你要什麼?」 「我要你」
132.9萬字8 10928 -
完結4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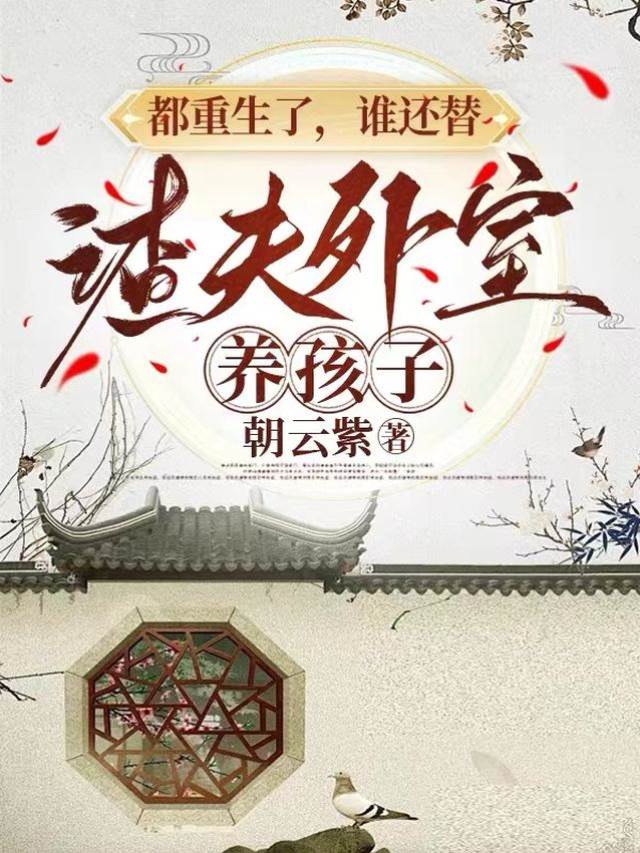
都重生了,誰還替渣夫外室養孩子
上輩子,雲初輔助夫君,養大庶子,助謝家直上青雲。最後害得整個雲家上下百口人被斬首,她被親手養大的孩子灌下毒酒!毒酒入腸,一睜眼回到了二十歲。謝家一排孩子站在眼前,個個親熱的喚她一聲母親。這些讓雲家滅門的元兇,她一個都不會放過!長子好讀書,那便斷了他的仕途路!次子愛習武,那便讓他永生不得入軍營!長女慕權貴,那便讓她嫁勳貴守寡!幼子如草包,那便讓他自生自滅!在報仇這條路上,雲初絕不手軟!卻——“娘親!”“你是我們的娘親!”兩個糯米團子將她圍住,往她懷裏拱。一個男人站在她麵前:“我養了他們四年,現在輪到你養了。”
85.6萬字8.18 288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