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產當天,我離婚了》 第1卷 第67章 就在這里,脫光!
祁宴禮目一沉,慍怒流轉,“現在離婚?”
“對。一年時間,沈楚語或許可以等,但肚子里的孩子等不了。我清楚,你一定會讓的孩子留在祁家,但只要我還是你的妻子,我就有權拒絕。如果我不同意,那老爺子也不會答應。”宋辭嗓音沙啞,目筆直的向他,說:
“我想祁總應該也不希你跟沈楚語的孩子被人當做私生子吧?而且……祁家家主在外有私生子的消息一旦傳出去,外界會怎麼看?”
祁宴禮冷嘲熱諷,“先示弱,再威脅,同樣的招數,你們宋家倒是屢試不鮮。”
宋辭臉蒼白,微張,解釋辯駁的話到邊卻又生生卡住,最后干的開口:“我不能眼睜睜看著爸爸死在牢里,兩年前的婚,一切的錯都在我,你恨我,要怎麼報復我都可以。”
“是麼?如果我要你自己從那跳下去,一命換一命呢?”祁宴禮眼眸沉得仿佛能滴出墨來,“祁太太也愿意嗎?”
Advertisement
宋辭順著祁宴禮的視線,側頭看向那片落地窗。
它還敞開著,風呼嘯著吹進來,剛才被推下去的失重仍清晰可。
宋辭角繃直,只覺得遍鱗傷的心好似被摁進鹽水里,細的疼通過管傳遍四肢百骸,疼得難以息。
良久,才找回自己的聲音,聲線輕的向他確認:“是不是……只要我跳下去,你就會救我爸爸?”
男人冷笑,殘忍的說:“宋辭,你沒有跟我討價還價的余地。”
言下之意就是即便他出爾反爾,現在也只能且必須相信,否則,宋長國死路一條。
宋辭自嘲一笑。
旋即強撐著站起,沒有片刻猶豫,徑自往那片落地窗走。
邊緣。
風迎面呼嘯,吹的發。
宋辭眼簾微垂,百丈高樓深不見底,瞬間映眼底。
說不害怕,那都是假的。
可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
剛才猛然往下墜的覺再度涌上來,讓的呼吸都不由得一,手攥拳,指甲死死地掐著掌心,轉過,眼神里帶著決絕,對祁宴禮說:
“希……祁總說到做到。”
祁宴禮看著人形單薄的站在邊緣,臉蒼白近乎明,明明心里篤定的認為這人不敢跳下去,只不過是在裝模作樣罷了!卻不知道為什麼心臟驀然一痛,痛得他有那麼一瞬間不上氣來,腦海中不自覺的浮現起昨天看到宋辭果斷將刀扎張海昌肩膀的畫面。
仿佛有人在他的耳邊說:‘快阻止!真的會跳下去!’
他還沒來及想明白這道聲音從何而來,宋辭閉眼后仰的畫面便猛地撞進他的視線。
祁宴禮寒眸驟然,心跳仿佛停止。
他倏地沖上前,一把抓住人的手臂,將扯進來抵在旁邊的固定落地窗上。
額角的青筋凸起,他一時沒克制住怒火,低吼:“你他媽真的瘋了!”
宋辭心跳急劇加速,睫羽了,雙眸布滿,明明怕得全發抖,卻死死咬著下極力克制,就這麼安靜的盯著祁宴禮。
祁宴禮被這眼神弄得心里不舒服,驀然想起昨天顧廷曄吻的畫面,積的煩躁不減反增,視線落在潔白的額間,戾之在眸底凝聚。
抬手,用拇指暴的的額間。
宋辭吃痛,本能的向往后。
“你敢一下!”祁宴禮的警告又冷又沉,像是從牙里出來般,手上的力道跟著加重。
沒一會兒,宋辭的額頭就紅了一片,好似能滲出來。
可即便如此,祁宴禮也不滿意。
他垂眸,戾的目落在人白皙的鎖骨,上只有沐浴的清香,淡得若有似無,卻能在不知不覺的人心弦。
兩人的距離很近,宋辭能明顯覺到男人看的眼神,冰冷又赤。
“祁……”
“掉。”
宋辭狠狠一怔,幾乎是瞬間聽懂祁宴禮的意思,瞳孔輕,“祁宴禮,可不可以去休息室……”
的正對面,是連接辦公室外的大片明玻璃,可以清楚的看見人來人往的書辦。
“宋辭,我不喜歡一句話說三次。”祁宴禮松開,居高臨下的冷晲著,“就在這里,掉。”
宋辭止不住的戰栗,對上祁宴禮沒有任何緒起伏的眼神,只覺得嚨艱,彌漫著一鐵銹味。
半晌,眼看男人的耐心快要耗盡,緩緩抬起手,一顆一顆解開自己服的扣子……
猜你喜歡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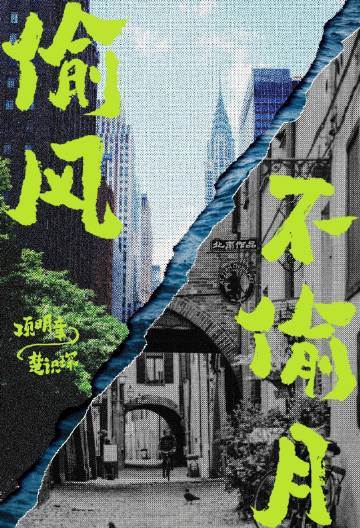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170 章

離婚后,秦少夜夜誘哄求復合
薄棠有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她暗戀了秦硯初八年。得知自己能嫁給他時,薄棠還以為自己會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直到,他的情人發來一張照片秦硯初出軌了。 薄棠再也無法欺騙自己,秦硯初不愛她。 他身邊有小情人,心底有不可觸碰的白月光,而她們統統都比她珍貴。 恍然醒悟的薄棠懷著身孕,決然丟下一封離婚協議書。 “秦硯初,恭喜你自由了,以后你想愛就愛誰,恕我不再奉陪!” 男人卻開始對她死纏爛打,深情挽留,“棠棠,求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她給了,下場是她差點在雪地里流產身亡,秦硯初卻抱著白月光轉身離開。 薄棠的心終于死了,死在那個大雪紛飛的冬天。
30.6萬字8 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