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奴三年后,整個侯府跪求我原諒》 第546章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難過
杜副將仔細觀察著耿叔的臉,像是企圖從耿叔的神中找出一不尋常來。
昨夜他雖然傷了蕭衡,但他確定,自己并未傷及蕭衡的要害,怎麼會死了?
可耿叔此刻的臉上本看不出半點端倪,他下意識地看向一旁的喬念。
就見喬念愣坐在原地,全然沒有反應。
杜副將終于還是沒忍住,開了口,“怎麼就死了?蕭將軍他的子明明康復了,前兩日就能下床了,怎麼……”
“他先是與王爺了手,以至于上的舊傷裂開了不,后來又遭了刺客,雖然并未傷及要害,卻連累舊傷盡數發作,衫都被鮮浸了。”
耿叔一邊說著,一邊垂下眸去,“也怪我,沒有守在蕭將軍邊,直到今早才發現……”
楚知熠知道,耿叔在撒謊。
可他的視線還是忍不住朝著喬念看了過去。
此刻,喬念的臉上并沒有出半點悲傷的模樣,可楚知熠一眼就看出來,的況不太好。
當下便是沉聲問道,“尸首呢?”
既然是要撒謊,那自然是要將這個慌撒得圓滿。
畢竟,就算他不問,杜副將也會問的。
耿叔早有準備,“穆家的公子心善,派了馬車將蕭將軍的尸首運回京去了。”
之后耿叔又說了什麼,喬念是一點兒都聽不進去了。
Advertisement
的視線落在手中的兵書上,那上頭麻麻地寫滿了各種計策。
原本是看得興起,眼下卻只覺得看著頭疼。
蕭衡,尸首。
這兩個詞,怎麼也無法聯系到一起。
那個人,是曾經深了十幾年的人,是活到現在的人生里,大半的生命都與之一起度過的人,是那個給過寵溺,也給過最絕最冷漠的人。
恨過的人。
活生生的人。
可怎麼,會死的?
喬念實在想不明白。
大夫的醫不行,可是給了他傷藥的啊!
他為何不用?
還是說,明明用了,也保不住他的命嗎?
“喬姑娘,喬姑娘?”
耳邊,傳來一聲聲輕喚。
喬念終于回過了神來,看向正喚著的杜副將。
眼神中染著幾分疑。
杜副將卻是試探般問道,“您還好吧?”
喬念看著杜副將,眨了眨眼。
還好嗎?
應該是還好的。
對于蕭衡,是真的早就已經不了。
可不,并不表示會希他死。
相反,因著那曾經備關照的十五年,反倒是希他能好好活著。
可他卻死了……
喬念緩緩轉頭,朝著楚知熠看了過去。
就見那雙幽深的眸子里,帶著幾分憂。
喬念張了張,是想告訴楚知熠,不用擔心,沒事。
可一開口,那話竟然就變了。
“我,我好像,有點難。”
心口那一陣又一陣翻開來的,名為悲傷的東西,令得此刻整個人都難得厲害。
那個曾經與坐看山花爛漫的年,竟化為了虛無。
楚知熠下意識地握了握拳,而后站起,一邊朝著喬念走去,一邊下令,“都出去。”
“是。”
耿叔應了聲,便是出了營帳。
杜副將也跟著離開,卻還是不忘回頭看了一眼。
就見,楚知熠已是將喬念抱進了懷里,一聲聲,低低地安著。
而喬念的側臉靠在楚知熠的肩上,眼眶里的那一滴淚也被杜副將看得清清楚楚。
看來,蕭衡是真的死了。
杜副將沉了沉眉,終于放下了帳簾。
楚知熠雖然在安著喬念,但眼角的余卻在注意著杜副將。
只等他離開了,方才微微松了口氣,沉聲道,“假的。”
喬念一愣,忙是從楚知熠的懷里掙開,盯著楚知熠看,“什麼?”
“耿叔方才的話,應該是說給杜副將聽的。”
喬念這才好似明白了過來,眼底的淚竟莫名洶涌了起來,連雙都在微微抖著,“真的?”
楚知熠很肯定地點了點頭,“晚些再找耿叔細問,好了,別哭了。”
他抬起手,大的拇指輕輕抹過的臉頰。
糙的,卻心口一點一點回了溫。
所以,耿叔方才的話,是為了騙杜副將。
結果,卻將給騙了?
喬念終于低下頭,雙手捂住了自己的臉,任由眼淚落在掌心。
好一會兒,才抬起頭來看向楚知熠,淚眼婆娑,“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我與他早就已經沒有任何關系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這麼難……”
在聽到蕭衡死訊的那一個瞬間,的大腦甚至空白了一瞬。
楚知熠卻是明白的。
“因為你是人。”
是人,就會有,而人的,又是那麼復雜。
哪里是簡簡單單的一個與不,就能解釋得那麼清楚的?
他知道,那十五年里,沒人能比得上蕭衡跟林燁。
恐怕連荊巖都不能。
在被捧為掌上明珠的那十五年里,蕭衡與林燁,是最大的功臣。
只是后來,時流轉,捧著的人卻幫著別人將踩進了泥濘里。
自然會恨,會怨,會委屈。
卻絕對不會希,他們死。
的難過,何曾又不是在為那十五年的而難過?
聽著楚知熠的話,喬念方才還有些不知所措的心,徹底安穩了下來。
他就是有這樣的本事。
不管有多慌,只要他一句話,便能釋然不。
卻聽著楚知熠道,“只是你這樣子,還得再演演。”
聞言,喬念點了點頭。
方才杜副將見到的樣子,應該已經信了八九。
倘若不繼續演,豈不是功虧一簣?
只是,喬念有些不明白,“大哥為何還留著他?”
明明在突厥的時候,軍中的細被發現后就被殺了,甚至還被掛在了高桿之上。
為何還放任著杜副將在軍中游走?
楚知熠笑了笑了,“蕭衡那邊雖然不知是何況,但杜副將與棠國有聯系是事實,既如此,那何不將計就計?”
聞言,喬念瞬間便恍然大悟。
揚了揚手中的兵書,沖著楚知熠一笑,“看得再多,也不及大哥半分。”
楚知熠抬手,了喬念的腦袋,“慢慢學,學一輩子都行。”
猜你喜歡
-
完結552 章
掌歡
(此書內容不全,請觀看另一本同名書籍)駱三姑娘仗著其父權傾朝野,恃強淩弱、聲名狼藉,沒事就領著一群狗奴才上街。對清陽郡主來說,這種人敢在她麵前撒野,她伸根手指頭就弄死了。直到她睜開眼,發現自己叫駱笙。
38.8萬字5 26029 -
完結527 章
嬌嬌貴女一紅眼,禁欲王爺折了腰
京城第一美人沈定珠為給家族洗清冤屈,做了一輩子的替身白月光,獻媚討好數年,最后卻中毒慘死。重生后,竟又回到家族蒙難之日,馬上要被丟入軍營為妓。她再次選擇投靠蕭瑯炎,知道他日后會成為九州霸主、開疆辟土,利用他才能救回流放漠北的父母親人。只是這一次,她與前世不同。她跟他談利益,談條件,談生死,唯獨不談情。甚至幫他與白月光做掩護。她替他做了一切,唯獨不會愛他。后來蕭瑯炎登基,殺紅了眼,提著所謂白月光的腦袋問她“愛妃心中那個忘不掉的男人,到底是哪一個?”
114.3萬字8 18074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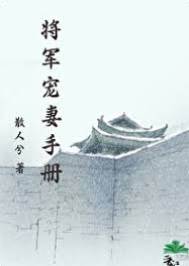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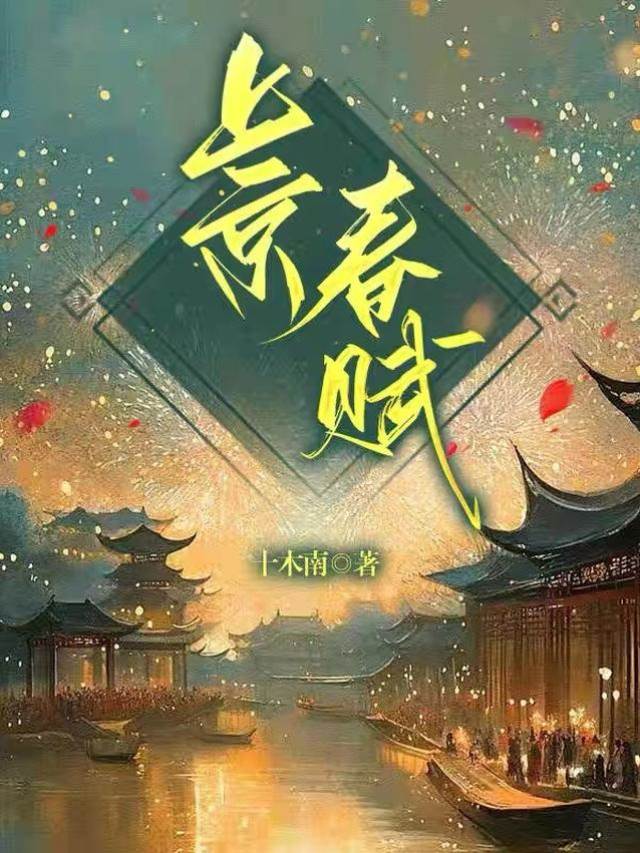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