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詐死以后,薄情傅總他突然瘋了》 第1卷 第38章 電話
今日是蘇忱輕死去的第192天。
管家疲力盡的回到休息室,依舊是懷念蘇小姐的一天。
說實話,自從那次日記事件后,他就覺得自家主人變得越來越神失常。管家每天都在苦惱,思考如果辭職,自己還能在哪里找到如此高薪的工作。
“管家。”
正思考著,魂的來了。
他立即正襟危坐,瞥見本該已經休息的主人走出臥室,神態很詭異,平日裝作溫潤的桃花眼里裝著捧刺骨涼水,看似平靜,線卻比平時繃得。
傅文琛道:“去把蘇忱輕留下來的畫搬出來。”
管家:“……”
大晚上的,真是活爹。
但他敢怒不敢言,面上笑的比誰都老實,手腳麻利的跑去倉庫,讓人搬畫。
這些跟蘇小姐有關的東西,本該在半年前就被收拾出來扔進垃圾箱。但那晚他家傅先生看了蘇小姐的日記,突然改變主意。
沒扔,
但是鎖進了倉庫。
很快,布滿灰塵的畫被逐個擱置在客廳,許多畫已經褪,變得陳舊而丑陋。
這樣的畫無疑已經不備欣賞價值。管家眼觀鼻鼻觀心的站在一旁,倒是有些好奇,這位傅先生搬畫出來,到底是要做什麼。
然后就看到男人走近畫前,抬起手機,將屏幕上的一張圖片靠近畫,似乎在比較。
管家忍不住看。
Advertisement
“來,”傅文琛反而讓出位置讓他看,挑眉,神間居然出些許莫名的愉悅,“你說,這兩張畫像不像?”
管家愣住神,已經許久沒見傅先生這樣笑過。上次見,還是蘇小姐活著的時候。
他又仔細觀察,實話實說:“五像。”
傅文琛語氣變輕:“那你說,這兩張,會不會是一個人畫出來的?”
管家:“……”
瘋了,真是瘋了。
他保持沉默,心道死了的人怎麼可能畫畫?在地府里畫完然后郵過來?
離譜。
與此同時,手機屏幕上跳出數條新訊息。傅文琛眼底笑意消失,將手機收回。
[鐘昧:還在嗎?]
[鐘昧:有意思,看個畫把人給看沒了。]
他回復消息:
[傅文琛:在。]
[傅文琛:畫一般,不值錢。]
對方秒回:
[鐘昧:哦。可是我喜歡,我花了好幾十萬買的呢。]
傅文琛盯著這行字,眸底沉靜而抑,他盯了片刻,打字追問:
[傅文琛:冒昧問一句,這是哪位畫家的作品?]
對話框上的“正在輸”跳了半天,終于跳出一段稍微長些的回復。
[鐘昧:沒誰,無名畫家。以前在國外讀書,喜歡臨摹,今年已經三十多歲了吧,已婚已孕,帶倆小孩。怎麼?傅總興趣?]
[鐘昧:您興趣的話,我可以讓離。/微笑]
[鐘昧:我知道,這畫是不是跟您之前那個小人的風格有點像?誒,理解,誰不知道傅總是個深種?您放心,我一定讓離,把的兩個孩子一起打包給您送去,您看怎麼樣?]
傅文琛冷笑了聲,回復:
[傅文琛:不用。]
他把手機屏幕按滅,冷冷瞥一眼面前已經舊到看不清線條形狀的畫作,轉。
對話框那邊,
鐘昧倚著辦公桌,笑得快要直不起腰。他跟這個人作對十幾年,還從沒見傅文琛吃過這種啞虧。對這場惡作劇的效果非常滿意。
說起來,他能這麼開心,還是要謝那位蘇畫家。
鐘昧笑著拿起手邊的畫,仔細欣賞。
細致獨特的筆、富濃郁的彩,看起來,他這幾十萬花的并不算賠。鐘昧覺得,這位蘇畫家即使沒有傅文琛的幫助,或許也能打拼出來一番天地。
他拿著畫走到書柜前,
思索片刻后,還是將畫放進了保險箱里。
·
關于自己的畫被拿去惡作劇這件事,蘇忱輕本人毫不知。
跟這位鐘先生簽訂合同后,便開始履行每天一幅畫的工作任務,日收二十萬。
蘇忱輕也不再擺攤。
起初兩天,畫畫的地點在工業園區的那棟大樓里。鐘昧每次都坐在秋千上睡覺,讓覺得自己不是在畫人,而是在畫一只考拉。
鐘昧聽到的形容,笑得差點從秋千上掉下來,并且告訴,以后去鐘宅作畫。
鐘宅距離所住的地方很遠,
由于來回通勤過于麻煩,鐘昧提出讓搬去住,反正客房多得是。當然,這只是一個選擇,是否搬過去由自己決定。
蘇忱輕想,有別墅為什麼不住?
遂搬家。
和傅文琛喜歡的建筑風格不同。
傅文琛的房子大部分是黑白配,飽和度低,走極簡風格,和他這個人的心一般死氣沉沉,充滿棱角。
但鐘昧不同。鐘昧喜歡明艷張揚的,喜歡各種花里胡哨的擺件。
鐘昧父母早逝,其他親人覬覦鐘家家產,也早就與鐘昧撕破臉,勢不兩立。
整座房子平日幾乎只有鐘昧一個人。
偶爾,還會有隔壁的老先生來做客。
蘇忱輕不認識這位老先生,想來應該是鐘家的朋友。吃不慣滬市的食,會下廚做自己的家鄉菜,每日順帶投喂一下來做客的老人,把人哄得極開心。
老先生說要認做養,
蘇忱輕想到自己的父親,低頭挑揀了許久的菜,忍住嚨的酸,說好。
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天,蘇忱輕已經到手快要一百萬。就在覺得錢十分好賺的時候,傍晚,鐘宅的傭人忽然跑來,說有電話,要接一下。
“那位很重要,”傭人的表十分窘迫,像是也沒料到會接到這樣的電話,顯得張又害怕:“正好鐘先生不在,那位老先生也不是鐘家人。只能您先接了。”
蘇忱輕問:“這麼重要的電話,難道不該直接打給鐘先生?為什麼要打進家里。”
傭人也很無奈:“不知道,按理來說,這位確實不該給家里打電話。”
鐘宅沒有管家,也能理解傭人的難,于是便跟隨傭人到座機,拿起話筒。
蘇忱輕屏息,
一瞬間,莫名的警惕讓沒有立即開口。仿佛隔著話筒的音孔,到了悉的、令人窒息的抑氣場,無形的手般扼住了的嚨。
聽到音孔里傳出悉的嗓音。低沉、溫醇,帶著讓人無法抗拒的笑意:
“你好,”
傅文琛輕聲問:“是鐘的朋友?”
猜你喜歡
-
完結1213 章

龍鳳萌寶:總裁大人寵上癮
五年前,一夜情謎。五年後,看到照片里跟自己一模一樣的龍鳳萌娃,江煜城的心都要化掉了。「五千萬,孩子歸我,錢歸你。」男人獨斷霸道。呆萌女娃:「爹地賺錢不就是給媽咪和我們花的嗎?」腹黑男娃:「而且爹地以後的財產都是我們的。」左欣欣:幹得漂亮!江煜城:……
328.3萬字8 155329 -
完結459 章

一孕成歡:爹地,束手就擒
她貌美如花,為了母親甘愿給人生孩子。他身家千萬,迷惑眾生,卻因為愧疚寧愿找人生個孩子。可她玩不過命運,錢到手了,媽卻死了。他也斗不過謊言。本以為是真愛負責,卻不想走進枕邊人步步為營的算計……當她以弟媳婦的身份出現在婚禮的現場[],他的心猶如刀割一般的刺痛!你是給我生孩子的女人,憑什麼嫁給別人?
87.4萬字8 28851 -
完結111 章

霍總別虐了,夫人已發瘋嘎嘎亂殺
【絕不原諒 男二上位 娛樂圈】南芷簽下離婚協議時,回想與霍紹霆的七年,隻覺不值。霍家遭遇橫禍,她陪他住地下室、撿瓶子,陪他吃過所有的苦。在事業的巔峰,選擇退出娛樂圈與他結婚。然而,他在功成名就後,卻帶著一個又一個的情人招搖過市。意外懷孕時,她小心翼翼的給他報備,卻隻得他一句:打掉!她終於死心。燒掉關於兩人的一切,再也沒有回頭。……江市霍少是娛樂圈的龍頭大佬,手裏有無數資源,無數女人趨之若騖。他對每個女人都很好,唯獨對自己的糟糠之妻心硬如鐵。讓她失去孩子,逼她離婚。真的失去南芷後,他痛不欲生,追悔莫及。從此她在人間,他墜入無間地獄!……離婚複出後,有記者問:“請問結婚有什麼好處?”她說:我覺得…每個人都該有每個人的報應。記者又問:你以後還會相信愛情嗎?她答:男人別來沾邊。粉絲狂熱:姐姐我可以。季影帝:現在去暹羅還來得及嗎?南芷:…………再次重逢,是在頒獎典禮上。他看著她,聲音暗啞卑微:“阿芷,我錯了,再愛我一次好不好?”她隻是瞥了他一眼,聲音清冷:“絕不!”……經過一段失敗的婚姻,南芷水泥封心,隻想跳過男人擁有一個可愛的
21萬字8.33 63325 -
完結260 章

綠我?我轉投京圈太子爺懷抱氣死渣男
婚禮當天,老公就跑去了國外和祕書纏綿。綠我?看誰綠過誰?林清桐轉身就保養了一個帥氣逼人的小實習生。整的誰沒有小三似的。小實習生寬肩窄腰身體倍棒,又撩又欲夜夜笙歌。逍遙了三年,老公要回來了,林清桐給了小實習生一張鉅額支票。“我老公回來了,你走吧。”沒想到小實習生大發雷霆:“跟那小子離婚,和我在一起。”林清桐嗤之以鼻,轉身離開並把人給開了。沒多久,她竟然在自家公司看到了小實習生。他竟然是她老公的小舅舅!完蛋了,她好像惹到了不該惹的人……
48萬字8 11115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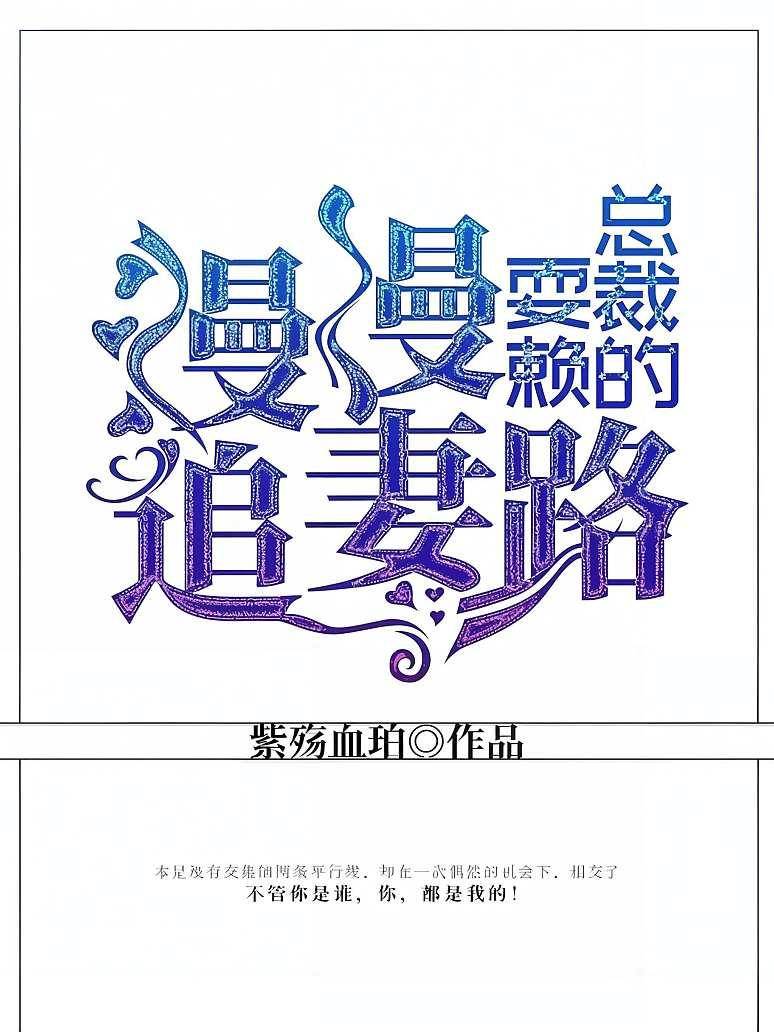
耍賴總裁的漫漫追妻路
本是沒有交集的兩條平行線,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事件一:“醫藥費,誤工費,精神損失費……”“我覺得,把我自己賠給你就夠了。”事件二:“這是你們的總裁夫人。”底下一陣雷鳴般的鼓掌聲——“胡說什麼呢?我還沒同意呢!”“我同意就行了!”一個無賴總裁的遙遙追妻路~~~~~~不管你是誰,你,都是我的!
27.3萬字8 1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