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婳燕爾》 第1卷 第57章 赴宴
司珩坐在云婳后的搖椅上,若有所思地向窗外,等著梳妝。
云婳想戴司珩送的那套飾品,便特意選了件同的襦。
“這樣穿,可以嗎?”云婳將淡的流蘇玉簪在云鬢上,走到司珩面前,輕輕轉了一圈,征詢地問。
大幅的擺隨著轉而逶迤展開,好似一朵春日里灼然綻放的桃花,襯得仙姿玉的小臉,更加嫵妍麗。
倒真是人比花花無,花在人前亦黯然。
司珩眸微滯,對云婳出手,遲聲開口:“很好看。”
常言道為悅己者容,是以,當云婳聽到司珩的夸獎時,瓣抑制不住地上揚。握住他的手,任由他拉著坐在他膝上,乖乖地倚在他前。
搖椅隨之晃,云婳頭上的流蘇玉簪輕輕在司珩耳側,就像夏日里微醺的風,在平靜的湖面上推出一圈圈人心弦的漣漪。
司珩手搭在云婳腰側,又貪地抱著坐了一會兒,兩人才起出門。
暮四合,金陵臺燈火輝煌,亮如白晝。
賓客們或錦玉帶,或羅飄飄,踏著紅綢鋪就而的迎賓道,步這影錯的盛宴之中。
老于世故的林府丞笑容滿面地站在金陵臺門前,等著紛至沓來的達顯貴們。
瞧見司珩和云婳下了馬車,趕忙迎上前,恭敬道:“下見過辰王殿下,見過辰王妃。”
Advertisement
不管別人如何看待這個不寵的王爺,但在林府丞看來“瘦死的駱駝永遠比馬大”,所以該有的禮數半點不能。
司珩抬了抬手,讓林府丞起。
林府丞笑著引路在前,親自將司珩和云婳帶席中。
隨著兩人的,無數雙眼睛或直視或暗瞟,紛紛投落在兩人上,看得人渾不自在。
而眾多視線中,亦有一道溫和而慈的目。
云婳輕輕拽了拽司珩的袖,聲低語:“殿下等我一會兒,我去和林夫人也就是錦書的母親打個招呼。”
司珩“嗯”了一聲,便見云婳踩著端莊的小步子緩緩走向林夫人。
“婳兒。”林夫人見云婳過來,手迎了上去。
“夫人。”云婳彎起眼睛,笑著握住林夫人的手。
林夫人拉起云婳的手,上下打量了一番,又坦地看了司珩一眼,不由欣地說:“看來真如錦書說的那般,王爺對我們婳兒很好啊,婳兒可是出落得越來越標致了。”
云婳有些不好意思地赧一笑:“夫人過獎了。”
朝林夫人后看了看,卻沒瞧見林錦書,于是疑地問:“夫人,錦書呢?”
“錦書染了風寒,我便沒讓來。”作為林錦書唯一的好朋友,林夫人對云婳有著屋及烏般的喜。
“那嚴不嚴重啊?我明日過府去看看錦書,方便嗎?”云婳擔心地蹙起眉尖。
林夫人挲著云婳細的手背,搖了搖頭:“不嚴重,過幾日就好了。婳兒若是想來,就等錦書病好的,省得把病氣染給你,那我們可真就過意不去了。”
云婳還想說什麼,林夫人笑著打斷:“好孩子,等你有時間來府上,咱們再細細說話,快過去王爺邊吧,別讓人等著急了。”
云婳回頭看了司珩一眼,正好對上他來的目,于是不再推,臉上凝著溫甜的笑:“那我改日再去看您和錦書。”
林夫人笑著點頭,目送云婳走回司珩邊,看著司珩自然地牽起云婳的手,看著兩人越走越遠的背影。
腦中閃過些許似曾相識又闊別已久的畫面。當初,和林老爺也曾有過這樣一段如膠似漆的燕爾之時,但隨著柳姨娘的出現,隨著林老爺一房又一房的納妾,當初那點意早已磋磨得半點不剩。
不大吵大鬧,不撕破臉,是給彼此最后的面。
宴席尚未開始,云婳和司珩便四走走。兩人走到一無人的回廊,正要拐過去,卻聽到回廊另一側傳來一前一后的腳步聲。
司音停下腳步,轉看向后面的沈既白,聲音里著難得的:“既白,本宮已隨你來了闃州,你還要拒我于千里之外嗎?”
聞言,云婳輕輕捂住,瞪大了眼睛,側頭看向邊的司珩,眼神中滿是探聽了的驚訝和興。
司珩看著云婳的小表,薄溢出一寵溺的淺笑,抬手了的頭。
沈既白負手而立,俊朗的面上無一波瀾:“臣早已對公主言明,承蒙公主錯,但萬不敢耽誤公主婚嫁。”
司音癡癡地著沈既白,眼中并無驚詫,有的只是不甘。同樣的話,這三年里,沈既白對說了無數遍。
不明白,都肯放下公主的架子主對他示好,就算一顆頑石,三年也該有松吧,然而并沒有。
司音掩在袖下的手指摳進掌心,些微的疼讓恨聲問:“你是嫌棄我嫁過人?”
“不是。”沈既白礙于司音長公主的份,說話不得不克制,但實際上他心里煩躁異常。
“那好,沈既白,本宮告訴你,只要你一日未娶,本宮就一直等你。”這話司音三年前就想好了,否則這麼多年也不會如此執著。
十五歲嫁給瓦達爾王時,是沈既白送去的草原。二十三歲重回大魏,又是沈既白率部將迎回。
而這些年他又一直未曾娶妻,這一切都讓司音偏執地認為:和沈既白之間有著天定的緣分。
“這又何必。”沈既白沉聲開口,卻沒有再多言語。不過為斷了司音的念想,他確實產生了要娶妻的想法。
“不用你管。”司音甩了下袖,揚著下驕傲地從沈既白邊肩而過。
原來是而不得啊,這種覺最難了,可偏偏是最勉強不得的東西。
云婳珍視地看向旁的司珩,忍不住出手臂環住他勁瘦的腰,仰起小臉,下抵在他骨,地著他。
司珩回抱住撒的人,漆眸浮上堪比日月般的溫潤,低頭在的上親了一下。
待司音走遠后,沈既白向回廊另一側司珩和云婳所在的方向,沉聲道:“出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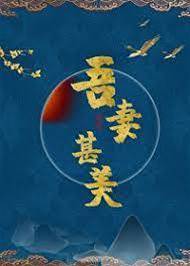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
完結2238 章

天下第一妃
她,二十一世紀Z國軍情七處的頂尖特工,一朝穿越成為懦弱無能的蕭家廢物三小姐!未婚夫伙同天才姐姐一同害她遍體鱗傷,手筋腳筋被砍斷,還險些被大卸八塊?放肆!找死!誰再敢招惹她,休怪她下手無情!說她是廢物?說她沒有靈獸?說她買不起丹藥?睜大眼睛看清楚,廢物早就成天才!靈獸算個屁,神獸是她的跟屁蟲!丹藥很貴?別人吃丹藥一個一個吃,她是一瓶一瓶當糖豆吃!他,絕色妖媚,殺伐決斷,令人聞風喪膽的神秘帝王。當他遇上她,勢必糾纏不休! “你生生世世只能是我的女人!
411.7萬字8 36333 -
完結1065 章

新婚夜和離,失寵醫妃冠絕京城
醫學天才穿越成淩王棄妃,剛來就在地牢,差點被冤死。身中兩種蠱、三種毒,隨時都能讓她一命嗚呼。她活的如履薄冰,淩王不正眼看他就算了,還有一群爛桃花個個都想要她的命。既然兩相厭,不如一拍兩散!世間美男那麼多,為什麼要天天看他的冷臉?……“我們已經合離了,這樣不合適!”“沒有合離書,不作數!”就在她發覺愛上他的時候,他卻成了她殺母仇人,她親手把匕首插入他的心口……真相大白時,他卻對她隻有恨,還要娶她的殺母仇人!“可是,我懷了你的孩子。”“你又要耍什麼花招兒?”
177.9萬字8.18 12197 -
完結274 章

醜女絕色,瘋批暴君夜夜囚寵
前朝覆滅,最受寵愛的小公主薑木被神醫帶著出逃。五年後她那鮮少接觸過的五皇兄平叛登基。她易容進宮,為尋找母親蹤跡,也為恢複身份……一朝寒夜,她忽然被拉入後山,一夜雲雨。薑木駭然發現,那個男人就是龍椅之上的九五之尊……她再次出宮那時,身懷龍胎,卻在敵國戰場上被祭軍旗,對麵禦駕親征的皇帝表情冷酷無比,毫不留情的將箭羽瞄準於她……他冷聲,“一個女人罷了…不過玩物,以此威脅,卻是天大笑話!”(注:此文主角沒有冒犯任何倫理)不正經文案:……獨權專斷的暴君為醜女指鹿為馬,即便醜陋,也能成國家的絕美標桿!恢複真容的醜女:……那我走?——————種植專精小能手,從人人厭憎的“禍國妖妃”,變為畝產千斤的絕色皇後!
49萬字8 26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