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風將至》 第49章
“哥,歡迎回國。”
封老爺子的壽宴, 舉辦地點在輔川郊區一老爺子早年購買的私人莊園,由徐昭禮家酒店的主廚團隊負責。
檢查了邀請函,南知在服務生的帶領下, 走進莊園。
傍晚時分,夕西斜。
莊園裏像是被鍍上了一層金,滿目皆是耀眼的,四周縈繞著淺淡的花香, 偶爾還能聽到幾聲鳥鳴。
自助餐式的花園裏, 人來人往。
那個端著紅酒杯、一黑西裝的油頭中年人,好像是某科技公司老總。
那個穿著紅禮服、端莊婉約的中年, 好像是帝都四大名媛之一。
……
雖然早有心理準備, 但親眼看著那麽多曾經只在雜志、電視裏見過的大佬出現在眼前,南知還是到格外拘束。
這是從未想過會踏足的一個世界、一個讓覺得自己格格不的世界。
正如封震業所言,不適應, 不用強迫自己去適應。
南知拿了幾塊小蛋糕,端著瓷碟坐在角落的秋千上,安靜吃著,時不時無聊地觀察四周。
不遠, 穿著一襲紅修長的封雲挽背對著, 正站在角落打電話。
但細看發現,的耳環居然只戴了一只,可能是掉了。
就在南知想著要不要去打個招呼,順帶提醒一下耳環的事時,一個穿著黑西裝的影先一步朝封雲挽走了過去。
男人溫文爾雅, 南知記得, 肖璐璐曾經給看過他的采訪照——
那是景氏集團新上任的總裁景延。
同是豪門出, 認識似乎并不奇怪, 南知本沒有放在心上,但下一秒,卻突然看到景延從口袋裏掏出一只耳環,極為自然地塞進了封雲挽的掌心。
他的腳步沒有停留,甚至沒有和封雲挽打招呼,像是單純做了件好事不留名。
Advertisement
而封雲挽也沒有任何意外,神自若地把耳環戴上,便又開始和邊人寒暄。
這不起眼卻親的舉,沒有引起周圍任何人的關注,南知卻差點被橙嗆住,默默移開了眼神。
難不,之前聽說封雲挽和男朋友一起住,那個男朋友就是景延?
就在出神的時候,餘好像察覺到一凝視。
側頭一看,許亦文和鄭惜惜站在一起,但眼神卻毫不帶遮掩地看著。
南知想起,張姨和說過,雖然第一次見面,許亦文的失約讓鄭惜惜不太高興,但後來在鄭董的撮合下,倆人又見了一面,許亦文的態度不明朗,鄭惜惜卻好像看上了他。
看起來也的確如此,眼前的鄭惜惜端著一個瓷碟,吃一口,看許亦文一眼,臉上帶著溫的笑意。
但很快,當意識到許亦文的視線落在南知上時,臉上的笑意就慢慢消失了,看著南知的眼神,也多幾分打量的意味。
許亦文往前邁了一步,似是想朝走來,幸好,被一陣鼓掌聲打了步調。
南知回頭去,一深藍綢唐裝的封老爺子拄著龍頭拐杖,神矍鑠地從遠的主樓走了出來。
而他旁,封弋罕見地穿上了一黑西裝,滿桀驁退去幾分,卻依舊顯得難以接近。
這是封弋第一次明正大以“封震業孫子”的份出現在公衆面前,在此之前,大多數人對他的印象都是“叛逆、難管教”,因此眼前這個姿拔、氣質高冷的封弋,瞬間令現場的不人倒吸一口涼氣。
而最驚訝的,自然要數許亦文。
這段時間,他雖然跟著母親去過老宅一兩次,但每次封弋都不在家,他怎麽也想不到,封弋,居然就是以前那個假沈佚。
他握拳頭,視線直直看著封弋和老爺子,直到發現他們轉朝南知而去。
“知知,來了啊。”老爺子今天格外高興,眼睛皺紋微微疊起。
南知迎了上去,笑著遞出了手裏的禮盒:“封爺爺,生日快樂。”
其他人的禮,封震業都是轉給一旁的傭,讓們先暫時統一保管,但南知的禮卻不一樣。
封震業剛拿到手,就把手裏的拐杖遞給封弋,而後興沖沖地拆了起來。
這不免讓旁人,對這個看起來年紀輕輕、又很面生的姑娘,多了幾分忌憚。
南知送的,是一套圍棋子。
“這是之前去古鎮窯廠,跟那邊的老師傅學著親手制作的,可能質量沒有那麽好,還封爺爺不要嫌棄。”
封震業嚴肅了神:“你說這什麽話,你送的禮,爺爺有過不喜歡的嗎?這麽多禮裏,就你送的最合爺爺心意。”
封震業的話不輕不重,但近的不人,都聽在耳朵裏。
其實是得罪人的話,但封震業顯然有這個囂張的權利。
把南知送的禮小心翼翼又放好,封震業朝許亦文招了招手。
許亦文立刻舉步走到南知邊。
封震業擡手指了下封弋,向許亦文介紹:“小文應該還是第一次見吧?你表哥,封弋。”
許亦文還沒從震驚中緩過來,聞言沒有任何舉。
封震業覺得奇怪,自己這外孫一向很有禮貌,此刻是怎麽回事?
“小文,怎麽不喊人?”
許亦文這才回神,松開握得死的右手,朝封弋手,笑得很是客套:“哥,歡迎回國。”
封弋僅僅只是扯了扯角。
見到他這表,南知幾乎都能想象到下一秒他裏又要說什麽不給面子的話,但今天這場合,顯然不合適。
手,借著他的遮擋,輕輕扯了扯他的西裝下擺。
封弋果不其然聽話地閉了,但擡手的姿態依舊有點囂張,只握了不到一秒就松開了。
“封董!”
有人舉著紅酒杯過來打招呼,封震業被轉移了注意力,自然也沒關注到倆人之間暗藏的劍拔弩張。
“小文,你和阿弋一起,陪外公去招待賓客。”說完,封震業轉頭看向南知,“知知,你休息一會兒。”
“好的,封爺爺。”
南知不知道,這算是老爺子幫解了許亦文的圍還是湊巧,但也不想去想這麽多,只默默退回角落松了口氣。
傍晚六點十八分,壽宴正式開席。
雖然同在主桌,但和許亦文之間隔了三個位置,又不是正對面,恰好避免了低頭不見擡頭見。
而封弋的位置,卻在旁邊。
顯然是有人私下過手腳。
有服務生過來問喝什麽酒。
之前醉酒的覺,讓南知終生難忘,而且今天心不錯,并不想喝酒,但視線掃過桌上那一溜的酒,想喝飲料的話,卻說不出來了。
“紅……”
“紅酒吧”三個字只說了一個,面前的紅酒杯卻被人移開。
封弋淡聲道:“給一杯茶。”
還有茶啊?
南知愣住。
但服務生卻毫不覺為難,恭敬地道了聲:“請稍等。”
不用喝酒,南知心裏多是開心的,但又覺得一杯茶放在一桌子酒杯裏,顯得跟小孩兒似的,問封弋:“別人都喝酒,我喝茶會不會很奇怪?其實我會喝酒的。”
封弋像是輕哼了一聲,腦袋湊了過來。
“還想再占一次便宜?”
他說的有點輕,宴客廳裏又嘈雜,但南知還是聽到了他的話。
怎麽會有這麽不要臉的人啊?
被氣到,低聲嘟囔:“你醉了才占人便宜!”
封弋慢悠悠地喝了口紅酒,“哦?怎麽占的?詳細說說。”
南知撇了撇,哪好意思跟他細說那天晚上的細節,比如落在鎖骨的那個吻。
飯局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期間一直有人來向老爺子敬酒。
可能是下午的時候發現在老爺子面前面子很大,也有不人順勢將視為了敬酒對象。
封弋在的時候還好,他一臉冷漠,指關節在桌上敲敲,對方就明白了意思,不敢再勸南知喝酒。
但封弋出去接電話時候,就難做了。
最終,南知也無奈選擇了尿遁。
莊園很大,服務生們又都在宴客廳,南知繞了一圈,才終于看到洗手間的指示牌。
走廊外不遠,封麗樺像是在教訓服務生。
南知經過時,看到拿起餐車上的一對筷子,怒氣沖沖地扔了出去,憤怒地責罵道:“我有沒有跟你們說過?筷子都得是定制的?”
“抱歉封小姐。”服務生立刻彎腰道歉,“定制的筷子數量不夠了,這些筷子也是新的,是經理特意……”
“經理?你讓你們經理來跟我說!我們家從來不用這些幾十塊錢的東西!破爛玩意兒拿進去,丟誰的人?!”
……
南知無語地搖了搖頭。
走了幾步,卻腳步頓住。
突然想起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
作者有話說:
大家猜猜什麽事?哈哈哈哈哈真的真的很重要!
ps:很快就要結婚啦!
猜你喜歡
-
完結2426 章

總裁的嬌寵妻
她本是名門千金,卻一生顛沛流離,被親人找回,卻慘遭毀容,最終被囚禁地下室,受盡折磨,恨極而亡。 夾著滿腔怨恨,重生歸來,鳳凰浴火,涅槃重生。 神秘鑰匙打開異能空間,這一世,她依舊慘遭遺棄,然置之死地而后生,她不會再重蹈覆撤,她要讓那些曾經踐踏過她的人,付出代價。從此以后,醫學界多了一個神秘的少女神醫,商界多了一個神秘鬼才....
243.7萬字8 214071 -
完結303 章

豪門盛寵之陸總寵上癮
他是海城最尊貴的男人,翻手可顛覆海城風雨,卻獨寵她一人。 “陸總,許小姐又有緋聞傳出。” 男人眼睛未抬半分,落下兩字“封殺。” “陸總,許小姐想自己當導演拍新戲。” “投資,她想要天下的星星也給她摘下來。” “陸總,許小姐不愿意結婚。” 男人挑眉抬頭,將女人強行連哄帶騙押到了民政局“女人,玩夠了娛樂圈就乖乖和我結婚,我寵你一世。”
67.5萬字8 27643 -
完結388 章

愛你日久彌深
叢歡只是想找個薪水豐厚一點的兼職,才去當禮儀小姐,不料竟撞見了自家男人陸繹的相親現場。叢歡:陸先生,你這樣追女人是不行的。陸繹謔笑冷諷:比不上你,像你這樣倒追男人的女人,只會讓人看不起。雙份工資打給你,立刻離開,別在這礙眼。叢歡:好好好,我這就走,祝你成功追美、永結同心。陸繹:就這麼將自己心愛的男人拱手讓人,你所謂的愛果然都是假的。叢歡忍無可忍:狗男人,到底想怎樣!
74.5萬字8 578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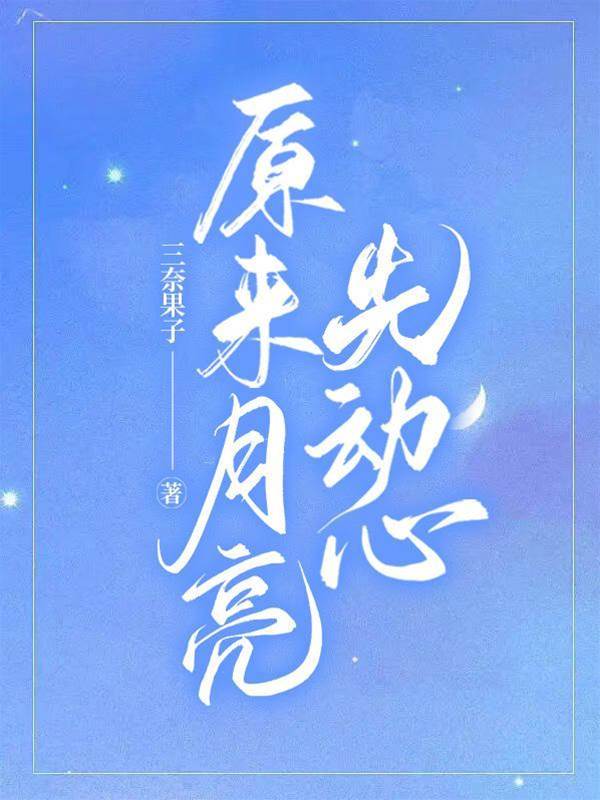
原來月亮先動心
【已簽約出版】原名:《喝醉後,我錯撩了閨蜜的小叔》【蘇撩 甜寵 教授 七歲年齡差 校園 救贖】【蘇撩腹黑小叔X古靈精怪少女】江落是十足的手控,為了一張手照,搭訕了一位帥哥,不料事後發現,對方居然是她閨蜜的小叔!江落腰板挺直,站姿乖巧:“小、小叔好。”……多年後,南大突然傳出生物學係的高嶺之花傅教授已經結婚的謠言。同事:“傅教授,這些謠言都是空穴來風,你別信……”“澄清一下,這不是謠言,”傅紀行冷靜補充,“我確實結婚了。”!!!江落跟傅紀行扯證時,她正讀大四。扯完證回去的路上,男人手裏拿著小本子,溫聲提醒:“喊了我這麼多年的小叔,是不是該換一下稱呼了?”“什、什麼稱呼?”“比如……”男人的吻落在她唇上——“老公。”
21.2萬字8 8278 -
完結506 章

離婚止損
兩人的娃娃親在景嶢這裏根本沒當回事,上學時談了一段張揚且無疾而終的戀愛,迫於家人的壓力,最後還是跟褚汐提了結婚。兩人結婚之後像普通人一樣結婚生女。外人看來雙方感情穩定,家庭和睦,朋友中間的模範夫妻。兩人婚姻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褚汐打小性格溫柔,品學兼優,自從知道自己跟景嶢有娃娃親的時候,就滿心歡喜的等著兩人結婚,總以為兩人一輩子都會這樣在一起。偶然的一天,聽到景嶢用一種意氣風發且張揚的聲音跟自己的母親說他談戀愛了,有喜歡的人,絕對不會娶她。此後再見麵,褚汐保持合適的距離,遇見了合適的人也開始了一段戀愛。兩個人的戀愛結果均以失敗告終,景嶢問她要不要結婚,衝動之下褚汐同意了。衝動之下的婚姻,意外來臨的孩子,丈夫白月光的挑釁,都讓她筋疲力盡。心灰意冷之後提出離婚,再遭拒絕,曆經波折之後達到目的,她以為兩人這輩子的牽掛就剩孩子了。離婚後的景嶢不似她以為的終於能跟白月光再續前緣,而是開始不停的在她麵前找存在感!
99.2萬字8.18 228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