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見被我哥死對頭強取豪奪后》 第1卷 第55章 你身上沒臟就好
沒想到正如裴致所說,晚上真的下起了雨。
這場雨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裴晰出門的時候,雨已經停了。
榆市已經步秋季,一場秋雨一場寒,空氣中滿是雨后獨有的味道,裹著一清冷的氣息。
裴晰小心地拎著手里的飯盒,避著路上的水坑。
準備去江承家里看看他,帶著李媽新熬的大骨湯。
昨天晚上,已經在微信上跟江承提前打好了招呼。
因為怕骨頭湯會被晃撒,裴晰打了一輛車,車子開不進小巷,只能停在馬路邊。
下車之后,裴晰就看到路邊站著一個人。
他穿著一件黑的沖鋒外套,雙手揣在兜里,拉鏈拉到頂,下埋在領里,只出凜冽的眉眼和直的鼻梁。
黑發黑的襯托下,一張臉顯得更加白。
看到裴晰,他本來幽黑平靜的眼睛忽然亮了一瞬,抬腳大步朝走過來。
裴晰沒想到江承會出來等,等到江承走近,看到他的鼻尖已經被風吹的有些泛紅。
Advertisement
也不知道是在路邊站了多久。
“我認識路的,你不用出來接我。”裴晰看著他說。
江承目一頓,然后低聲道:“沒關系,反正在屋里待著也很無聊。”
裴晰聞言點了點頭,“也是,也不能總是在屋里待著,是該多活活。”
江承低低地“嗯”了一聲。
兩人并肩沿著大路往巷子口走,路中有車迎面駛來,裴晰覺自己手臂一。
下一秒,被拉向馬路側,江承將自己和調了個位置。
走里面,江承走外面。
整個過程很快,胳膊上的力量一即分,裴晰都還沒有反應過來。
“我又不傻,有車過來自己會躲。”仰頭看著江承的側臉,莞爾一笑。
江承雙手依舊揣在兜里,眼睛看著前面的路,“嗯”了一聲。
那姿態仿佛是,雖然他知道裴晰不會有危險,但他就是想讓走在里面。
一碼歸一碼。
裴晰看著他的“冷酷”模樣,歪著頭看他一眼,語帶笑意:“不過還是謝謝你啊。”
今天沒有扎馬尾,頭發半披著,江承余看到頭發順地從肩膀上下來,染上一層。
“不用謝。”他揣在兜里的手了。
把換到馬路側是下意識的舉,他自己甚至都在胳膊出去之后才反應過來。
兩人并肩走進小巷,因為下了雨,所以本就凹凸不平的路面上積了很多水,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洼。
小巷很窄,兩人小心地避著水坑,后忽然傳來托車的嗡嗡聲,裴晰下意識去看,托車卻已經飛馳而來,濺起一片泥水。
裴晰低呼一聲,江承已經摟著的肩膀,擋在了前。
托車從江承后疾馳而過,嘩啦一聲,水坑里的水被濺起大半個人的高度。
裴晰甚至聽到大半的泥水落到江承服上的聲音。
連忙去看,江承的后背上果然沾上了大片泥水,星星點點,臟污一片。
裴晰眉頭瞬間皺了起來,“什麼人啊,這也太沒有素質了!”
又扭頭去看,那托車早就沒影了,想找人算賬都找不著了。
江承卻渾不在意地搖了搖頭,來回在上打量了兩遍,輕聲說:“沒事,你上沒臟就好。”
裴晰一怔,抬頭到江承認真的目,心臟不自覺地震了一下。
上確實一丁點泥水也沒有被濺上。
他長得高,肩膀又寬,覆過來的時候,整個人將擋得嚴嚴實實的。
裴晰耳畔不自覺熱了熱,扯了下江承的袖,垂眸低聲道:“...快回去換服吧,快走。”
兩人很快走到江承家里。
裴晰是第三次來這里,居然才發現,江承家的院子里有一個葡萄藤架,上面還結了一些果子。
因為下雨的緣故,他把洗完的服晾在了里屋的屋檐下,看樣式似乎依舊是之前的那幾件。
裴晰注意到江承的服很,也都是毫無新意的黑白灰。
跟裴致的琳瑯滿目的柜完全形了鮮明的對比。
江承打開里屋的門,裴晰走了進去,屋里依舊很是整潔干凈,有點無法想象,江承在傷的況下是怎麼打理的衛生。
“我進去換一件服。”江承看著裴晰,指了指臥室的方向。
“哦,好。”裴晰點頭,“快去吧。”
江承點頭,剛要抬腳往臥室走去,卻忽然轉,走到裴晰面前。
“裴晰,手。”他輕聲說。
裴晰一怔,下意識睜了睜眼睛,卻還是乖乖地出手。
下一秒,掌心落一個溫熱的東西。
裴晰低頭,手指收了一下。
是一罐旺仔牛,熱的。
猜你喜歡
-
完結890 章

蛇仙相公慢慢來
一場重病,讓我懷胎十月,孩子他爹是條蛇:東北出馬仙,一個女弟馬的真實故事……
202.3萬字7.67 80747 -
完結834 章

寵婚蜜愛:傅先生他又想娶我了!
結婚兩年,兩人卻一直形同陌路。他說:「一年後,你如果沒能懷孕,也不能讓我心甘情願的和你生孩子,那好聚好散。」她心灰意冷,一紙離婚協議欲將結束時,他卻霸佔著她不肯放手了!!
77.3萬字8 94329 -
完結267 章

被渣後小叔叔寵我入骨
那一夜,淩三爺失身給神秘的女人,她隻留下兩塊五和一根蔫黃瓜,從此杳無音訊……被養母安排跟普信男相親的栗小寒,被一個又野又颯的帥哥英雄救美,最妙的是,他還是前男友的小叔叔。想到渣男賤女發現自己成了他們小嬸嬸時的表情,她興高采烈的進了民政局。結果領證之後,男人現出霸道本性,夜夜煎炒烹炸,讓她腰酸腿軟,直呼吃不消!
73.5萬字8 32067 -
完結183 章

成蝶
分手多年後,路汐沒想到還能遇見容伽禮,直到因爲一次電影邀約,她意外回到了當年的島嶼,竟與他重逢。 男人一身西裝冷到極致,依舊高高在上,如神明淡睨凡塵,觸及到她的眼神,陌生至極。 路汐抿了抿脣,垂眼與他擦肩而過。 下一秒,容伽禮突然當衆喊她名字:“路汐” 全場愣住了。 有好事者問:“兩位認識” 路汐正想說不認識,卻聽容伽禮漫不經心回:“拋棄我的前女友。” - 所有人都以爲容伽禮這樣站在權貴圈頂端的大佬,對舊日情人定然不會再回頭看一眼。 路汐也這麼以爲,將心思藏得嚴嚴實實,不敢肖想他分毫。 直到圈內人無意中爆出,從不對外開放的私人珠寶展,今年佔據最中央的是一頂精緻又瑰麗的蝴蝶星雲皇冠。 據傳出自商界大佬容伽禮之手,於他意義非凡。 好友調侃地問:“這麼珍貴的東西,有主人了嗎?” 容伽禮不置可否。 殊不知。 在路汐拿到影后獎盃當晚,滿廳賓客都在爲她慶祝時,她卻被抓住,抵在無人知曉的黑暗角落處。 路汐無處可躲,終於忍不住問:“容伽禮,你究竟想幹什麼?” 容伽禮似笑非笑,語調暗含警告:“你以爲……回來了還能輕易躲得掉?” 路汐錯愕間,下一秒,男人卻將親手設計的皇冠從容的戴在路汐發間,在她耳畔呢喃:“你是唯一的主人。” ——在廣袤的宇宙空間,蝴蝶星雲終將走到生命盡頭,而我給你的一切,比宇宙璀璨,亙古不散。
27.2萬字8.18 5293 -
完結2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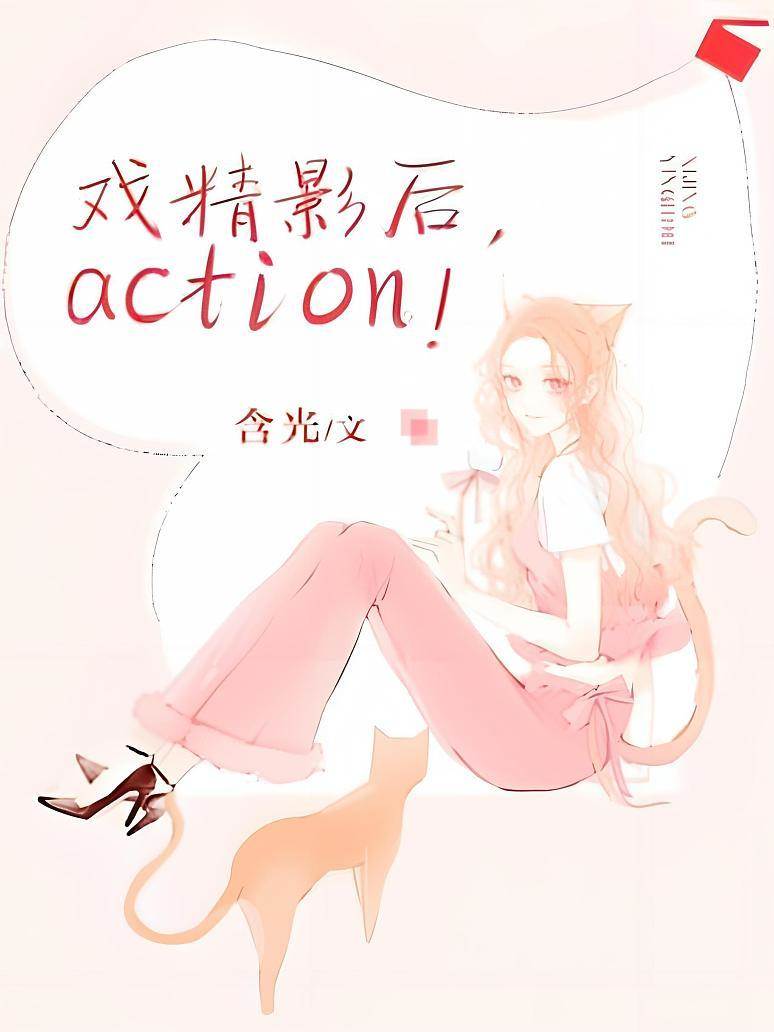
戲精影后,action!
影后楚瑤瑤被人害死一命嗚呼,醒來后已經是20年后,她成了臭名昭著的十八線女明星。 渣男渣女要封殺她?小助理要踩她上位?家里重男輕女要吸干她?網友組團來黑她? 最可怕的是身材走樣,面目全非! 影后手握星際紅包群,這些全都不是問題。星際娛樂圈大佬們天天發紅包,作為影后迷弟迷妹只求影后指導演技。 第一步減肥變美。 第二步演戲走紅。 第三步虐渣打臉。 第四步談個戀愛也不錯……隔壁的影帝,考不考慮談個戀愛?
40.3萬字8 1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