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嫁豪門,首富小叔哄著我結婚》 第1卷 第096章 郁家的人都很討厭你
隨著郁寒深一步步走近,司桐一步步往后退。
“洗完了?這睡倒是適合你。”郁寒深的視線直白地上下打量司桐。
剛洗過澡的小姑娘,上帶著一清澈的水霧,整個人看起來似水,干凈清純。
質睡穿在上,襯得孩清麗的容多了幾分。
說完,郁寒深的視線落向沙發背。
司桐察覺到,猛地想起來剛放在那邊晾著的,臉上一熱,趕撲上去撿起來揣在外套兜里。
“您進來怎麼不敲門啊?”的手在口袋里攥噠噠的布料,語氣不自覺嗔,帶著不滿。
郁寒深眼底含笑,低沉的嗓音漫不經心:“藏了什麼寶貝?”
聽出他明知故問,司桐心里又又氣,臉上更紅,把頭扭去一邊不看他:“我要睡覺了。”
郁寒深手掰正孩的小臉,了的臉頰,說起正事:“以后賀恒做你的專職司機,出門不要再坐公地鐵,想去哪兒提前聯系他。”
司桐下意識拒絕:“不用這麼麻煩。”
一個學生,而且是眾所周知的窮學生,忽然冒出來專車,顯得很可疑。
而且郁寒深的車,肯定都是豪車,更惹眼。
話音未落,被郁寒深強勁的力道拉坐下來,坐在男人大上。
“不給你安排輛專車,以后再遇到壞人怎麼辦?”郁寒深摟著,手進孩外兜里,把那條噠噠的拿出來,面不改地展開放在之前的位置。
司桐想阻止已經來不及,眼看著那麼私的東西,就這麼大咧咧地呈現在郁寒深括的肩膀旁邊。
得想找個地鉆進去。
可是郁寒深卻神如常。
“賀恒手不錯,有他跟著你,我放心。”郁寒深說著,抱小孩似的把小姑娘往懷里抱一點,呼吸間都是孩上的人香。
Advertisement
他把手里的半截香煙咬在角,忽地抱著司桐起,朝床邊走去。
司桐被他這舉嚇得心里咯噔一聲。
“郁、郁總……”張得呼吸不穩,“我、我不要……”
郁寒深把司桐放在床上,手撐在耳邊,另一只手從邊拿走煙,熄滅在床頭柜的煙灰缸里。
“不要什麼?”郁寒深說著,坐在床邊,慢慢俯下,薄落在孩的臉頰,一邊輕輕蹭著小姑娘的,似親非親。
一邊嗓音低啞地問:“說話,不想要什麼?”
司桐所有的都集中在臉側,男人的微涼,可呼吸卻那麼燙人。
繃著,完全不敢,也不敢開口。
半夜三更,孤男寡共一室,本就是件危險至極的事。
眼前又是個有正常生理需求的年男,能覺到郁寒深的忍和克制,也能覺到他的克制快到達極限。
如果不是礙于的學生份,恐怕郁寒深早就……
司桐不敢深想,咬著閉上眼睛,控制不住地輕。
此時只覺自己像是被猛按在爪下的獵,無力逃,只能等待被慢慢吃掉。
以前和郁知珩在一起,正是最青純粹的年紀,那時候在教室過道上偶遇,相視一笑,就很甜。
做過的最出格的事,也不過是晚自習一起在場散步,牽一下手。
郁寒深卻完全不同,帶著年男人濃烈的和強勢的侵占,肆無忌憚,讓不知道怎麼面對,本無從招架。
好一會兒。
耳邊麻熱燙的呼吸撤離,頭頂響起男人抑的低沉聲音:“司同學,晚安。”
司桐沒說話。
隨后,聽見窗簾合上發出的輕微聲響,接著穩健的腳步聲離去,房門被帶上。
一直到房間歸于平靜,才敢睜開眼。
燈被關了,只在衛生間門口留了一盞昏暗的小燈,司桐拍了拍撲通跳的心臟,打定主意,以后要盡量避免和郁寒深單獨接。
好在第二天醒來,郁寒深已經不在別墅。
賀恒倒是在。
看見司桐,他笑了笑:“郁總我以后跟著你,藥我順便帶來了。”
司桐沒想到郁寒深昨晚剛說完,今天就安排上了,心知要是不同意,那個男人又會‘懲罰’,只好默許。
吃完飯喝完藥,司桐去了醫院。
穿過門診大廳去后面的住院大樓,意外遇見秦思涵。
司桐本想當沒看見徑直走開。
“桐桐。”秦思涵卻住。
司桐柳眉皺起,看著擋在面前的秦思涵,聲音冷淡:“有事?”
“我懷孕了。”秦思涵臉有些蒼白,笑容卻很甜,“本來我不想這麼著急要孩子的,可是知珩天天晚上纏著我,一不小心,就懷上了。”
司桐面沉靜,眼底一緒都沒有,也不接的話:“如果沒別的事,麻煩讓開。”
秦思涵擋著沒,著平坦的小腹,又道:“我搶了你的男人,搶了你郁家的位置,你很恨我吧。”
“不過,就算我不搶,你也進不了郁家的門,你知道郁家的人都怎麼說你嗎?”
秦思涵邊笑容不減,“我嫁進郁家這一個月,聽說了一些有關你的傳聞。”
“知珩以前因為你的事,在家里經常耍酒瘋,所以郁家的人格外討厭你,說你腳踩兩條船、水楊花,說你坐牢是罪有應得,就算我不足你們,你也進不了郁家的門。”
最后幾句,倒是讓司桐臉上有了點變化,去年國慶隨張夢玲去郁家老宅,正是因為郁知珩耍酒瘋扔酒瓶,才了傷。
張夢玲也說過郁知珩是為了前友才這樣,還說過‘他那個前友人品不怎麼樣,跟他往的同時還勾搭另一個男生’這樣的話。
司桐面的變化很淡,恢復得也快,“說完了嗎?說完麻煩讓開。”
秦思涵見自己說了半天,面前的孩始終淡靜,預想中的嫉妒和不甘,統統都沒從司桐臉上看到。
不皺了皺眉,四年不見,這個賤人倒是變得難搞很多。
不信司桐真的不郁知珩了。
郁知珩不管是長相、家世、還是才華,都是頂尖,整個海城找不出比他更優秀的青年。
司桐曾經那麼他,怎麼可能說放下就放下。
司桐越是表現得冷靜淡然,秦思涵心底的危機越濃烈。
也不知道為什麼,懷孕前,郁知珩和如膠似漆,尤其是到了晚上,總是要折騰很久。
可是自從懷孕,忽然從郁知珩上到某種疏離。
那種若即若離,似是而非的疏離,讓覺得不安。
明明他還是對照顧有加,可就是生出一莫名的恐慌,不知道為什麼。
這讓又想起結婚前,在郁知珩公寓看見的那幅司桐的素描畫。
直覺,郁知珩心底還是有司桐的。
秦思涵還想再說點什麼來試探司桐的真實心,郁知珩的聲音忽然在后響起:“涵涵,藥拿好了,我們走吧。”
今天秦思涵來產檢,因為孕吐嚴重,醫生開了點藥。
在秦思涵轉之際,司桐徑直從邊繞過去。
“桐桐。”秦思涵再次住,雙眼盯著:“你會祝福我和知珩,對嗎?”
司桐聽懂了的言外之意,秦思涵是在問,會不會回頭搶郁知珩。
司桐卻只覺得這兩個人腦子都不好,一個個的非要糾纏。
沒說話,也沒回頭,就像沒聽見。
穿過連廊來到住院部,坐進VIP病房專用電梯,司桐看著電梯金屬壁映出的自己。
耳邊,是秦思涵的話,郁家人很討厭郁知珩的前友。
其實不用秦思涵說,司桐也知道,郁知珩發酒瘋那晚,從郁家人難看的臉上不難猜出,他們對郁知珩為前友發瘋的行為很不滿。
別人是什麼看法倒是不在意,郁寒深是怎麼想的?
會不會也覺得罪有應得?
陸鳴玄已經死了,除了秦思涵,沒有任何人或者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當年的事,是那兩人聯合設下的圈套。
如果能證明和陸鳴玄發的那些聊天短信,是和曾經的好友秦思涵發的,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提起申訴,還自己公道。
猜你喜歡
-
完結271 章

且以深情共余生
相似的聲音,相似的容貌,遇見了同一個他。兜兜轉轉,走走停停,時光不改蹉跎。如果上天再給她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一定奮不顧身愛的更加用力!
50萬字8 9205 -
完結378 章

玄門回來的假千金又在擺攤算卦了
肖梨在玄門待了一百年,同期進來的那條看門狗小黑,都已經飛升上界,她還只能守著觀門曬太陽。老祖宗顯靈告訴她,“肖梨,你本來自異界,塵緣未了,若想飛升,还得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却凡尘杂事,方可勘破天道!” 回到现代,肖梨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这一世,没有留念,两手空空跟着亲生父母离开肖家。 圈内人都在等着,肖梨在外面扛不住,回来跟肖家跪求收留。 却不想…… 肖梨被真正的豪门认回,成为白家千金,改名白梨。
64.4萬字8 60458 -
完結189 章

荒腔
沈弗崢第一次見鍾彌,在州市粵劇館,戲未開唱,臺下忙成一團,攝影師調角度,叫鍾彌往這邊看。 綠袖粉衫的背景裏,花影重重。 她就那麼眺來一眼。 旁邊有人說:“這是我們老闆的女兒,今兒拍雜誌。” 沈弗崢離開那天,州市下雨。 因爲不想被他輕易忘了,她便胡謅:“你這車牌,是我生日。” 隔茫茫雨霧,他應道:“是嗎,那鍾小姐同我有緣。” 京市再遇,她那天在門店試鞋,見他身邊有人,便放下了貴且不合腳的鞋子。 幾天後,那雙鞋被送到宿舍。 鍾彌帶着鞋去找他。 他問她那天怎麼招呼都不打。 “沈先生有佳人相伴,我怎麼好打擾。” 沈弗崢點一支菸,目光盯她,脣邊染上一點笑:“沒,佳人生氣呢。” 後來他開的車,車牌真是她生日。
28.8萬字8 17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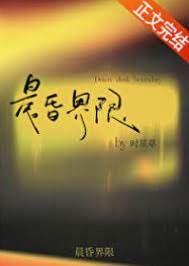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