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扮男裝后皇帝卻彎了/苟官》 第107章 【番外】假如2
“還沒打呢。”種蘇忙道,“好巧啊,今日又遇到。”
年看了種蘇一眼,又瞥向阿魯與他后那幫同伙。
“他們欺負你?”
種蘇了鼻子,覺得倒說不上欺負,同齡人間的打鬧是常有的,只是這阿魯比較不講武德而已。
阿魯卻被年那一瞥看的心中微,只覺有莫名的迫,再看他后的兩名高大隨從,其中一名還手中抱著劍。
阿魯放下叉腰的手臂,面退意。
然而就在這時,種瑞卻領著一伙人從街角那頭遠遠沖過來。
“胖魯,你還敢堵我妹!找死!”
年聽見這聲,側首看種蘇,面驚訝。
阿魯見種瑞氣勢洶洶沖來,頓時驚慌,急之下,先推了面前的種蘇一把。種蘇正站在街邊大樹下,樹上被臨街的商戶釘了幾顆釘子,平日里掛曬點臘食。
種蘇毫無防備,腳下一個趔趄,眼看就要撞上樹干。
千鈞一發之際,旁的年出手,以手掌墊在腦后。
種蘇腦袋結結實實的撞了上去,那一下不輕,似乎聽見年嘶了聲。
種蘇來不及看,種瑞等人已沖過來,立刻開始混戰。
“公子小心!”
隨從馬上護住年,擋在他前,年則順手將種蘇拉至后,同樣將種蘇隔在混戰圈外。
隨從試圖制止這場混,奈何兩伙半大的孩子人數著實不,又得顧及年安全,只能出聲喝止,卻收效甚微。街邊的人家也被驚,紛紛出來制止。
“都給我住手!”
最后一聲天降怒吼,學堂的夫子揮舞著教鞭出現,終于令這場混戰結束。
“公子,你的手!”
種蘇低頭一看,方發現年手背上一條痕,顯然被樹干上的釘子劃傷,傷口還頗深,珠一顆顆往外冒出。
Advertisement
見了,阿魯種瑞等人都慌了,不敢再做聲。
年看著手背,微微擰眉,隨從慌張的要帶年回家,一旁有人建議前面不遠就是醫館,于是老夫子衡量了下,見種蘇與年認識,便讓種蘇與兩個孩子帶年去醫館,種瑞與阿魯等則被拎回學堂,接問詢。
種蘇帶年匆匆進醫館,那兩個孩子并不認識年,只在外頭百無聊賴的等著,種蘇始終陪在年邊。
清理傷口的時候,年的手微微了下。
“很疼吧。”
種蘇抿著,十分擔心與愧疚,從兩個隨從的神來看,他從小到大一定很傷,他手指修長,手背上的皮潔無比,這道傷便猶為打眼。
“可千萬不要留疤呀。”種蘇憂心道。
年說,“我又不是姑娘家,一點疤痕無妨。”
種蘇道:“不是姑娘家也不行,這麼好看的手,多可惜呀。”
年看了種蘇一眼,頓了頓,道:“你是孩兒?”
“剛剛你聽到啦?”種蘇點點頭,大方的承認,“我是孩兒,剛那個模樣 與我一樣的是我哥,我們是雙生子。”
“我種蘇,小名阿蘇,”種蘇又道,“你什麼名字?以前沒有見過你呢。”
年回答:“我姓燕,單名一個回。京城人士,游學路過此地……”
這與先前種蘇的猜測差不多,只沒想到是從長安而來,種蘇眼中一亮,長安啊,那可是大康都城。
說話間,大夫已理好傷口,上過藥,用薄紗包裹纏繞了半個手掌,只出幾手指。
“這幾日注意不要沾水,食辛辣,夜間或會有些痛,小公子便忍著點了。”大夫叮囑道。
種蘇先一步自覺的付了藥費,而后與燕回離開醫館。
門外的兩個小孩見沒事了便跑走了,作為打架的主要參與者,種蘇也還得回學堂去做個待,不能耽擱了。
“燕公子,你住哪里啊?”種蘇問。
“佑恩寺。”
“這樣啊,”種蘇道,“那你明日出來嗎?到時我陪你去換藥。”
佑恩寺位于錄州郊區,離錄州城中說遠不遠,說近不近,問題還在于,它曾是一座皇家寺廟,如今雖不如曾經盛名,卻也香火繁盛,相應的規矩也頗為森嚴,每月初一十五方對外敞開大門,平日里不是人人都能隨時。
燕回能夠借住佑恩寺大抵是因為他的游學份,這一點佑恩寺倒是跟其他寺廟一樣,一貫優待讀書人。
如今非初一和十五,種蘇又還得上學,恐怕不能去佑恩寺尋燕回。
“不一定出來,”燕回看看種蘇,說,“這傷只是意外,且是小傷,你不必太過自責。走吧,后會有期。”
他眼中仍有種淡淡的疏離,話語卻十分溫和,只是那語氣中有幾分不容置喙。
種蘇哦了一聲,心中的愧疚因他的話而稍稍減淡,點了點頭了,也有模有樣的說了聲后會有期,便轉去往學堂。
已近黃昏,金的晚霞鋪滿天邊與街道,種蘇走了一段,回頭,朝燕回揮揮手,面上依稀可見明亮的笑容。
燕回還站在原地,本能的想要回應,忽然發現抬起的是傷的手,又馬上放下,換了另外一只,沖種蘇揮了揮。
這次當街打架影響惡劣,夫子了解清楚況后,一個不饒,將幾大主犯通通拎到那條街的路口樹下罰站。
當街斗毆,何統?喜歡打架是嗎,不怕丟臉是嗎,便站那里去,讓所有人好好看看!
那條街是附近學子們上學下學的必經之路,種瑞與阿魯等人頂著書本齊刷刷排排站,一時引來陣陣笑與指指點點。
種蘇雖是無辜被堵的人,卻畢竟參與其中,前日結結實實確實打過一架,因而也逃不掉責罰。但念在是被迫參與,且是孩兒,便不用當街罰站,改而站在阿魯家店中門旁,算是給留了份面。
阿魯的爹瘦瘦長長,如同麻稈兒,終日好彈琴蕭,木訥寡言,不 大管家中事,人倒是個老實人。
見種蘇在自家店里罰站,等夫子走了,便將種蘇到柜臺后坐著,還給沖了杯糖水。
“姑娘家家的,打什麼架,不下心傷了臉,以后怎麼嫁人?孩子溫一點才討人喜歡。”阿魯爹嘟嘟囔囔的說。
種蘇抱著瓷杯,喝著甜甜的糖水,笑笑的聽阿魯爹絮叨,也不反駁,晶亮的雙眸盯著門口經過來往的行人。
糖水即將喝完之際,種蘇眼中一亮,咕嘟兩口喝完杯中剩余,將杯子放下,對阿魯爹道了聲謝,便匆匆跑了出去。
“燕公子!”
燕回聞聲回頭,他今日穿了件月白錦袍,腰上墜著只碧綠玉佩,猶如芝蘭玉樹般。
“等到你了!”種蘇笑著道。
“你等我?”燕回看著種蘇,微微揚眉,“昨天我并沒有說一定出來。”
“你說不一定。”種蘇歪歪頭,“所以也有可能出來嘛——不知為何,我覺你會來。”種蘇眨眼,那意思很明顯,看,我的覺是對的。
燕回又揚了揚眉,不置可否。
“你去換藥嗎?”種蘇問。
“嗯。”
“我陪你去。”
“其實不必……”
“走吧走吧。”
燕回不是個能被輕易說服和掌控的人,通常沒人能阻止或違背他的意愿,但種蘇也有的“說一不二”,燕回竟無法拒絕。
種蘇剛走了兩步,卻想起什麼,停下腳步。
“對了,我父親認識一位神醫,家中有些他配制的奇藥,喏,這個是祛痕的,你拿好,以后記得涂。”
種蘇從袖中掏出只小瓷瓶,遞給燕回。
“還有一事,”種蘇說道這里便回頭,沖樹下喊了一聲,“哥!”
種瑞取下頭上頂著的書,面不改的走過來,有模有樣的行了個禮,“燕公子好,我是種蘇兄長種瑞。”
種瑞接著表達了昨日傷到燕回的歉意,又道家中雙親知道了燕回為種蘇了傷,十分過意不去,知燕回為游學學子,便力邀他至家中一坐,吃頓便飯,聊表謝意。
這也是百姓們對游學學子們的一種善意,畢竟無論貧窮或富有,出門在外總不比家中的。
種瑞難得正正經經,這番話說的有禮而誠懇,充分轉達出了種父種母的誠意,燕回看看種瑞,又看看種蘇。
種蘇眼中的期與熱只差滿溢出來,說:“我家廚子做的獅子頭是錄州一絕哦。”
燕回微微笑了,點點頭,“好,那卻之不恭。”
種蘇頓時樂了,眼可見的高興。于是幾人約了時間,種瑞完任務后便又依舊頂著書本回去樹下罰站,種蘇則陪著燕回去醫館換藥,并告知他自己家的地址方位等。
“公子,不是后日要走嗎?怎的……”
回去佑恩寺的路上,隨從這才開口問燕回。
燕回走在前頭,晚霞照在他俊的面孔上,他微微瞇了瞇眼。
他真名李妄,乃大康儲君太子殿下。燕回只是對外所用的名號。
這是他第一次游學,出來已一月有余,錄州并非這次計劃中的停留地,只因前些日子突風寒,便借住佑恩寺,暫行調理。既然來了,稍好后,便到城中四下轉轉。
于是見了撞到面前的種蘇。
“再留幾日,”李妄說,“嘗嘗錄州的獅子頭。”
這是一個理由,也是一個借口,李妄與種蘇認識不過幾日,總共也沒見過幾面,但種蘇每次都笑瞇瞇的,兩只眼睛充滿熱忱。如果他拒絕邀請,或許那雙眼睛會失。
不知為何,他并不想種蘇出那樣的神。
猜你喜歡
-
完結475 章
廚女當家:山裡漢子,寵不休
一朝穿越成食不裹腹,家徒四壁的農家貧戶,還是一個沖喜小娘子。 陳辰仰天長嘆。 穿就穿吧,她一個現代女廚神,難道還怕餓死嗎? 投身在農門,鄉裡鄉親是非多,且看她如何手撕極品,發家致富,開創一個盛世錦繡人生。 唯一讓她操蛋的是,白天辛苦耕耘賺錢,晚上某隻妖孽美男還要嚷嚷著播種種包子。 去他的種包子,老孃不伺候。
87.3萬字7 49745 -
完結1071 章

權寵天下:本候要納夫!
忠遠侯府誕下雙生女,但侯府無子,為延續百年榮華,最後出生的穆千翊,成為侯府唯一的‘嫡子’。 一朝穿越,她本是殺手組織的金牌殺手,女扮男裝對她來說毫無壓力。 但她怎麼甘心乖乖當個侯爺? 野心這東西,她從未掩藏過。 然而,一不小心招惹了喜怒無常且潔癖嚴重的第一美男寧王怎麼辦? 他是顏傾天下的寧王,冷酷狠辣,運籌帷幄,隻因被她救過一命從此對她極度容忍。 第一次被穆千翊詢問,是否願意嫁給她,他怒火滔天! 第二次被穆千翊詢問,他隱忍未發。 第三次,他猶豫了:讓本王好好想想……
102萬字8 40383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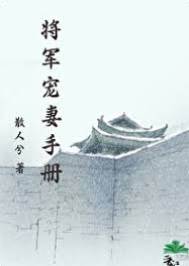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