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后,她被首富前夫掐腰寵》 第67章 第67章 他的解釋
夏淺看著眼前的位于市中心黃金地段的大平層豪宅,有些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愣著做什麼,進來。”傅寒夜不耐。
夏淺不想進。
打死都不想進去。
因為這里才是傅寒夜日常居住的家。
雖說這套豪宅臥室不止一個,但讓住這里,還不如讓住那座冷清的半山別墅呢!
“傅寒夜,你是不是忘了我們要離婚了?現在讓我住進你的公寓,算什麼?當我是人?還是當我是你用一個億買下來的暖床工?你就不怕夏吃醋?”
夏淺凝視著傅寒夜,眼眸中俱是破碎的星,一字一頓地問道。
傅寒夜一時語塞。
不知從哪一個瞬間起,他心中原本很清晰的線就被扯了,剪不斷理還。
他還在試圖理清它們,所以,夏淺的這個回答,他此時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無法解釋,傅寒夜便直接跳過了解釋,霸道地說道:“夏淺,我應該已經說過,離婚的事,我自然會安排,你乖乖配合就行。什麼時候我想清楚了,我們再說離婚的事!”
Advertisement
夏淺心臟驀地跳了一拍。
他說,等他想清楚了,再說離婚的事。
這是不是說,他在猶豫是不是該跟離婚的事?
他是不是……有點喜歡上了?
夏淺知道自己這種想法很賤,但……無法控制自己的胡思想。
就像在黑暗中跋涉太久太久的人,哪怕只是看到一點點疑似的束,也會欣喜若狂,不能自已。
這段之中,太早太深,早已骨,所以注定了毫無招架之力,輸,就是一敗涂地。
和他離婚,斬斷,忍著撕心裂肺的痛,將傅寒夜從自己的生命中剝離出去,并不是狠心用刀清去傷口上化膿的創口,而是壯士斷腕。
單純只是清創,隨著時間的推移,傷口還有愈合的可能。
但斷腕,卻是無論歲月如何流轉,都不可能恢復的傷。
夏淺怔怔地凝著他,有些結地問道:“這是不是……就是說……你……你可能不會跟我離婚?可是夏……夏怎麼辦?你不是和夏已經……”
傅寒夜著夏淺眼眸中,僅僅只是因為他的一句模棱兩可的話,就仿佛枯木逢春一般熠熠生輝的芒,心中最的地方,沒來由地痛。
這應該……就是心疼的覺吧?
他對前半部分的話沒有回答,對最后一個問題反問道:“我和夏已經怎麼了?”
夏淺有些黯然地垂下眸去,說道:“你們那天在辦公室,我親眼看到夏衫凌……”
剛剛一時激,都忘了這件事了。
傅寒夜和夏已經……真的……能原諒他這一點麼?
傅寒夜冷冷地道:“你看了全套?”
夏淺愕然地抬頭,一時沒反應過來,等反應過來之后,臉上頓時通紅一片,眼底也掠過屈辱:“沒……沒有……”
難道還非要悲慘地看完全部過程,才算捉干在床麼?
傅寒夜睨了一眼,有地解釋道:“沒看全,就一口咬定我們做過?”
猜你喜歡
-
完結70 章

完美先生與差不多小姐
文案1 某乎:和年齡相差很多的人談戀愛是種怎樣的體驗? 云舒:謝邀。和先生相差八歲,算是相親認識。 大概感受就是,年紀也不小了,兩人吵架時先生一個眼風掃過,感覺又回到了小時候闖禍被家長發現時大氣都不敢出的狀態。 先生日常訓我三連擊:“你敢和我頂嘴,嗯?”“怎麼和長輩說話呢?”“你怎麼又不聽話了?”。 先生常說和養了個女兒沒差。 當然,年紀大些確實比較會寵人。 文案2 某乎:那些被大家認為雙方很不般配的戀情最后結果都怎麼樣了? 章斯年:謝邀。目前很恩愛。只能說感情一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并非大家眼中的完美先生,太太也并非全是缺點。真正愛一個人,連對方一些亂七八糟的小毛病小習慣都覺得可愛無比。 云舒:網紅圈中的一股清流、娛樂圈中的一股泥石流,放飛自我脫口秀主播。 章斯年:前一本正經大學教授現互聯網金融新銳,S市名媛想嫁排行榜第一名,江湖人稱完美先生。 本文又名:#相親相到了掛過自己科的教授是種怎樣的感受?# #被家里先生罰寫檢討日常# 先婚后愛小甜餅一枚~希望大家喜歡!
21.1萬字8 10267 -
完結609 章

傅少別鬧:夫人太兇猛
初見時傅時弈一身狼狽,對著從天而降的少女求救,少女卻無情地路過。“抱歉我趕時間,下次吧。”“隻要你救我,這兩個億就是你的。”蘇薔沒想到一時心軟救下這個麻煩精就被纏上了,她上學傅時弈成了代理校長,她相親傅時弈來攪局,連她收拾白蓮花妹妹他都趕來看戲。“錢還你,能別老在我麵前晃了嗎?”“我的錢全都給你,讓我在你身邊一輩子。”
114.4萬字8 22076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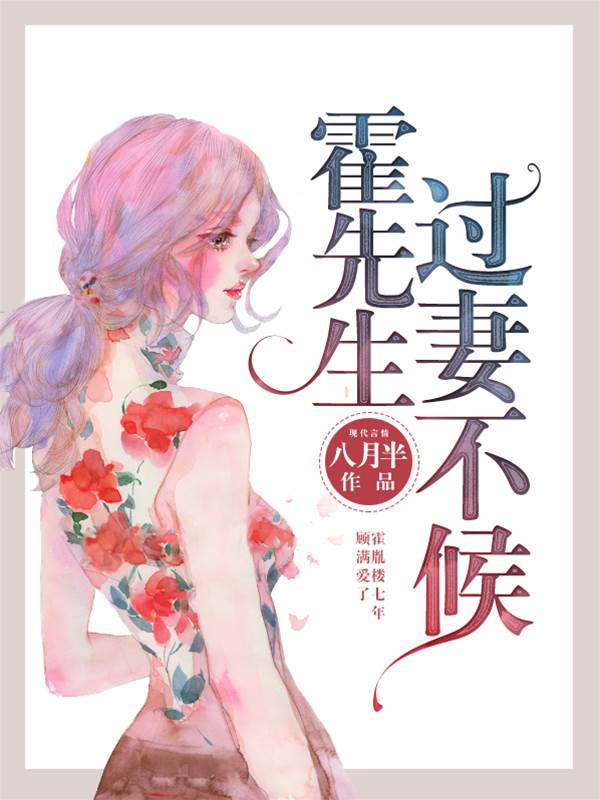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8451 -
完結100 章

不原諒!二嫁豪門后,渣前夫哭紅了眼
顧文林有了私生子,那個一向那方面不行的男人,最終帶著自己的私生子,站在了她的面前。他說:“我的就是你的,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接他回來,我只是通知你,不是和你商量。” 她心里冷笑,轉身計謀離婚。 離婚后,她星光璀璨,耀眼奪目。 再婚當天,渣前夫跪在她面前,大聲哭泣。 “清清,你回來好不好?我一定對你好。” 葉總站在她身側,嘴角揚起一抹笑意,“她不需要。”
17.3萬字8 3909 -
完結403 章

京圈太子爺視我如命,一吻成癮
【看破紅塵高冷太子爺X香香軟軟開朗小太陽】【八歲年齡差+超甜+京圈太子爺+理智淪陷】 京圈太子爺顧黎商禁欲高冷不近女色,手腕上一串黑色佛珠分外惹眼,遺世獨立。 看著身邊兄弟們對花花世界的流連往返,他表示:沒興趣,不理解,但尊重。 直到有天,被逼婚逼急了的顧黎商放話:“我不結婚,我出家。” 顧老爺子想盡辦法讓他開葷,卻次次失敗。 偏偏這次遇上了宋皙,一個被家里趕出來,無依無靠的可憐蟲。 陰差陽錯下,宋皙送酒走錯了包廂,遇上了顧黎商。 顧黎商自詡能坐懷不亂,可這個香香軟軟的女人入了懷,瞬間全身所有的細胞不受控制的叫囂。 “你身上是什麼香味?” “迷魂香? ” 自此以后,顧黎商中了一種叫“宋皙”的毒,極致溫柔,攝魂奪命,再也戒不掉,為了她甘愿落下神壇。 以前別人下班,顧黎商能工作到深夜。 現在別人忙的鍵盤打出火星子,顧黎商提前下班。 “該下班下班該回家回家,我家小妻子離不開我,我先走了。” 到底是誰離不開誰啊! 敢情他們是牛馬,顧黎商反倒成情種了?
73.6萬字8 67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