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裏的花》 第 31 章
第 31 章
……
一個漆黑的深夜,年輕的白人焦急地拍著木板門,裏不停地道:“老板,老板,開開門!我買藥!我攢夠錢了,我是來買藥的!”仔細一看,懷裏還抱著個瘦弱的、眼睛很大卻只能無神地睜著、著氣的孩子。
當胖的中年男老板終于把門口打開時,他看到面前的漂亮孩,發出了一陣得意笑聲:“波德斯涅日尼克(Подснежник)·斯捷潘諾夫,是你呀,怎麽這麽大半夜的送上門來?”
“我有錢了,你看!那個藥,我買,我買!”
“喲!這錢,不是我剛在酒吧時塞到你脯裏的嗎?”男人的笑容越來越得意,“你怎麽能拿我的錢給回我呢?”
“這是我賺的,沃紐奇,不不,沃尼亞尤希·涅普裏亞特先生,你不能這麽不講道理!”年輕的生一邊躲著他過來的茸茸大手,一邊繼續哀求:“我的孩子快不行了,求你,這次不是讓你施舍,我給你錢!”
“嘿嘿,我還是喜歡小波德你聲著我沃紐奇呢!”男人一把抓住的肩膀,另一只手卻向懷裏的孩子。
孩想抓住孩子,卻又怕老男人扯痛他,只好把手松開一點,讓孩子豎著沿著的到地板上自己站穩。
那是一個大概三四歲的孩子了,卻瘦得異常,呼吸急促而紊。眼圈發著紅,白得毫無。
老男人說著“這就對了嘛”,向孩出了他胖得流油的手掌。
孩閉上眼睛側開頭,一邊催促著:“快一點!我的孩子很難了……”
男人一邊滿不在乎地說著“那就讓他死吧”,一邊發出了被稍微滿足、而求更滿足的、像是野低吼一般的聲音。
Advertisement
“……不!”
隨著白人的一聲微弱的的尖,畫面變了:那座黑乎乎的、發臭的山,靠著另外半邊沒打開的木頭門,緩緩地下去,又轟隆一聲倒向一側。
肚子上一個黑乎乎的、發臭的裏,咕嚕咕嚕地往外冒著黑乎乎的、發臭的。
白人的呼吸聲,和那瘦得滲人的孩子一樣,沉重而紊。而他們的手——四只手,都地握著一條細鐵——那是藥店老板放在門邊的,用來勾住卷簾門開合的鐵,兩端都磨得尖尖的。
那個孩子大得讓人不安的眼睛轉向他的媽媽:“我殺了……他?”
“不、不!是我做的,你什麽都沒做!”慌張地松開了握著的兩手。
的手上一片粘糊糊,而小男孩的兩只細弱小手卻白淨如初。此刻,小男孩的手指也一一地從細鐵上離開,像潔白的花瓣,片片綻放。
細鐵“鐺”地落到地上。
白人發呆看著自己的孩子,又突然被這聲音驚醒過來似的,沖進店裏憑著記憶翻找到男孩平時要用的藥,又轉沖出門口,一把抱起的孩子,地抱在前,然後大步大步向著深黑的夜幕裏沖進去。
……
原來,我也是被人期待過、被過的。
即使那些,既貧窮又無奈,既黑暗又腥。
不顧我呼喊、轉而去的卡佳,是殘存在基因裏的唐晚星的記憶。
我的孕母,不,我的媽媽,即使知曉我是一個怎樣的小孩,即使在傳基因上與我毫無關系,也願意用盡全力,護我、我。
年突然來了一勇氣,猛地推開了門。
屋裏的燈慘白慘白的。
他們應該是準備吃晚飯,許是男人們都不在家,人們打算湊合著吃點馕和茶,還有碼在盤子上的像方塊一樣的東西,是炸豆腐嗎?不過已經看不出了,盤子被枕在坐在主位的向前撲倒的小的額頭一側,盛滿了頭上流出的紅黑。
那位一個月前還溫地給他夾菜的阿姨,現在倒在了面對門口的那側牆邊,懷裏抱著自己5歲的兒。們的頭部旁邊都有一小片紅黑粘稠,兩人也毫無生機了。
年向前挪著自己的步伐,呆呆地朝們出手……
“你最好別。”一聲短促的威脅。
年慢慢地從右側轉過子,用那只完好的眼睛定定看著後的鬼魅,輕聲問:“為什麽?”
“哈哈哈哈,你雖然不殺們,們卻是因你而死!”吳凡筆直地指著他的鼻子。
“為什麽?”年執著地問。
“為什麽?呵呵,你以為你做的事,與我們做的又有什麽不一樣!”
吳凡再走前一步,手裏的搶頂住了他的腦門:“你與我們,又有什麽不一樣?!”
“……跟我們走吧!”他收起搶。
年呆呆地跟在吳凡後面,如一行走。
他們的車悄悄地出了城,向著西方那一抹殘留的明前進。
夜晚的戈壁灘星點點,卻照不進年麻木的心;越野車在顛簸,他的隨之搖晃,心卻像死水一般平靜;車窗外的風呼嘯而過,卻無法吹散他心頭的霾。他的視線一直停留在遠一片荒山之上。
不一會兒,連最後一微也消失了,前方是一片無盡的黑暗,讓他不到一希。
車在戈壁灘上飛弛了一個多小時,終于停了下來,吳凡一手拽起年前的服把他拖出車,又推搡著年往前走了幾步。
他們來到一個蔽的山口,走進去後還能看見好幾臺越野車藏匿其中,四周是陡峭的巖壁,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將他們與外界隔絕。
不遠,一個莊嚴得像月夜之王的魁梧影步步從黑暗的山中走出,是張恩國。他沉著臉,目在年上打量了一番,當他忽然留意到年手腕上戴著的特殊手串時,他忽然回,扇般巨大的手掌猛地落在吳凡臉上。
“頭兒,你這是!”吳凡被打蒙了,但接著他也馬上意識到問題所在——
就在這時,遠方的天際線突然亮起一束車燈,猶如夜空中最耀眼的明星,接著直升機的轟鳴聲響徹雲霄,打破了夜晚的寧靜。特種部隊的車隊與空中力量迅速集結,將峽谷包圍。
特種部隊一直暗暗追蹤著手串的移軌跡,直到它停在塔沙古道上即將穿越昆侖山的那一段,那裏有個廢棄已久的古老隘口——赫提隘口,穿越它可以直達中亞地區。
行的時刻來臨!
指揮通過擴音向那些亡命之徒發出震撼人心的指令:“立刻釋放人質、棄械投降!”
張恩國目如炬,冷靜地審視著逐漸迫近的特種部隊,他的臉上沒有流出任何恐懼之。他迅速而巧妙地指揮著手下,充分利用峽谷的複雜地形,心布置了一道又一道堅固的防線。
特種部隊指揮握著無線電,聲音激昂地指揮著這支銳的隊伍。隊員們如利劍出鞘,全副武裝,蓄勢待發。地面部隊矯健如獵豹,在峽谷外靈活布陣,準備應對任何突發況。直升機則如同空中霸主,在峽谷上空盤旋,隨時準備進行致命的俯沖支援,展現出無可匹敵的霸氣。
然而,張恩國和他的手下絕非易于對付的敵人。他們如同訓練有素的狼群,在張恩國的準指揮下,展現出了驚人的協同作戰能力。他們巧妙地利用峽谷的每一寸土地,與特種部隊展開了一場驚心魄的較量。每當特種部隊試圖突破防線,他們都會如同鬼魅般出現,手中的武火閃爍,將攻擊者至絕境。
槍聲、炸聲在峽谷中回,火與硝煙織一幅慘烈的畫卷。特種部隊雖然裝備良、訓練有素,但在張恩國和他的手下面前,卻顯得舉步維艱。他們雖然一次次發起猛烈的攻擊,但始終無法撼張恩國心布置的防線。整個峽谷仿佛變了一個巨大的戰場,張的氣氛彌漫在每一個角落,讓人不寒而栗。
在這場殘酷的混戰中,被“劫持”的年孤獨地蜷在一塊碩大的巖石上,脊背佝僂,眼神空地盯著虛無的前方。周圍槍聲、炸聲此起彼伏,但他卻仿佛置于另一個世界,對這些嘈雜聲音充耳不聞。
生我又是為何?
既帶我來,如何不解我?
年緩緩擡頭,向山上方那一線天空,直升機的探照燈猶如來自天堂的聖,穿黑暗傾瀉而下,卻照不進他心的深淵。
而在這喧囂的戰場上,他竟能聽到天空傳來如同來自遠古召喚的縹緲鐘聲,鐺、鐺、鐺……
特種部隊猶如猛虎下山,不斷地向張恩國的防線發起沖擊。他們時而如同獵豹般匍匐潛行,尋找敵人的破綻;時而如雷霆萬鈞,迅猛沖鋒,試圖撕開裂口。
腥與槍聲織在一起,激起了那些亡命之徒更加瘋狂的抵抗。他們肆無忌憚地開火,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來阻撓特種部隊的猛攻。他們的眼中燃燒著對戰鬥的狂熱,對死亡的蔑視,仿佛這場戰就是他們存在的全部意義。
然而,張恩國團夥的人數有限,怎能抵擋我方源源不斷的生力軍呢?勝利的天平開始向我方傾斜。
就在戰鬥愈發激烈之際,張恩國突然作迅速地拽過邊的年,將他擋在自己前,猶如一道人盾牌。
“停手!”他大吼,“不然我殺了他!”
場面瞬間陷了死寂,只有風聲和偶爾響起的槍聲回在空曠的峽谷中。
所有人的目都聚焦在那年上,然而年的眼中卻沒有一波瀾,仿佛置事外,他甚至還扯著角,對著張對峙的特種部隊人員輕笑了一下,笑容平靜而淡然,仿佛他預料到這一刻了。
“張恩國,立刻釋放人質!”特種部隊指揮馬上通過擴音發出嚴厲的警告,聲音在峽谷中回,帶著不容置疑的權威,回響在每個人的耳畔。
而此刻,唐萬裏站在特種部隊的後面,目地盯著那個被張恩國挾持到前面的孩子。孩子的頭發黏糊糊的,淩不堪,形比以前又消瘦了許多,髒兮兮的白襯顯得空。原本白皙的因為強烈的紫外線和營養不良,已經變得又黑又黃,甚至出一病態。他心裏怒不可遏:張恩國!你拐走他就拐走吧,和你那麽多年兄弟,你把我家小曄弄這樣?
張恩國輕蔑一笑,反駁說:“人質?你們太天真了!你們知道他的代號嗎?黑客界的大名鼎鼎的SL!Solar Light,日之華,曄!把名字都擺到臺面上了,自信到本不怕被追蹤!這孩子五年前就在網絡世界混得風生水起,無所不能。你們知道他以前幹過那些大事嗎?數都數不過來!”他開始逐一列舉這位年黑客曾經攻破的各大機構服務。
張恩國一邊說著,又用手臂圈住年的脖子,強迫他擡起頭,正面面對衆人。
唐萬裏仔細一看,更是心如刀絞:年的左眼還包著紗布,但那紗布已經污穢不堪,左邊臉上似乎還殘留著一道淚的痕跡。
他忍不住心中又是一陣大怒:這麽久了,小曄的眼傷怎麽還沒好?那紗布那麽髒,萬一染了怎麽辦?萬一瞎了怎麽辦?聽目擊者說,他臉上還有個大傷疤!
那個曾經皎若明日、纖塵不染的小曄呢?不、不,只要他能回家,就算瞎了,我也會好好照顧他,我一定會好好疼他……
唐萬裏的思緒如同韁的野馬,胡思想著,一顆心早已一團。
年在心中冷笑。張老頭這麽做,不過是拖延時間,為手下贏得息機會,更是為了自己做出決斷,死心塌地跟隨他遠走。
自己負重大罪孽,留在此地只會面臨無盡的審判與懲罰。沒有理解、沒有信任、沒有包容,就算贖完罪,也永遠只被質疑與排斥。自己的法定監護人,唐家將因自己蒙,被輿論推至風口浪尖;而同學們則會驚愕地得知“真相”,以最惡劣的因來推斷所知的果。
猜你喜歡
-
完結114 章

豪門老公破產后
阮顏從二十一歲大學畢業之后就嫁入豪門成功產子,過的是無憂無慮的闊太生活,誰也沒想到二十七歲這年,風云變幻。 她那位被稱為商業金童的總裁老公居然賠的連條褲子都不剩了。 一家三口身無分文被趕出來好不容易租到了房子,阮顏才發現了最大的問題,她看了一眼手里牽著即將入學一年級的小豆丁,懊惱道:“完蛋了,幼小銜接班還沒報!孩子讀一年級怎麼辦?” 尤其是小豆丁連拼音都認不全…… 看文提示:1、女主前期就是靠著美貌生子上位,介意請莫點。 2、本文多會描寫幼小銜接教育課文的事情,比較細水長流,旨在讓大家了解孩子多麼需要家長陪伴。 3、適當狗血,增加戲劇性,大家莫介意。
26.1萬字8 9241 -
完結1747 章
千億總裁寵妻成癮
出現部分章節有空白問題,請大家在搜索框內搜索《千億總裁寵妻上癮》進行觀看~ —————————————————————————————————————————————————————————————————————————————————————————————————————— “老公,快來看,電視上這個男人長得和你一樣帥!”在電視上看見和自己老公一模一樣帥的男人莫宛溪非常驚訝。賀煜城扶額,“你確定他隻是和我像?”“不對,他怎麼和你一個名字?”被惡毒閨蜜算計以為睡了個鴨王,誰知道鴨王卻是江城最大的金主爸爸。天上掉餡餅砸暈了莫宛溪,本來是爹不疼,四處受欺負的小可憐,現在有了靠山,整個江城橫著走。
318萬字8.33 462778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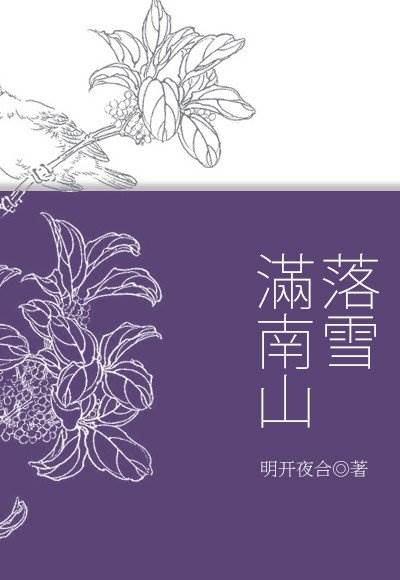
落雪滿南山
[小說圖](非必要) 作品簡介(文案): 清酒映燈火,落雪滿南山。 他用閱歷和時間,寬容她的幼稚和魯莽。 高校副教授。 十歲年齡差。溫暖,無虐。 其他作品:
18.5萬字8 2384 -
完結296 章

心尖蘇美人
當一個女人獲得經濟獨立,事業成就。 男人就只是調劑品,周啟萬萬沒想到,他會栽在她手里,一栽幾年,食髓知味欲罷不能。 蘇簡拉開抽屜,看著里面的九塊九以及一張紙做的結婚證書&”&” 周啟扯著領口,低笑:“這什麼東西?誰放這里的?” 蘇簡默默地把它們拿出來,道:“扔了吧
42萬字8 98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