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瓏雪》 第 115 章
第 115 章
【長汀莊園】
徐錦歌坐在哥哥的車, 凝著莊園的名匾,不贊嘆道,“不知道是那位大家寫的, 中帶剛, 頗有風骨。”
說話的功夫,徐寧徊的車已經進了長汀莊園。今夜這裏有場拍賣會, 他們為一套古董茶盞而來。久遠的朝代、神的花紋、上好的材質,單取一項特質就足以令各地富豪趨之若鶩。
徐寧徊循聲看向妹妹, “聽說是新耀太子爺自己寫的。”
徐錦歌沉迷于周游世界、收集古董, 呆在汀城的時間可以說是極的, 但仍知新耀之名。靠礦業發家,至今已富足了四代。若要說汀城哪家是“old money”, 從來繞不過新耀陳家。
“哥,你見過這新耀太子爺了嗎?帥嗎?”
關注點明顯側重于後半部分, 徐寧徊不笑了聲, “沒有。但即便是帥, 也不適合你。”
徐錦歌下意識地問道, “為什麽?”
徐寧徊:“聽說他不大好,大多數時候都于山清水秀的地方靜養,這長汀莊園就是其中之一。”
“你閑不住的子,能得了這種生活?”
徐錦歌:“確實不了。”
對話就此歇停。
一刻鐘後,徐寧徊將車停在了拍賣會場外。這會場其實就是這長汀莊園的主樓, 一幢雅致的別墅。別墅側邊有天然湖,眼下正值五月,湖面上覆滿蓮葉, 蔥翠滴。
徐錦歌剛下車,注意力就給這片旖旎勾拽住了。對徐寧徊說, “哥,你先進去吧,我在這裏拍幾張圖。”
徐寧徊:“去吧。”
徐錦歌獨自走向了蓮湖,到了近,影影綽綽間仿佛有冰涼水汽拂向的臉。很冰,不微微瑟了一下,但過後,只覺神清氣爽。沉溺于景,沿著蜿蜒回廊越走越遠。
Advertisement
在蓮湖僻靜一角,瞧見了人,是個和差不多年紀的男人。還隔了段距離,樣貌幾何還無法確定。但有一點徐璟歌已然篤定:這男的謫仙掛的,自帶清冷。
徐錦歌沒有擾人雅興的習慣,看到人後,便決定掉頭離開了。哪知才轉,竟聽那男人喚。
“徐錦歌?” 他在詢問,可他真的出了的名字。
徐錦歌轉過來,就這麽不遠不近地睇著他,“你是誰?你怎麽知道我的名字。”
男子微微勾,“我是陳元初,你聽說過嗎?”
徐錦歌:“!!!”
防備心頓時沒了,因為聽過陳元初這個名字,不就是和哥哥方才討論過的新耀太子爺麽?
穿薄霧走向他,也終于看清了他的樣貌。和想的一樣,他的模樣生得好極了,氣度溫潤儒雅。白加黑的裝束簡單至極,卻也沒能削淡這份高貴綺麗半分。
“你是陳元初?長汀莊園的名匾是你寫的?”
陳元初凝著因淡藍禮服越發深邃澄澈的姑娘,眉眼間有笑意氤氳開來,“是。徐小姐覺得那些字怎麽樣?”
他一直坐在躺椅上,并未起迎。他的語態,他臉上的笑,他的......目的一幀幀,讓徐錦歌生出了一種和陳元初是老人的錯覺。他們之間,客套寒暄是可以略去的。不知不覺中,越發的放松。
“我剛進莊園時還同哥哥誇了這幅字,我想想我是怎麽說的?”
徐錦歌故作思忖,十數秒後,“我說‘不知道是哪位大家寫的中帶剛頗有風骨’。”
陳元初:“多謝徐小姐誇贊。”
說這話時,他臉上的笑容還是很淡,但徐錦歌能看出來他的笑意由衷,他在因的誇贊歡喜。
有一瞬,心生迷惘。
可還沒來得及細思,陳元初忽而站起,對說,“要不要嘗試釣魚?”
話落,變戲法似地拿出了一個折疊馬紮,展開,坐定。
徐錦歌忍不住笑:“我都還沒答應呢,你怎麽就忙活開了?”
陳元初:“你會拒絕嗎?”
徐錦歌:“......沒想過。”
徐錦歌從來也不是個矯怯弱的人,永遠清楚自己想要什麽并且勇于爭取。
就像現在,對陳元初心存好奇,在他不反的況,無疑是想探尋更多的。僅僅是猶豫了十數息,便去到了他邊,坐在了躺椅上。
的目一陣梭巡,這才發現陳元初釣魚連只桶都沒有。
“你來多久了?桶都沒一只,釣到了魚你打算裝哪兒?”
陳元初浸于陌生又悉的鮮活中,不由晃神。
從兩個月前開始,他重複地做著同一個夢。
古老王朝的太子,為了來世能遇見自己的妻子,以獻祭,每半月一次。每回過後,他都要虛弱地躺上好些時日。那樣聰穎的一個人,他該是知道神鬼玄妙,他的祈願大幾率不能實現,可他還是做了。
做得極好。
他留著命看著自己的兒為這八荒四海之主,也用天命之人的去溫養一個有的未來。
這個,就是西地首富之,徐錦歌。
陳元初從小著英教育,不信神鬼篤定懦弱者才將希寄托于虛無神佛。可是當他不斷地醒在一攤冷汗之中,當他知道汀城存在著一個徐錦歌的姑娘,他變得不那麽確定了。
夢中的太子,或許真的用“執”撼了天。好奇心促著他去做些什麽,這才有了眼下種種。當那個徐錦歌的姑娘出現在他手可及之,當上的冷香于他鼻前浮沉,他被一種強烈的宿命擊中,控制。
陳元初
徐錦歌
陳元初默念著這兩個名字,鼻間泛出酸意,可他卻在笑。與此同時,無聲地對夢中的“他”說,“恭喜得償所願。”
“唉,你發什麽呆?”
“我剛問你,釣魚不拿桶是什麽作?”
陳元初于姑娘的詢問中回神,既而朝笑笑,“我忘了。”
他藏起了真正的答案。
他坐在這裏本不是為了釣湖中的魚,而是一只人魚。
絕,極富生命力。
而,已經安然地來到了他的邊。
徐錦歌不知他心中所想,聞言即應,“新耀太子爺真神人!”
說話間,還朝著他翹起了大拇指。
陳元初被逗笑,“那不釣魚了,一道去拍賣會瞧瞧吧。”
徐錦歌這才記起自己今晚的目的,“你不說我差點忘了,我的古董茶盞。”
一對璧人相偕步拍賣會場,時不時說上兩句。明明才認識,起來卻是輕松又隨意,仿佛老朋友面。
徐寧徊被旁的兄弟郝鄴拍了下,“唉,錦歌和陳元初認識啊?”
徐寧徊瞥了他一眼:“什麽?”
郝鄴下顎一挑,示意他看不遠。
徐寧徊循著他的指引看了過去,錦歌邊確實有一名男子。
“他就是陳元初?”
郝鄴點頭:“是,兩年前因為我爹的關系見過一面,在私家醫院裏。”
徐寧徊:“他不好?”
郝鄴:“這我就不知道了。這些個大家族的繼承人矜貴著呢,狀況能隨便讓人知道?”
徐寧徊沒再說什麽,他明白,郝鄴說的是真的。
他也沒有任何後續作,不過是一道進來,這都計較,顯得他們徐家小家子氣。
可他沒想到,這個晚上,徐錦歌都沒能回到他的邊。因由他無從得知,但陳元初一直霸著他妹妹是如山的事實。
當下,陳元初和徐錦歌落坐後不久,拍賣師便走到人前,溫婉淺笑宣布拍賣會開始。
不到半個鐘頭,前四的拍品陸續有了主人。在此期間,陳元初一次都未有舉起過手中的出價牌。
徐錦歌好奇地問了句,“釣魚不帶桶,拍賣會來幹坐?”
陳元初:“......”
釣魚不帶桶這茬,是不是過不去了?
徐錦歌將他無奈的表看在眼裏,輕輕笑了聲,“不是幹坐啊?那你看上什麽了?”
“我啊,就喜歡那套名喚蘿的茶盞。”
陳元初一瞬也未有遲疑:“我也是。”
只是這因由同大不同。
是發自心的喜歡。
而他,是因為喜歡。
真心所想,二度藏在了心裏。
那廂徐錦歌想讓他讓讓,結果話都到邊了,又給咬碎吞了回去。他們并沒有多悉,這樣的要求,哪怕是以開玩笑的形式訴諸于口都是不合適的。
又十來分鐘過去了,那套繪了神花紋的蘿茶盞終于顯于衆。
純粹無暇的白瓷,印繪了澤豔滴的花兒,籠于薄中,著一種經過歷史磨礪的態。
深邃,高貴。
只是這時候,包括徐錦歌在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蘿不僅僅是這套茶盞的名字,也是漫漫歷史長河中一個古老強盛的國度的聖花。
它曾經是這世間至至高貴的一抹,也曾與堅韌無畏這樣的字眼羈絆良深。
“底價三千六百萬,每次出價不得低于100萬,且必須是一百萬的整數倍。”
拍賣師不疾不徐地說道,拍賣要求漸漸明晰,也為這項拍賣定了基調。
--這是一場數人的競逐。
“蘿茶盞正式進拍賣流程,請各位出價。”
徐錦歌第一個舉起了報價牌,“三千六百萬。”
想好了,這是第一次舉牌,也是最後一次。深知不是陳元初的對手,同時也覺得這套古董茶盞真的很適合謫仙一般的他。但,仍堅持為自己的喜努力,哪怕這努力在所有人看來都是徒勞無功的。
“三千六百萬一次。”
“三千六百萬兩次。”
在拍賣師即將再度確定最高價時,陳元初舉起了出價牌。
“兩億。”
場仿佛被施了固定咒,沉寂,落針可聞。最先反應過來的是拍賣師,喊出了當前最高價,“兩億一次。”
“兩億二次。”
誠然,場存在著有能力繼續挑高價格的人,但沒人願意以這樣的方式進陳元初的眼。
再則,他這麽砸無疑是在告訴所有人,他對這套古董茶盞勢在必得。他都存這個心了,誰還能贏得了他?
無人舉牌。
古董茶盞在拍賣師第三次確認最高價後,有了新的主人。
徐錦歌笑著對陳元初說,“恭喜。”
陳元初:“承讓。”
拍賣會結束後,徐錦歌回到哥哥邊,和他一道離開。回家路上,徐寧徊問怎麽和陳元初撞上了。
徐錦歌沒有任何瞞地細說了,末了,道,“我覺得陳元初的裏住著一個古人,他做什麽,都有種謙謙公子的味道。”
“他若是去演古偶,肯定火糖。”
徐寧徊失笑,“陳元初演古偶?你就想想吧。”
徐錦歌:“我就想!想想礙著誰了?”
那個晚上,徐錦歌做了個夢。
幽靜雅致的院,有位藍子正在飲茶,面前擺著的手中攏著的,正是今日陳元初拍下的那套蘿茶盞。
一幀幀,皆是清晰。
除了的臉,始終被一團白霧籠著,怎麽也看不清。
忽而,有只人類崽沖進了的懷中。
“娘親。”
藍子趕忙放下了手中的茶盞,不輕不重地敲了崽的頭,“以後可不能再這麽猛沖了,萬一撞落了娘親的茶盞,娘親和你都要被熱茶燙傷了。”
崽乖順道好,隨後又說,“夕夕不想娘親被燙傷,夕夕會保護娘親的。”
藍的子笑了,“娘親也會保護夕夕的。”
喧熱過後,是無限溫。
這時候,崽又對藍子說,“娘親,夕夕長大能做皇帝嗎?小叔叔說夕夕是做帝的好料子。”
藍子怔而輕笑,“夕夕,皇帝是整座江山的主人,看著立于高位無上榮耀,實則不了付出,疲累勞只是這些付出中最不值得被提到的一樣。”
人類崽堅持:“夕夕不怕累。”
“既是這般,夕夕當然是可以做皇帝的。我們子,也能撐起家國。”
崽聽完很是高興,用小腦袋抵著母親胡的蹭著。
正瘋呢,有道溫潤男聲從回廊那頭傳來,“你們娘倆兒說什麽好事呢,不帶我。”
猜你喜歡
-
完結847 章

穿書後,我嬌養了反派攝政王
(章節內容嚴重缺失,請觀看另一本同名書籍)————————————————————————————————————————————————————————————————————————————————————————————————————棠鯉穿書了,穿成了炮灰女配,千金大小姐的身份被人頂替,還被賣給個山裏漢做媳婦,成了三個拖油瓶的後娘!卻不曾想,那山裏漢居然是書里心狠手辣的大反派!而那三個拖油瓶,也是未來的三個狠辣小反派,最終被凌遲處死、五馬分屍,下場一個賽一個凄慘!結局凄慘的三個小反派,此時還是三個小萌娃,三觀還沒歪,三聲「娘親」一下讓棠鯉心軟了。棠鯉想要改變反派們的命運。於是,相夫養娃,做生意掙錢,棠鯉帶着反派們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後來,三個小反派長大了。一個是位高權重當朝首輔,一個是富可敵國的大奸商,一個是威風凜凜的女將軍,三個都護她護得緊!當朝首輔:敢欺負我娘?關進大牢!女將軍:大哥,剁掉簡單點!大奸商:三妹,給你遞刀!某個權傾朝野的攝政王則直接把媳婦摟進懷。「老子媳婦老子護著,小崽子們都靠邊去!」
145.2萬字8.33 120041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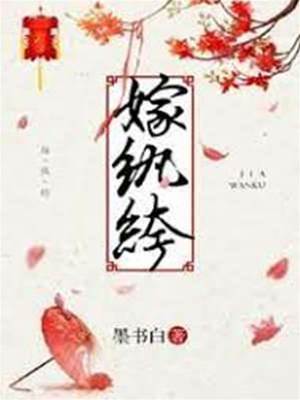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2012 章

戰神王爺是妻奴
一朝穿成被人迫害的相府癡傻四小姐。 從死人堆里爬出來,隨身攜帶醫藥實驗室和武器庫。 對于極品渣渣她不屑的冷哼一聲,迂腐的老古董,宅斗,宮斗算什麼? 任你詭計多端,打上一針還不得乖乖躺平! 絕世神功算什麼?再牛叉還不是一槍倒! 他,功高蓋世,威震天下的戰神王爺。 “嫁給本王,本王罩著你,這天下借你八條腿橫著走。” “你說話要講良心,到底是你罩我,還是我罩你呀?” “愛妃所言極是,求罩本王。” 眾人絕倒,王爺你的臉呢?
362.3萬字8 380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