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籠中雀她渣了瘋批皇帝》 第2卷 第六十八章 我帶你去曬太陽
自鳴時分開始的這場易儲之爭,原本燕王黨占了倒的優勢。他們人把天子從睡夢中拉起來,一陳天生異象,星命轉移;二陳太子羸弱,不復久已;三陳皇長孫胎死腹中,太子后繼無人,乾朝危矣。
還不過一個時辰,太子一黨便敗下陣來。
燕王黨武將居多,如今又在辯論中大獲全勝,氣勢洶洶,幾乎要騎到太子一黨的脖子上好好地捶他們一頓。
他們恨不得直接沖到龍椅上,天子立刻昭告天下,好結束這場沒完沒了的前辯論,趕將許鶴儀攆出去,擁戴燕王主東宮。
不,要是可以的話,他們甚至想直接沖到龍椅上去,把風燭殘年的老皇帝薅下來,直接擁戴許之洐南面稱帝,那才一個痛快!
他們這些武將,在陣前打了多年的仗,自然是一派獷豪放的作風。若是此時有宮人侍婢端上酒來,他們立馬就能舉杯慶賀了。
天子也沒什麼辦法,果然,很快就召燕王后殿議事去。
許之洐正要起前往后殿,見伯嬴匆匆上前,在他邊附耳低語道,“姜姑娘不見了,似乎是被宮里人接走了。”
許之洐目森冷,一言不發,便知事有變。他的母親既已經答應了他放過姜姒,便不會再將暗中帶進宮里。那麼還能命人帶姜姒進宮的,必然只有當今天子了。
須臾,他臉上冷的神兀自斂去。
沒人知道天子與燕王到底在后殿說了些什麼,燕王也遲遲未回到宣室。燕王黨心急如焚,在大殿負手踱著步子。太子一黨的人大多搖頭嘆息,有的覺得易儲已是必然,直接打道回府睡覺去了。
Advertisement
*
許之洐隨天子到地牢的時候,遠遠看著地牢深奄奄一息的姜姒,似一塊被人棄的破布袍子。周遭是遍地的鼠蠅蚊蟲,骯臟又難聞。
這麼悶熱的天,無人看顧,無人給換藥,必是很難熬吧。
那粟的已經上了前去,打開牢門,揪起散的發髻,拿起喂豬的大木勺子便往里灌著什麼東西。
姜姒略一掙扎,那木勺里的湯便傾倒得滿臉都是,虛弱地嗚嗚了幾聲,旋即又沒了什麼聲音。
粟見趴在地上一不,又著人提了一個大木桶來,桶里滿滿的都是冰,聲音不高不低地喝道,“來呀,天兒太熱了,給姜良媛泡個涼水澡。”
這涼水澡是宮里地牢夏日常見的罰手段,將渾是傷的宮人或婢子扔進冰桶里死死按住,他們浸在寒骨髓的涼冰中,往往不到半炷香時間,就不了了。
即便活著出去,這全寒氣侵,也必罪人落下個寒邪毒的病。這寒邪毒怪得很,罪人往往經年腰疼痛,沉重怕冷,便是炎炎烈夏,也需將自己裹得嚴嚴實實,否則風一吹便似鉆進骨髓一樣疼痛。待年歲漸長,連走路都不能夠。
若是在冬日,便搞出個鐵桶刑,鐵桶里盛滿剛燒紅的木炭,把犯人扔至炭上,只需剎那工夫,犯人上那薄薄的一層皮,便被燒灼個。
這時牢里的宮人將姜姒抬起扔進木桶中,最初時黏黏膩膩的子遇到冰,覺得涼涼的很舒適,果真不到半炷香的時間,寒涼的水便順著傷口侵的四肢百骸。
姜姒輕著扭子,企圖離冰桶遠一些,那兩個宮人卻死死地按住了,怪氣道,“急什麼,不過是剛剛進來,按咱們地牢的規矩,得足足泡上兩個時辰呢!必要把這一大桶的冰全都泡得化了水,才你出去。”
姜姒渾發抖,臉青紫。那里需兩個時辰,只怕再有半炷香時間,人便沒了。
凍得連話都說不利索了,“大人......求......求你,放......放我出去......”
那粟尖笑道,“不急,死不了,上頭代了,總會給你留一口氣兒的。”
周遭的冰漸漸消融了水,見要昏迷過去,那粟又著人用方才那大木勺子,盛了滿滿一勺熱水,給當頭澆下。
姜姒一個激靈醒來,又是無窮無盡的寒涼無躲藏。
若再要昏迷,那粟便再當頭澆上一大勺熱水,迫使醒來。
人已經是奄奄一息了。
便是遠遠地看著,亦能到這刺骨的寒冷。許之洐眉間鷙頓生,低聲道,“停手吧,我應了便是。”
天子笑了一聲,“我兒竟是個種。”
說著揚揚下,邊的便趕招呼了一聲,“放人!”
那粟這才示意另幾個宮人將姜姒拖出來扔在地上。許之洐不再去看天子,朝地牢深走來,他朝前走著,解開了腰間的玉帶,下了長袍,聞著這充斥著腐朽骯臟氣息的味道,一步一步地朝姜姒走去。
他朝姜姒走來,就意味著朝權力遠去。
但他依舊朝走來。
周漉漉的,半昏半醒,蜷在地上,瑟瑟打著寒。
必然是極冷的,又必然是極絕的。
許之洐跪坐下來,他將瑟瑟發抖的姜姒抱在他溫熱的懷里,抖開長袍將裹住。曾經說,“我有我的路,殿下不必費心。”
他垂著眸子看,喃喃問道,“這便是你自己選的路嗎?”
這便是你自己選的路嗎?這條路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這便是你自己選的人嗎?他眼看著你死,眼看著用你來換儲君的位子。
你究竟什麼時候才能知道,許鶴儀并非你的良人。
這時候姜姒的意識是清醒的,抓住許之洐的胳臂,努力再靠近一些,企圖從他上獲得更多的溫暖。他的膛是堅毅寬厚的,他的臂膀亦是堅實有力的,蜷在他的懷里,便顯得越發小瘦弱。
姜姒費力睜開眸子去看眼前的人,的眼神虛乏迷離,似有千斤之重,迫得睜不開眼。但仍然看得清許之洐那雙悉的、細長的眸,正一不地、憐惜地看著。
他上的杜衡香,在這腐臭溽熱的地牢里,令心安。
似是每一次最危急的關頭,他都在。他在,便能安然無事,朦朦朧朧中姜姒這樣想著。縱是有過鞭打折辱,他也不過是奚弄,他從來不想讓死。
覺得周是克制不住的寒,忍不住將他抱得更一些,的聲音喑啞低微,“殿下,我好冷。”
許之洐不知道的是誰。
的是許鶴儀吧,的心里從來都只有許鶴儀。
許之洐抱起,的子輕盈得仿佛只剩了一骨架,他說,“我帶你出去,帶你去曬太。”
猜你喜歡
-
完結310 章

重生有喜:皇後孃娘撩又甜
前世,鄰居家竹馬婚前背叛,花萌看著他另娶長公主家的女兒後,選擇穿著繡了兩年的大紅嫁衣自縊結束生命。可死後靈魂漂浮在這世間二十年,她才知道,竹馬悔婚皆因他偶然聽說,聖上無子,欲過繼長公主之子為嗣子。......再次睜眼,花萌回到了被退婚的那一天。自縊?不存在的!聽聞聖上要選秀,而手握可解百毒靈泉,又有祖傳好孕體質的花萌:進宮!必須進宮!生兒子,一定要改變聖上無子命運,敲碎渣男賤女的白日夢!靖安帝:生個兒子,升次位份幾年後......已生四個兒子的花皇後:皇上,臣妾又有喜了覺得臭兒子已經夠多且無位可給皇後升的靖安帝心下一顫,語氣寵溺:朕覺得,皇後該生公主了
69.4萬字8.18 60887 -
完結436 章

秀色可餐:夫君請笑納
一窮二白冇有田,帶著空間好掙錢;膚白貌美,細腰長腿的胡蔓一朝穿越竟然變成醜陋呆傻小農女。替姐嫁給大齡獵戶,缺衣少糧吃不飽,剩下都是病弱老,還好夫君條順顏高體格好,還有空間做法寶。言而總之,這就是一個現代藥理專業大學生,穿越成醜女發家致富,成為人生贏家的故事。
98.4萬字8 16809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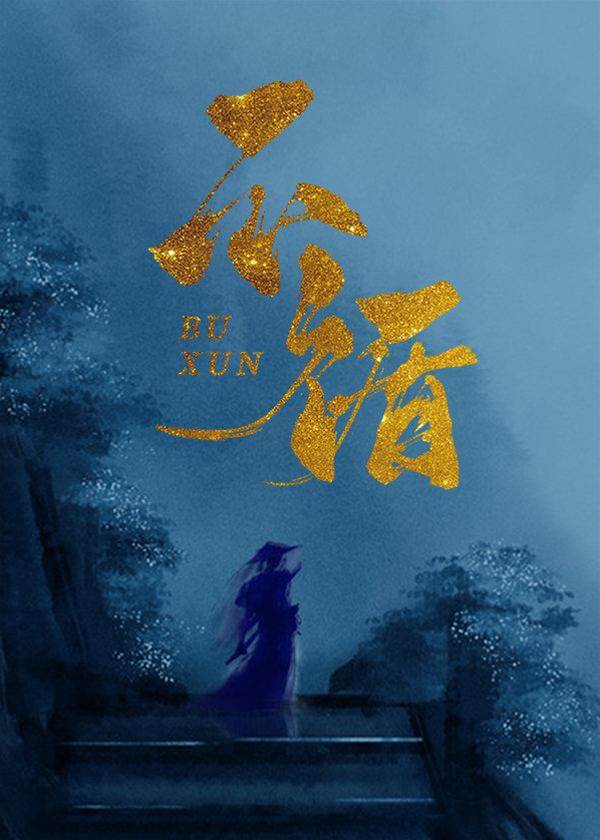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50004 -
完結194 章

曾聽舊時雨
鎮北大將軍的幺女岑聽南,是上京城各色花枝中最明豔嬌縱那株。 以至於那位傳聞中冷情冷麪的左相大人求娶上門時,並未有人覺得不妥。 所有人都認定他們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的一雙。 可岑聽南聽了卻笑,脆生生道:“世人都道他狠戾冷漠,不敢惹他。我卻只見得到他古板無趣,我纔不嫁。” 誰料後來父兄遭人陷害戰死沙場,她就這樣死在自己十八歲生辰前夕的流放路上。 再睜眼,岑聽南重回十六歲那年。 爲救滿門,她只能重新叩響左相高門。 去賭他真的爲她而來。 可過門後岑聽南才發現,什麼古板無趣,這人裝得這樣好! 她偏要撕下他的外殼,看看裏頭究竟什麼樣。 “我要再用一碗冰酥酪!現在就要!” “不可。”他拉長嗓,視線在戒尺與她身上逡巡,“手心癢了就直說。” “那我可以去外頭玩嗎?” “不可。”他散漫又玩味,“乖乖在府中等我下朝。” - 顧硯時從沒想過,那個嬌縱與豔絕之名同樣響徹上京的將軍幺女,會真的成爲他的妻子。 昔日求娶是爲分化兵權,如今各取所需,更是從未想過假戲真做。 迎娶她之前的顧硯時:平亂、百姓與民生。 迎娶她之後的顧硯時:教她、罰她……獎勵她。 他那明豔的小姑娘,勾着他的脖頸遞上戒尺向他討饒:“左相大人,我錯了,不如——你罰我?” 他握着戒尺嗤笑:“罰你?還是在獎勵你?” #如今父兄平安,天下安定。 她愛的人日日同她江南聽雨,再沒有比這更滿意的一生了。
29.9萬字8 1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