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馴服》 第192章 穆歡你是,幫著溫柔?
會開心嗎?
溫陷了沉思,一直以來都沒有和江游說過這兩個孩子是他的,其實有的時候,真相并不重要,就算說了又能怎麼樣呢。
他們之間早就回不去了。
溫流察覺到了溫的猶豫,一邊開車一邊哼著小曲說,“你和江游現在已經不可能復合了,要不也算了吧,江游知道了,反而還多一樁心事放不下。”
溫流說得有道理,溫垂下眼睛,輕聲喃喃著,“但我總覺得現在的江游和過去變得有些不一樣了。”
溫流多看了溫一眼,“怎麼了?”
“他好像在背著我們做些什麼。”溫知道自己過去和江游有許多糾葛,但因為記憶損所以細節記不太清楚,只能靠本能來把江游劃分到壞人那一欄里面去,“我怕他以后會做出對孩子們有害的事。”
“那你相信我。”
溫流笑著踩了一腳油門,“江游就算再不是個東西,也不會對孩子下手的。”
溫嘆了口氣,“但愿吧,等到這里一切結束,我還是想去國外一個人把孩子養大,然后再也不回來了。”
“為什麼?”
“因為這里的人和事,都帶給我太多影,我不想孩子長在一個充滿罪惡的地方。”
溫想起了溫凜和溫瀲的小臉,他們是最后的希,是深陷泥濘時候努力托起的,還沒被玷污的花。
不知道為什麼,腦海里掠過溫凜和溫瀲以后,最后竟然轉變了江游的臉。
現在的江游和以前太不一樣了,過去他意氣風發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是那種可以隨時隨地去害任何一個人的渣男,就如同全世界都不過是他手里的玩,他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時候,不會考慮任何一個他的人的。
現在呢。
Advertisement
現在的江游沒了過去那些出挑的意氣,卻變得愈發銳利和深沉。
他的眼神很空卻又很滿,裝了太多溫看不懂的東西,暗的,罪惡的,就好像是在某個瞬間,江游已經徹底死去了。
而現在的他,拖著一口氣,不過是在完什麼還沒完的東西。
“江游會死。”
忽然間,溫喃喃著說了這麼一句話。
嚇得溫流開車路上一下子踩住了剎車,年輕狂的他也難得一見地變了表,“你為什麼會這麼說?”
“我不知道,我只是就這麼覺得,冥冥之中,他給我這樣一種錯覺。”
溫坐在那里,著車窗外迅速掠過的風景,就仿佛眼前也走馬燈似的過了一遍和江游手的每個瞬間。
回憶完這一遍,你就要消失了。
“他好像在緩慢地燃燒然后死去。”
溫將目收回,而后靠在椅子上,緩緩閉上眼睛,“現在的江游給我一種這樣的覺。就是——他終究在某個特定的時刻會死去的覺。你沒有到嗎?”
溫流搖搖頭,“我只是覺得他的攻擊變得更加明顯了,過去江游收著點的,頂多是唉怪氣,刺激刺激人,眼神撐死就是看不起這個那個……現在,就像是帶槍出巡。”
溫流想了想要用什麼詞語來形容現在的江游,他說,“江游是不是想干一票大的然后退居深山啊?問題是他也沒有什麼大事可干啊。”
溫仍舊維持著閉著眼睛的樣子,并沒有睜開。
“哪怕我現在和他已經毫無關系,可是江游上的這些緒我卻依舊能夠察覺出來。”像是在宣讀著什麼神圣的審判似的,平靜無波,卻又帶著深深的,濃重的,無力的宿命。
“或許有朝一日江游這個罪該萬死的人真的咽氣了,全天下都會高興得慶祝起來。而我這個他的宿敵,則會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為他抬棺的人。”
跑車在高架橋上劃過一道弧線,隨后載著分崩離析的意消失不見。
*******
溫走了,曾紅的頭七儀式還在繼續,不人進來吊唁,就好像當初溫江海葬禮上的畫面重現了似的。
人人都戴著假面,假假意地說幾句虛偽客套的話,勸說著讓人節哀,實則不過是出于關系和利益的牽扯才肯出面講這些最沒用的字眼罷了。
在溫離開以后,江震也走了,似乎是一點都不想在自己“妻”的葬禮上多待,還找了個借口說實在是太悲傷了,心里承不住,才過早離場。
在場的賓客紛紛慨江老爺子到底還是個有有義的人。
江震剛走沒多久,門外又出現了一抹年輕的影,有人好奇看了一眼,發現來的是穆歡。
穆歡有些張,手里拿著一束花放在了曾紅的照前,拜了拜以后剛要走,就被江家一個小輩住了。
“我認得你!你不是溫的朋友麼!真惡心,走了一個溫,來一個你!”
穆歡意外,站定以后去看是誰說話,發現是江家的一個遠房小輩,沒記錯的話,江彎彎。
“沒有,過去我和曾紅阿姨也算是認識的,這次離世,我是代表我自己——”
“你過去不就是被陸老爺子包養的大學生麼!你裝什麼清高啊!”
江彎彎最不喜歡穆歡這種自己沒什麼本事,卻往豪門里湊的人了,“沒有陸老爺子,你也配認識我曾紅伯母?我看你今天來獻花不是真的為了吊唁,而是為了拓展人脈,順便蹭一蹭熱度吧!”
其心可誅,這話太傷人了,穆歡老實的子,當即就站著不走了,還皺著眉辯解說,“你怎麼能這樣說我呢?我和陸老爺以前是真心相過的,我從未低他一等過。確實是因為陸老爺我才會被帶進這個圈子認識你們,所以我才更要來吊唁不是嗎?”
當初穆歡也算半個“陸家夫人”,所以才會連帶著認識了曾紅為首的一群豪門貴婦,覺得,就算過去和曾紅有矛盾,如今死者為大,于于理來祭奠一下,都是應該的。
為什麼自己這樣做還要被人指摘呢?
穆歡有些不理解,“你們好喜歡把人想那麼壞啊,是不是你們自己本就壞,所以把別人往齷齪了想。”
穆歡向來直子,雖然看起來文文弱弱的,但是有啥說啥,認真又爽快,這一說,就讓江彎彎有些不樂意了,走上前,“我們壞?是你們這群企圖染指豪門財產的人壞吧!你就是過來個邊蹭個關系,還要我對你有好臉?誰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心疼我伯母離世呢。再說了,你有什麼資格說我壞?年紀輕輕能給陸老爺子當人的人——能好到哪里去啊!”
這話可就直接在了穆歡的痛上!
當初就是不了被人用這樣的眼神打亮,才會選擇離開陸老爺,哪怕后面收到了一些挫折,還是靠自己走出了一條路來。
把陸老爺給的全部都還回去,就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
穆歡堅定地看著江彎彎,“你污蔑我,你該向我道歉。”
江彎彎被穆歡氣笑了,上前還推了一把,“向你道歉?你擺明了幫著溫氣我們來的,別以為我不知道!如今沒了陸老爺給你當靠山,你是后悔了才會再出現吧!”
穆歡是個實心眼兒的,不得江彎彎這樣說自己,當場一張俏的小臉就氣得煞白,對江彎彎說,“果然江家沒一個好人,指不定江游還是你們家里面最像人的那個!”
江彎彎急眼了,沒想到穆歡膽子這麼大,居然敢當面說的不好,立刻就上前抓住了穆歡的領子,結果還沒來得及說話,門外又是一道聲音傳出來,“把手給我放下!”
那聲音冰冷得像是利刃,直接刺了江彎彎的耳,人一愣,下意識就松手了。
這手一松,就瞧見了門口有個帥氣高大的男人走進來,走到了穆歡邊一停,而后對著穆歡說,“我怎麼說?得我陪著進來吧?還死活說要表份心意,你看看人家歡迎你麼?你一個人進來就是挨人奚落笑話的份兒。”
穆歡委屈得眼淚在眼眶里打轉。卻依然咬著,站得筆直。
是好心,又辦傻事了。但問心無愧,隨便旁人如何潑臟水,不是鬧事來的。
倒是江彎彎傻眼了,沒想到突然間冒出來一個陸霽幫著穆歡,怎麼都想不到,這穆歡都跟陸老爺沒關系了,還能有陸家人幫忙站隊。
江彎彎以前就聽說過陸霽這個人,人人都說陸霽人如其名,長得風霽月。
過去就心陸霽,可是現在陸霽一出現,就是幫著一個——自己父親過去包養過的人說話?
江彎彎當場表大變,指著穆歡就說,“不要臉的貨,你不會是丟了老的勾引了小的吧!”
穆歡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聽見了什麼,甚至連陸霽都當場變了表,男人觀察了一下穆歡臉上的神變化細節,不知道為什麼一怒氣直接沖上來,對著江彎彎道,“你tm放干凈點!”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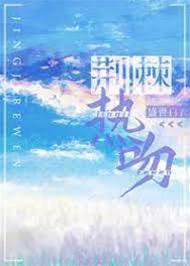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2033 章
盛世婚寵:帝少難自控
她的孩子還未出世便夭折在肚子裏!隻因她愛上的是惹下無數血債的神秘男人!傳聞,這個男人身份成謎,卻擁有滔天權勢,極其危險。傳聞,這個男人嗜他的小妻如命,已是妻奴晚期,無藥可治。他說:夏木希,這輩子你都別想從我身邊逃開!你永遠都是我的!她說:既然你不同意離婚,卻還想要個孩子,那就隨便到外麵找個女人生吧!我不會怪你。五年後她回來,發現那個男人真的那麼做了。麵對他已經五歲的孩子時,她冷冷地笑著:秋黎末,原來這就是你放棄我的原因?那時她不知道,這個男人已丟掉了一隻眼睛……而這個五歲的孩子,竟也滿身是謎!——那是夏與秋的間隔,夏的末端,是秋的開始。秋,撿到了失意孤寂地夏的尾巴。夏,許諾終生為伴,永不分離。經曆了離別與失去,到那時,秋,還能否依舊抓住夏的氣息?
566.6萬字8 14283 -
連載1657 章

雙寶媽咪是大佬顧挽情
五年前,顧挽情慘遭未婚夫和繼妹算計,與陌生男子共度一夜,母親因此自殺,父親嫌她丟人,將她驅逐出家門。五年后,顧挽情帶著龍鳳胎回歸,一手超凡醫術,引得上流社會無數人追捧。某德高望重董事長,“我孫兒年輕有為,帥氣儒雅,和你很相配,希望顧神醫可以帶著一雙兒女下嫁!”追求者1:“顧神醫,我早就仰慕你,傾心你,希望可以給我個機會,給你一雙兒女當后爸,我定視為己出。”
166萬字8 338525 -
完結442 章

把她送進監獄後,慕少追悔莫及
慕南舟的一顆糖,虜獲了薑惜之的愛,後來她才知道,原來一顆糖誰都可以。一場意外,她成了傷害他白月光的兇手,從京都最耀眼的大小姐,成了令人唾棄的勞改犯。五年牢獄,她隻想好好活著,卻背著“勞改犯”的標簽在各色各樣的人中謀得生存。再遇慕南舟,她不敢愛他,除了逃,還是想逃!慕南舟以為他最討厭的人是薑惜之。從小在他屁股後麵跑,喊著“南舟哥哥”,粘著吵著鬧著非他不嫁,有一天見到他會怕成那樣。他見她低微到塵埃,在底層掙紮吃苦,本該恨,卻想要把她藏起來。她幾乎條件反射,麵色驚恐:“放過我,我不會再愛慕南舟了!”慕南舟把她禁錮在懷中,溫柔纏綿的親她:“乖,之之,別怕,叫南舟哥哥,南舟哥哥知道錯了。”
85.7萬字8 63357 -
完結561 章
離婚后孕吐,總裁前夫追瘋了
隱婚三年,他甩來離婚協議書,理由是他的初戀回來了,要給她個交待。許之漾忍痛簽字。他與白月光領證當天,她遭遇車禍,腹中的雙胞胎沒了心跳。從此她換掉一切聯系方式,徹底離開他的世界。后來聽說,霍庭深拋下新婚妻子,滿世界尋找一個叫許之漾的女人。重逢那天,他把她堵到車里,跪著背男德,“漾漾,求你給我一次機會。”
117.1萬字8 257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