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絕色》 第58章
一周後,顧清淮各項指標均已回歸正常,順利出院。
到底是武警特戰出的警,素質常人不能比。
無數次死裏逃生,無數次在鬼門關與死神肩而過,顧清淮被授予公安部一級英模。
而在公安系統,能得到此項榮譽的,大多是烈士。
顧清淮雲淡風輕。
他說他只是做了一個排手應該做的,換了任何人,都會這樣做。
他有很多戰友犧牲在拆彈一線,又或者落下終殘疾,從未退。
他不特殊也不出,足夠幸運罷了。
第一次見行走的公安部一級英模,特警支隊的人都說,顧清淮這次是去閻王殿跟閻王爺握了個手回來。
而特警支隊支隊長念及他從警之後、除母親去世就沒休過假,而且這傷沒徹底好就來市局報到,難免容:“給你一周假,休息一下。”
顧清淮劍眉一挑,那眼神不怎麼厚道,偏偏上的話說得很漂亮:“這怎麼好意思,為人民服務罷了。”
這話說得領導很聽,支隊長覺得自己小看這個姓顧的兵了,瞧瞧人家,覺悟多高,思想多正,一級英模就是一級英模。
下一刻,打臉來得猝不及防。
只見那思想境界頗高的顧清淮拿起請假條,大筆一揮唰唰寫完,一秒沒耽擱地遞到他面前:“既然領導發話,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懇請領導簽字。”
話說得很謙卑、很禮貌,可那表活像是怕他下一秒就不承認,那眼神那語氣不像懇請領導簽個字,倒像是老子這假休定了、你簽也得簽,不簽也得簽。
混小子就是混小子,兵就是兵,那制服到底是不住一反骨!
這個姓顧的混蛋把局長的假髮氣掉都毫不含糊,更何況他一個支隊長!
他接過假條仔細看了眼:“你小子怎麼沒填日期啊?”
Advertisement
顧清淮理直氣壯:“留著以後用。”
支隊長警惕:“你準備幹嘛?”
顧清淮微微一笑:“當婚假。”
支隊長瞪圓眼睛:“定下來了?”
顧清淮這會倒是正經了:“沒,準備求婚。”
得,有朋友就是不一樣。
支隊長痛快地簽好字,把請假條塞回顧清淮懷裏。
正好這會兒有幾個今年新警的小夥子訓練回來,見到偶像齊刷刷杵了一排:“顧隊,炸彈炸的時候,您不怕嗎?”
支隊長冷笑:“他要是怕就奇怪了,排服不穿,直接索降,抱著炸彈往沒人的地方跑,不要命的主兒,你們可千萬別學他!”
顧清淮上警服筆,領帶打得一不苟,領帶夾上著國徽,扣子也扣得相當規矩、到結下方,警下兩條長筆直,賞心悅目。就是站姿鬆鬆垮垮,如果不是那服,說是街上的地流氓也有人信。
到他這個級別,得是地流氓的頭了,這混蛋後腰懶洋洋
靠著辦公桌,笑了下:“我怕。”
支隊長語氣滿是嘲諷:“你怕?”
顧清淮點頭,雖然人還是沒個正形,但態度相當認真。
多次執行任務,他顧清淮都是不要命的那個。
很多時候,大家覺得犧牲或許是他想要的解。
因為母親去世之後,他沒有任何放不下的人和事。
現在,他說他怕。
支隊長可不要太好奇:“你說說聽聽,你怕什麼了?”
炸彈的衝擊波也沒把顧清淮那張漂亮臉蛋搞殘了,而且因為住了一段時間院,皮更白,頭髮澤度很好,角彎彎翹著,更重要的是眼裏有,眼神明亮。
冥冥之中,這個人變得不一樣了。
細究起來,是那雙眼裏的薄霧散了,一派清明。
鐘意手裏抱著相機,來特警支隊找顧清淮。
紀錄片已經拍攝完畢,今日攝製組就要撤離。
大家想要擺個慶功宴,圖個熱鬧。
但一般人說估計不好使,所以派來問一問顧隊長。
推門而的時候,剛好聽見顧清淮說:“怕比早走,會哭。”
沒頭沒尾的一句話。
特警支隊瞬間開始起哄,甚至在看到之後,起哄聲更大。
而那神擋殺神佛擋殺佛的顧隊長難得不好意思。
他紅著耳朵,用那冷冰冰的聲線嚇唬人:“差不多得了,笑什麼笑!”
鐘意茫然,卻又好像約約能猜到他說的是什麼。
心臟酸,等人散去,揪住顧清淮的袖口,想要證實自己的想法:“說什麼呢?”
顧清淮垂下目,眉眼乾淨清俊一如年時,話張口就來:“說喜歡你。”
這樣的顧清淮哪還是特警支隊的顧閻王,他的眼睛彎著,角勾著,說是個調戲小姑娘的浪公子哥還差不多。
如果不是高中就認識他,在他竇初開的就把他騙走了,現在肯定要懷疑,顧清淮這麼會,是不是禍害過無數姑娘、欠過無數桃花債。
心跳瞬間加速,鐘意忘記正事。
顧清淮看臉紅得厲害,手背上的臉頰、給降溫:“找我?”
鐘意更害:“紀錄片今天結束,大家想要聚個餐,讓我過來跟你約一下時……”
只是話音未落,警報響起,特警支隊反恐突擊隊接到新的警——
不明男子在地鐵站留下包裹,說是不答應他提出的條件,他就要炸毀整個地鐵站。
鐘意最後一次將手裏的鏡頭對準他們。
紀錄片結束,這次不能再隨同拍攝。
眼前這無數次發生的一幕,為這次紀錄片畫下完句點——
夜幕下,是閃爍的紅藍警燈,黑的警用劍齒虎,整裝待發的反恐突擊隊隊員。
陳松柏拎起狙擊槍遞給喻行,喻行拉栓上膛驗槍的作教科書級別的標準。
顧清淮扣下頭盔護目鏡,神冷峻不怒而威,排服扔進後備箱,他跟各位隊員簡要通報警。
就在警車開出市局大院的前一秒,一個黑影追著警車狂跑,腳步不停——
從藏藍常服換回黑特警制服的鄒楊氣吁吁地出現,他朝著開走的警車拼命揮舞手臂:“我的調令下來了!我要回來了!等等我啊兄弟姐妹們!”
便見那警車停下,鄒楊一躍而上。
這是紀錄片的結尾,也是他們嶄新的開始。
經此一役,所有人浴火重生。
看著他們離開的鐘意輕輕彎下眼睛。
相信有一天,也可以像他們一樣。
-
當天任務結束,已經是晚上九點,紀錄片的慶功宴沒有延遲,如約而至。
難得放鬆,包廂裏有燈有蛋糕有果盤有開瓶的酒,還有最喜歡的他。
鐘意看他們笑,看他們鬧,聽他們用並不標準的粵語唱《紅日》,唱得上氣不接下氣。
最後,的目落在顧清淮的側臉。
隔著空氣,描摹他的眉眼鼻樑和清晰的下頜線,視線遊走,落在角。
他笑,角彎起的勾好漂亮,型問:“想吻我?”
被一秒看穿心事,鐘意的臉在昏暗線中紅得不明顯,可熱度很高。
顧清淮笑得不算正經:“等回家。”
他的手放在上,手指骨節分明有種玉石的質,掌心朝上紋路乾淨。
鐘意不需他多言,便把自己的手放進他的手裏,掌心相,十指扣。
兩人明正大搞著小作。
鐘意靠在顧清淮的肩窩,間隙吃一口他喂到邊的水果。
顧清淮偏頭,下蹭過的額頭:“高中的時候也想牽你的手。”
那薄薄的漂亮的很會說話,現在吃了好多梨,肯定很甜。
鐘意清亮的眼瞳太清澈,藏不住任何緒,想吻他的衝越發明顯。
切歌的間隙,空氣安靜一瞬。
又調回特警支隊的鄒楊顯然已經開心到變形,也把顧清淮的壞脾氣忘了個乾淨。
他蹬鼻子上臉一把好手,笑嘻嘻跑到顧清淮邊:“隊長,誰不知道你唱歌巨好聽,來一首。”
顧清淮劍眉一挑,隊長的威嚴還在,冰冷的聲線也特別唬人:“當我治不了你了?”
鐘意覺得顧清淮是見過的反差最大的人,不正經的時候像個浪公子哥,冷著臉的時候又是個系天花板,就比如眼下,帥得人。
鄒楊瞬間噤聲乖小鵪鶉,倒是喻行湊熱鬧不嫌事兒大:“隊長,再唱一次《沒那種命》嘛,我們聽過可是鐘導沒聽過呀。”
陳松柏笑得溫和:“就是,我們聽過沒有用,鐘導聽過才有用。”
他們的意思,明白,是想要心疼他,再也不要把他拋下。
“我唱。”鐘意溫聲開口。
眾人不可思議的目,就這樣齊刷刷地落在了自己上。
站起,走向高腳凳的時刻,比颱風天做報導還要張。
顧清淮看向鐘意。
那原本曖昧的迷的燈落到的上,瞬間變得很乾淨很。
視線中心的,坐在高腳凳上,那雙清淩淩的貓眼,其實是有些無措的,像高中的時候。
前奏響起的那一刻,鐘意的心跳比任何時候都要快,睫似乎都有重量。
抬起眼睛,目清澈如水,落在顧清淮上,滿滿都是不自知的溫。
“旁人在淡出,終於只有你共我一起……”
鐘意唱第一句,喻行就聽出來了,這是陳小春的《相依為命》。
生死都走過,在用《相依為命》回應顧隊長的《沒那種命》。
這個容易害、沉默寡言的導演,哪是心來想要唱歌。
的聲線溫溫,粵語發音並不標準,可是咬字近乎虔誠。
是在給的心上人念一封書。
大庭廣眾之下唱歌,鐘意是第一次。
剛開口時甚至還有些輕輕的抖,生無所遁形,手指攥著話筒。
那雙淺眼睛,映著斑斕的燈,燈深,是的顧清淮。
話筒將生的意放大,一字一句輕輕緩緩,羽一樣拂過心尖。
知道,他肯定聽得懂。
“年華像細水沖走幾個人與知己
抬頭命運燈柱罩下來是我跟你
難道有人離去是想顯出好有限
讓我學會為你貪生怕死……”
回憶在腦海,一幀一幀畫面,只要是關於他就無比清晰。
那天他蹲在自己面前,為自己拆下隨時可能炸的炸彈。
執行任務那麼多次,他沒有一次留下言。
唯獨那天,他看著的眼睛,眉眼溫到令人心酸。
——我們見面那天,你問,你穿婚紗好不好看。
——好看,鐘意,非常好看。
“即使邊世事再毫無道理
與你永遠亦連在一起
你不放下我
我不放下你
我想確定每日挽著同樣的手臂……”
他被欺負得不樣子。
他因為生死一線抱著炸彈往沒有人的地方跑。
可當他陷昏迷,他說的是不分手。
他也說,別哭,我帶你去買好吃的。
“不敢早死要來陪住你
我已試夠別離並不很淒……”
那麼殘忍,把自己自殺的傷口給他看。
再一次想要推開他,想要與他永世不見。
他卻紅著眼睛抱住了自己,明明自己眼裏有淚,卻在為淚。
明明遍鱗傷不樣子,卻要帶著一傷痛擁抱
帶刺的。
他說,我那麼寶貝的人,你卻想殺死。
他說,如果哪天,你還有放棄生命的想法,來找我好不好。
他說,你不要你自己了,我要。
目匯在一,顧清淮得償所願,鐘意紅了眼睛。
看著他,彎著流淚的眼睛,輕輕唱完最後一句——
“見盡了雲湧風起,還怎麼捨得放下你……”
顧清淮,我再也不會放開你了。
-
那天的慶功宴到了很晚,這一年的春夏秋冬,仿佛走了一輩子。
寂靜的夜晚,顧清淮陪在的邊,親吻的傷口、的脈搏、的心跳。
那麼溫,那麼繾綣,帶著此生最重的眷,心跳聲震耳聾,滿腔意想要說給他聽。
顧清淮將擁懷中,溫舒適,懷抱治癒,有最喜歡的味道。
鐘意聲音很、耳語大小:“突然想起以前看過一首詩。”
他長睫低垂,眼尾輕彎,全是縱容:“願聞其詳。”
猜你喜歡
-
完結271 章

且以深情共余生
相似的聲音,相似的容貌,遇見了同一個他。兜兜轉轉,走走停停,時光不改蹉跎。如果上天再給她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一定奮不顧身愛的更加用力!
50萬字8 9205 -
完結378 章

玄門回來的假千金又在擺攤算卦了
肖梨在玄門待了一百年,同期進來的那條看門狗小黑,都已經飛升上界,她還只能守著觀門曬太陽。老祖宗顯靈告訴她,“肖梨,你本來自異界,塵緣未了,若想飛升,还得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却凡尘杂事,方可勘破天道!” 回到现代,肖梨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这一世,没有留念,两手空空跟着亲生父母离开肖家。 圈内人都在等着,肖梨在外面扛不住,回来跟肖家跪求收留。 却不想…… 肖梨被真正的豪门认回,成为白家千金,改名白梨。
64.4萬字8 60458 -
完結189 章

荒腔
沈弗崢第一次見鍾彌,在州市粵劇館,戲未開唱,臺下忙成一團,攝影師調角度,叫鍾彌往這邊看。 綠袖粉衫的背景裏,花影重重。 她就那麼眺來一眼。 旁邊有人說:“這是我們老闆的女兒,今兒拍雜誌。” 沈弗崢離開那天,州市下雨。 因爲不想被他輕易忘了,她便胡謅:“你這車牌,是我生日。” 隔茫茫雨霧,他應道:“是嗎,那鍾小姐同我有緣。” 京市再遇,她那天在門店試鞋,見他身邊有人,便放下了貴且不合腳的鞋子。 幾天後,那雙鞋被送到宿舍。 鍾彌帶着鞋去找他。 他問她那天怎麼招呼都不打。 “沈先生有佳人相伴,我怎麼好打擾。” 沈弗崢點一支菸,目光盯她,脣邊染上一點笑:“沒,佳人生氣呢。” 後來他開的車,車牌真是她生日。
28.8萬字8 17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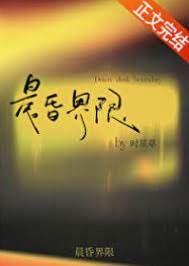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