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她》 第125章(1)
第125章 (1)
正好臨近中秋,花初開的時候,金陵城時興辦宴,雲綺做東,找了個有名的圃裏宴請親友,也請芳兒來賞花喝茶,請帖送到芳兒手中,嗤笑了一聲,將帖子拋出窗外,砸進湖裏。
宴席那日,芳兒突然改了心意,滿戴,珠寶寶氣赴宴。
幾人見面時,芳兒高傲拗著下,目冷冷看著甜釀和施連。
人上都帶著一氣,得意者明朗又耀目,失意人落寞又怯弱,拮據者窮酸鄙吝,如今他眉眼冷,姿疲倦又消沉,顯然是不如意的時候。
今日得了尊貴,見施連消沉,自然要趾高氣揚,一洗前恥,知道這宴請的目的,是對有所求。雖然心底真恨不得將施連千刀萬剮,當然也要萬般辱他。
“都說痛打落水狗,大哥哥如今四平八穩坐著,倒是一點也不著急。”
白眼看他:“不若你跪在地上,先對我磕十個響頭?我替你在大人面前言幾句,將那什麽勞什子案子放一放。”
施連低頭轉著酒杯,抿著薄不說話。
“還是大哥哥清貴,先學個唾面自幹,求個饒?”
雲綺先忍不住竄起來:“芳兒妹妹,大哥哥雖有對不住的你的地方,但你在施家呆了許多年,都是靠大哥哥供養,如今大哥哥有難,你不幫幫他,反倒在這冷嘲熱諷,未免也了點良心。”
“良心,你知道什麽是良心,你知道他對我做了什麽?”芳兒橫眉冷對,目如寒冰,“家裏數你最蠢,你什麽都不知道!”
甜釀只是覺得有些疲倦,疲倦于自己爭吵,也疲倦于聽旁人爭吵或者辯解,來來回回不過那些,一遍又一遍,沒完沒了的,始終解不得。
Advertisement
施連皺眉,擱下酒杯站起來要走,擡頭對著芳兒出個諷刺的笑:“不過是自己爬床的丫頭,當個小妾也夠得意洋洋沾沾自喜?以為山飛上枝頭就能當凰?”
滿座人都驚了,芳兒面發青,銀牙咬碎,目淬冰,將手邊案幾上的六角銀盞朝他劈頭砸來,失聲尖,“施連,你這種男人,你罪有應得,怎麽不去死!”
那銀盞正砸在他額頭,尖角在面上劃出一條細小痕,裏的殘酒潑了半個肩頭,將暮紫袍洇得斑駁狼狽。
他將線抿直,抖抖自己的袍子,出點冷笑,擡腳往外去。
甜釀和他一道上了馬車,默不作聲幫他去臉上跡,他扭頭看著車外,渾冷凝冰,一副拒人千裏之外的模樣。
“你不許去見張圓,不管是現在,還是以後……”他冷聲發話,“無論我如何,離他遠些。”
“好。”甜釀收回手絹,“知道了。”
甜釀知道他從孫先生手中走了十幾萬兩的現銀,通過湘娘子的關系找過人辦事,連著數日都在天香閣宴飲,因此常留一人在家。
楊夫人看甜釀每日坐著發愣,勸:“不如跟我出門走走,散散心吧。”
“幹娘,我不想出門。”甜釀將那副喜帕繡完,正和小雲拿著熨鬥燙平整,“您想去哪?讓小雲陪著您去。”
“去城外的義莊,祭掃楊家墳塋,來了這些日,也該去拜一拜。”楊夫人攜的手,“小九陪我一道去吧,也不遠,一日即可來回。”
甜釀想了想,因住在這宅子的關系,去一去也無妨,楊夫人見應肯,帶了滿車的香燭紙錢,帶著一起出了城。
那莊子在附近的山裏,只是一個極小的陵園,埋沒在荒草叢中,看得出來,墳碑都沒有風辦,不遠有家農戶,楊夫人每年給這家人十兩銀子,煩他們逢年過年除草上香。
“那時候也不敢大肆修墳建墓,原想著有一日扶柩運回原籍,後來也被耽擱下來。”
其實只有三座碑,一座葬的是父親和兒子,一座是母親和兒,剩下一個小小的土丘是獨葬。是最小的那個孩子。
“這是後來遷過來的墳,所以沒和母親姐姐合葬。大名楊玖,家裏頭喜歡小玖兒,胖乎乎嘟嘟的,抱在手裏沉甸甸,別提有多可。”楊夫人回憶起來,笑意滿滿,“我那時候也才十幾歲,被主母挑去伺候,專陪著這些哥兒姐兒跑跑跳跳。”
“怪不得。”甜釀微笑,“怪不得幹娘在錢塘邊見我,聽說我九娘,神有些異樣。”
“幹娘那時候認錯人了吧?是把把我錯認這個玖兒了嗎?”
“是啊。”楊夫人慨,拍拍的手,“玖兒,小九,我差點以為小玖兒起死回生,重活于世了。”
“我們兩個生得像嗎?”
“像。”楊夫人聲音很縹緲,“那時候還是個小嬰兒,兩個小酒窩,笑起來很甜呢,一笑的時候,覺得特別甜,眼睛都亮了,滿家的人都看著笑。”
“玖兒,我有些累了。”楊夫人撚香給,“你既然來,不如替我給亡者上一炷香吧。”
楊夫人在一旁站著,甜釀給每一個墓碑奉香,燒紙、獻牲,走到最小的那座墳堆,看見石碑上刻的字。
楊玖兒。生辰在六月二十八,四歲病亡。
回頭,見楊夫人掩面拭淚,哀容怏怏,跪下去給墓碑磕了個頭。
心頭突然沉甸甸的,像著一塊大石頭,得不過氣來。
回到家中,已是薄暮,楊夫人在車上悄然灑淚,被婢扶著去屋裏歇息,甜釀沐浴更,披著頭漉漉的發坐在屋裏。
家裏很安靜,他不在家中的時候,就格外的靜,他在家中,就常有人登門拜訪,有喧鬧笑語。
“公子還在天香閣麽?”人去找,“去把他喊回家來。”
饒是找人去喊,施連回來時也已近深夜,上都是酒氣,面潤白,兩頰嫣紅,一雙眼黑的漆黑,白的雪白,顯然是喝得不。
他腳步淩,了外裳一頭倒在床上,連聲喚茶。
甜釀端茶過去,他就著的手喝了一盞,聞見寢裏的香氣,將胳膊猛地一拽,跌在他膛上,看見他一雙微紅的眼和蹙的眉,了,被他仰面擡起上,一口咬住的,推倒在床上。
興許是因為醉酒的關系,興許是心郁結,他格外的,床帳的胡鬧直至曙初升才停歇,勉強有力氣開口說話:“昨日我陪幹娘去祭掃楊家墳墓。”
“嗯?誰家?”他嗓音也喑啞,是連日縱酒的後果。
“就是這屋子的舊主人。”甜釀擡頭看他,眉頭糾結,一副疲倦的模樣,“一家六口人,都葬在一起。”
“闔家團聚,也沒什麽不好,總比死者怨,生者哭,相隔的好。”他淡聲道。
“是麽。”甜釀著床帳喃喃自語,眨了眨酸的眼,也閉目睡去。
醫又到施家來問診,那個方子吃了兩個多月,是大補之藥,有些效用,只是藥溫熱,若一旦有孕,即刻停服。
老醫診過脈,皺了皺眉,撚須搖搖頭,斟酌著要增減幾味溫補大藥:“我試著再加幾味藥進去,夫人照常服用,看看效果如何。”
這日施連恰好也在邊,老醫顧及眷臉面,在醫屏後問他:“公子和夫人親幾載?”
施連明白醫的意思,回應道:“這兩年裏每日共寢,一直未有消息。”
“夫人向來如何?可還康健?”
甜釀沒有生過什麽大病,子骨一向還不錯,醫最後問:“夫人此前小産,那時如何吃藥調理的?可有當時開的方子?就怕是那時用錯藥,落下病……”
施連猛然劍眉下:“這兩年裏,未有小産之癥……”
“這倒是古怪。”醫嘀咕,“夫人脈象,滯外散,應是……”
幾年分離,有些問題,施連回答不上來。
醫又替甜釀診脈,問起甜釀這幾年每月月事,飲食寒暖:“從何時起,夫人開始月事不調,腹痛畏寒?”
“夫人那時是不是曾有過崩之癥?傷了本?”
“我……”甜釀在屏風後,,偏偏說不出話來。
“去喊小雲過來。”施連背手站在邊,扭頭喚人,語氣出奇的急迫。
小雲記得的,九娘子跟們初遇之時,有過長長短短幾日的腹痛,在金陵往吳江去的路上,浸了裳,連走都不方便,自那時候開始,每月癸水,九娘子痛得越來越厲害。
那時候們幾人年齡都很小,全然不懂這些,甜釀心裏張,以為自己是癸水,也沒放在心上。
醫收回了手:“這就是了,怕是這時的病,夫人那時是遇過什麽事,還是吃喝了什麽不幹淨的東西?”
上綿綿的,張了張口,想要說話,卻發不出聲音,最後聲道:“我喝過一口帶著雷公藤的酒……”
那杯毒酒,是哺喂給他的,也淺淺啜了一口。
那時候的腹痛,以為是雷公藤的緣故。
“那不是月事……應是夫人肚裏已落了胎,吃了雷公藤酒,將那胎兒打了下來。”醫嘆了口氣,“可能那胎沒有流幹淨,後來沒有好好調養,太過勞,落下了病,故有畏寒、腹痛的病。”
屋裏只有醫緩聲說話的聲音,大腦一片空白,施連站在邊,連角都是凝固的,一不,一雙眼裏滿是戾。
“因著這舊疾,才一直沒有孕事。”醫收回手枕,“倒是要好好調理才行。”
那時候苗兒生了寧寧,他便斷了避子丸。
原來那時已經……有孕。
因著那口雷公藤的酒和出逃……也斷送了腹中的胎兒……
世事無常,因果報應,不知是該哭該笑。
施連大步邁出去,送老醫出門,回來時進屋,卻又生生頓住腳步,他雙目接近漲紅,頜線繃得幾要斷弦,轉去耳房,寒聲讓人奉茶。
片刻之後,耳房裏哐當一聲,是瓷盞狠狠砸地的聲音,而後是噼裏嘩啦的聲響,伴著一聲厲喝:“滾!”
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失態。
聽著耳畔的靜,坐在凳上一不,清淚連綿滾落,一滴滴、一串串砸在上。
屋裏的婢都有些惴惴的,小雲有些忐忑:“九娘,公子他把耳房的東西都砸了,出了屋子……”
施連這夜沒有宿在家中,而是留在了天香閣,他在天香閣連宿了三夜,每日只派人回來取銀子用,甜釀派小廝去找他回家,卻被施連趕了回來。
後來他深夜醉醺醺歸來,見在燈下獨坐,慢騰騰解:“怎麽還不睡?”
“我等你。”甜釀起,站在他前替他。
他上有濃郁的酒氣,還有脂的香氣,襟口還落了一枚花娘的口脂。
甜釀頓住手,他低頭,一雙眸子深不可測,突然鉗住的下顎,迫使擡頭,將冰冷的印在臉頰上。
甜釀雙手揪住他的手臂,迎接他暴戾又強的吻。
他在上又啃又咬,吃痛皺眉,齒間沁出珠,他咬著的傷,汩汩的被他反複吸吮腹,那腥甜的氣息,有種嗜的快。
“痛……”真的痛,下頜幾乎要被他碎,全都在戰栗,“求你……”
他終于肯停下來放過,眼裏布,冷如刀。
“你願意嫁給曲池,願意給他生孩子,那我呢?我的那個孩子呢……我的孩子被母親毒死在腹中,我被拋棄……”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終于哭出來,“我那時候不知道自己有孕……”
“如果你不走,如果你不用避子丸下藥,怎麽會有今日的局面。”他咬牙切齒,面龐幾近扭曲,“我當年一心為你,你說不想生,我用避子丸,你說孩子可,我便停了藥,想要娶妻生子,可你是怎麽對我的?”
“我怎麽不恨,你以為我真的不恨?”他眼裏恨意滔天,“我從沒這樣對過一個人,最後我得到了什麽?我得到的都是我求來的,都是你施舍的。”
猜你喜歡
-
完結88 章

疾風吻玫瑰
江南葉家,書香門第,家風嚴謹。 獨女葉柔,溫婉恬靜,克制自律,從沒做過出格的事。19歲那年,葉柔遇上一個與她全然不同的少年——江堯。 他乖張、叛逆、恣意、頑劣,明目張膽地耍壞......眾人皆雲他不可救藥。只有葉柔覺得那是一道強光,不可逼視。她做了個大胆的決定,追求江堯。江堯為拒絕這個乖乖女,曾百般刁難,其中一條是:“想做我女朋友? 一輛頂配的WRC賽車,我明天就要。 ”當晚,葉柔偷偷典當自己的嫁妝,給他換回一輛WRC跑車。
26.2萬字8 31483 -
完結335 章
分手時孕吐,禁欲總裁徹底失控
安漫乖順的跟在江隨身邊三年,任他予取予求,他想當然的認為她是他手里的金絲雀,飛不出掌心。轉眼,他跟謝家千金訂婚的消息轟動全城。她心碎提出分開,他卻不以為然,直言我沒玩膩之前,你給我乖一點!他跟未婚妻恩愛曬的人人稱羨,背地里卻又對她糾纏不止,不給她名正言順的身份,卻又不肯放過她。直到一日,她隱瞞懷孕消息,不告而別。任他滿世界瘋找,再無音訊。再相遇,她已經是私募基金高級合作伙伴,千億家族的唯一繼承人,唯獨不再是他江隨的女人。他再也沒有往日的高傲跟矜持,跪在她跟前哀求“這一次,求你別再丟下我……”
64.1萬字8 12300 -
完結495 章

閃婚后,顧夫人她卷錢跑路了
初次見到姜思顏,顧寒川誤以為她是自己的相親對象。于是他直奔主題: “第一,結婚后我們分房睡。” “第二,每個月給你三萬塊的生活費。” “第三,在外面不準打著我的旗號胡作非為。” 姜思顏眉頭輕挑,“第一,性功能障礙就不要耽誤別人的性福。” “第二,每個月三萬塊著實是多了點,你可以留下二百五自己花。” “第三,我想問問,你誰啊?” 坐過來就逼逼叨叨的來了個一二三,神馬玩意? 看著罵罵咧咧離開的女人,顧寒川笑了…… 后來,兩家聯姻的消息一出,頓時轟動整個京都。 畢竟這倆人都不是省油的燈。 一個是臭名遠揚的千金大小姐。 一個是手腕狠辣的豪門大佬。 這二人結合,還能給他人留活路麼? 夜晚,路邊停下一輛紅色的超跑,一輛黑色的大G。 從黑色大G中走下來的姜思顏,稍有嫌棄的看了眼紅色超跑內的男人。 “確定非我不可?” 顧寒川語氣寵溺的道,“錢都砸出去了,難道你想讓我人財兩空?” 姜思顏微微一笑,“那你可別后悔!”
83.8萬字8 5892 -
完結233 章

和我媽敵蜜兒子的地下情
【娛樂圈+京圈豪門+港圈豪門】天才鋼琴作曲家x物理科研人才 【簡介1】 談愿聽聞,隔壁的那棟別墅搬來一戶新鄰居 這家人來自港城,說著一口港普,女主人穿得花枝招展,脖子和手指上碩大的珠寶快閃瞎裴女士的眼 暴發戶?這是談愿的第一印象 后來,他房間的窗戶斜對的隔壁亮起了燈 學習時、打游戲時、躺在床上時,總能聽見悠長動聽的鋼琴聲,是他沒聽過的曲調 他從窗戶窺探對面紗簾下女孩彈琴的背影 乖巧,這是談愿的第二印象 再后來,他撞見女孩和一個同齡男生的爭執 兩人說著港語,他不大聽得懂,女孩的聲音里的無情拒絕卻讓他覺得動聽 叛逆,這是談愿的第三印象 最后,這姑娘在談愿心里的印象越來越多 似是要將他的心填滿 談愿不想承認、又不敢承認 在他終心直面內心時 這姑娘,就這麼消失了 獨留他惦記這麼多年 【簡介2】 整個京圈都知道裴婉女士和何昭昭女士不合 京圈貴婦與港圈名媛互相瞧不上 連帶著談愿和阮昱茗都不準有接觸 裴女士嫌棄何女士的“壕”放 何女士看不慣裴女士的“端莊” 裴女士不喜歡阮昱茗的花邊新聞 何女士瞧不上談愿是理工直男 直到阮昱茗和談愿的地下情曝光后 兩人驚訝:“您倆什麼時候變閨蜜了”
44萬字8 111 -
完結12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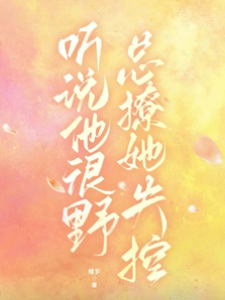
聽說他很野,總撩她失控
【真心機假天真乖軟妹VS假浪子真京圈情種】【雙潔+甜寵蘇撩+暗戀成真+雙向救贖+破鏡重圓+復仇he】 多年前,姜家被迫陷入一場爆炸案中,姜知漾在廢棄的小屋被帶回周家。 這棟別墅里住著一個大少爺,很白很高、帥得沒邊也拽得沒邊。 他叫周遲煜。 第一次見他,他的眼神冷淡薄涼,那時的她十三歲,卻在情竇初開的年紀對他一見鐘情。 第二次見他,她看見他和一個漂亮性感的女生出入酒吧,她自卑地低下頭。 第三次見他,她叫了他一聲哥哥。 少年很冷淡,甚至記不住她名字。 “誰愿養著就帶走,別塞個煩人的妹妹在我身邊。” —— 高考后,姜知漾和周遲煜玩了一場失蹤。 少年卻瘋了一樣滿世界找她,他在這場騙局游戲里動了心,卻發現女孩從未說過一句喜歡。 “姜知漾,你對我動過真心嗎?” 她不語,少年毫無底氣埋在她頸窩里,哭了。 “利用、欺騙、玩弄老子都認了,能不能愛我一點……” —— 他并不知道,十年里從未點開過的郵箱里,曾有一封名為“小羊”的來信。 上邊寫著:周遲煜,我現在就好想嫁給你。 他也不知道,她的喜歡比他早了很多年。 —— 年少時遇見的張揚少年太過驚艷,她才發現,原來光不需要她去追逐,光自會向她奔來。
22.1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