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疾皇叔的掌心綠茶(重生)》 要回來了
沈蕪走出殿,臉上瞬間掛上了溫婉順又楚楚可憐的微笑。
目睹了這一切的大宮:“……”
不得不慨沈姑娘的變臉速度。
沈蕪願意在大宮麵前展自己的真實一麵,是因為大宮在褚靈姝邊待了十年,自打褚靈姝賜號儀寧郡主搬到宮中,便一直是在伺候。
沈蕪的婢都不在邊,能靠的也就隻有這位大宮了。
側過頭,朝知春眨了眨眼。知春一個晃神的功夫,沈蕪便先走了出去。
知春微紅了臉,心道沈姑娘長得是真好看。
沈蕪到前殿的時候,陸之澤已經坐在位置上喝了一杯茶了。
見來,陸之澤眼前一亮,畔漾起笑,迎了過去,“昨日聽聞你進宮,可孤正在外頭辦事,回來時已晚了,便沒來瞧你。今早下了朝便往這來,還好你未出去,沒孤白來。”
沈蕪心道我還不如一大早出去溜達呢。
麵上卻是一副赧的笑,“見不到還有下回呢,臣會在宮裏住上一段時日,總能見到。”
陸之澤抬手想要去握沈蕪的手,笑著轉,手搭上知春的手臂,由著對方把自己扶到位子上坐好。
知春吩咐人給沈蕪也倒了杯茶,還把沈蕪前的披風了,把的袖子往下拉了拉,將手蓋住。
至此,沈蕪除了脖子和臉,無一皮在外頭,詫異地看了知春一眼,卻見知春安地對笑了笑。
知春做完這一切,低下頭,十分守禮又規矩地退到一旁,一句話都不多言。
外人看來,靜熙宮的這位大宮十分張沈蕪的子,照顧得也極為周到細致,夜裏才下過雨,晨間微涼,知春生怕沈蕪冷,這才給裹了個嚴實。
Advertisement
陸之澤心底有一不悅,可他偏偏挑不出什麽錯,沉默了片刻,才笑道:“還是郡主這裏的人心,比你府上的那兩個婢強多了。”
沈蕪微訝,“臣的丫鬟很好,不知們何得罪了太子?”
陸之澤道:“上回你暈倒,可不就是婢不上心的緣故?孤早說過送兩個宮裏的人到你邊伺候,你瞧儀寧這裏的人多心。”
沈蕪擰眉,還未拒絕,陸之澤指了指知春,“此事我會同父皇商議,他撥幾個像這樣的人供你差遣。”
“太子,我邊的人都用習慣了,那兩個丫頭說是伺候我的,其實更像是我的姐妹,你知我家就我一個孩子,沒有兄弟姐妹,阿爹不在,我很是孤單,多虧了們陪著我。況且我覺得們伺候得很好,若是您派了人來,隻怕們心裏會難過,以為我不要們了。”
陸之澤還想再說什麽,沈蕪轉了轉眼珠,又道:“家中還有表姐在,殿下若是隻送人給我而不給表姐,隻怕表姐心裏要委屈呢,殿下還是一視同仁的好。”
沈蕪在心裏冷笑了一聲,別以為他的心思看不出來,太子這是想往將軍府塞人呢。
阿爹治軍嚴明,治家更是容不得一點錯,將軍府如鐵桶一般,太子若想往府上塞眼線,隻能從或者楚輕瑤那裏手,楚輕瑤為了太子自是做什麽都心甘願,楚輕瑤傻,可不傻。
太子想瞞自己和楚輕瑤的私,那麽沈蕪就偏不讓他如願,見針,隻要有機會便會帶上楚輕瑤一句,一邊顯著自己大度,一邊還給足了旁觀人充分的想象空間。
知春垂著頭立在一側,聞言果然微微皺眉。
這沈姑娘與太子的關係似乎並不像是後宮的人傳的那般親,皇後雖屬意沈家做太子妃,但聽沈姑娘的話音,太子似乎同沈家的表姑娘亦有糾葛。
這倒是從未聽說過的事。
陸之澤沒聽出來沈蕪藏在話中的搪塞和深意,他驀地想起來上回,楚輕瑤去試探沈蕪和陵王的關係那次,說沈蕪似乎並不介意他們來往。
太子沒有多想,隻覺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二人若是能一起嫁進東宮,和平共,他既可以背靠沈家的勢力,又可以在楚輕瑤那裏到澎湃熱烈的崇拜,想想便人興。
他目變得很,“你總是這般通達理,此事再說吧,孤還要問問父皇與沈將軍的意思。”
“我阿爹?”沈蕪一愣。
陸之澤笑容和煦,點頭道:“孤此次來就為告知你,大軍已啟程回京,不日抵京,沈大將軍要回來了。”
沈蕪眼睛頓時亮了,“太好了!”
終於,與阿爹當真許久不見了。
陸之澤如願以償地在沈蕪的眼中見到了喜悅、激、以及依賴之,心滿意足地提出了告辭。
能見到沈蕪的笑臉,便不枉費他得知了這個消息後第一時間就往這邊趕。
沈琮誌回來了,那麽他們的婚事可否提上來商討一二了呢?
太子走了。
沈蕪興地了火盆,險些把盆踢翻。在宮們驚慌失措的喊聲中,興衝衝地奔回了殿,借用了褚靈姝的書房,一邊哼著聽不出曲調的歌,一邊提筆開始寫接下來的計劃。
……
太子從靜熙宮出來後,便直奔思政殿而去。甫一踏進宮殿,便聽到了他父皇笑嗬嗬的聲音:
“阿昭昨夜可休息好了?聽聞有個宮人不懂事,又吵著你休息了?”
“你也是的,怎麽能將人都趕走了?若是伺候的人不合心意就對朕講,朕砍了他們,但你那不能缺人照顧,要不將你府上的人進宮裏來?
陸之澤腳步一頓,聽著父皇討好的語氣,心裏生了抵,眉頭微皺,垂在側的手抓了抓裳。
父皇與他說話時從不會這般溫和、甚至堪稱是“低聲下氣”,他是皇帝,對待任何人不都該是一副高高在上的睥睨姿態嗎?為何對待陵王總是一副順從的樣子?
不就是因為救命之恩。父皇縱容陵王這麽多年,即便是還恩,也夠了吧。
陸之澤想到自己的求助接二連三地被這位小皇叔拒絕,臉就愈發難看,連帶著看向陸無昭的眼神都變得格外鬱。
一個瘸子,一個殘廢,憑什麽比他這個一國太子還要高貴?
一個廢罷了,有什麽傲的資本?
總管太監一眼瞧見了他,忙笑著迎了上去,“太子殿下到了,快進來。”
坐在主位上的男子劍眉星目,五周正,長眉上揚,黑瞳裏泛著溫和的,著一件明黃的龍袍,渾散發著與生俱來的高貴氣質。
見到陸之澤,他刻意收斂的上位者的威儀在不經意間流了出來。
這位便是霖朝第五位君王,嘉宗皇帝,陸培承。
陸培承收了對陵王的那份溫和,轉而有些冷淡和嚴肅地看向自己的兒子,“太子來得遲了。”
帶著十足威嚴的聲音陸之澤打了個冷戰,他忙恭敬行禮,“父皇。”
“恩。”
上位的君王不茍言笑。
陸之澤轉頭對著陵王揖了一禮,“小皇叔。”
陸無昭朝他微微頷首,離得近了,他約在太子上聞到了悉的花香氣與藥味相結合的味道,他隻見過一人能將這二者的味道融合得很好聞。
那個人昨夜還說要他以相許,今日便見了旁人。
他眸微暗,向太子的目有片刻沉凝。
餘瞥見嘉宗皇帝的目又落回到他的上,陸無昭淡淡將打量收回,漫不經心地回答皇帝方才的問題:“不勞皇兄費心,臣弟不需要人伺候。”
嘉宗帝的目和了下來,他言又止地看了看陸無昭的,終是什麽都沒說,點點頭,“好,都隨你。”
關懷完了陸無昭,並未他退下,他這個弟弟想在他這裏多待上一會,他不得。更何況,和太子的對話也沒什麽是陸無昭不能聽的,這個弟弟從小就是由他教導,脾氣秉他最了解,陸無昭聰慧至極,留在這裏,興許還可以幫他教育一下這個不的太子。
陸培承問了太子許多事,有些太子支支吾吾答不上來時,陸培承便往自己的弟弟上瞟,可惜這個弟弟就像是事不關己一般,置若罔聞,連個眼神都沒分給他們。
他懶洋洋地坐在椅上,眉梢眼角都在訴說著“隨意”二字,氣質懶散,對萬事都不上心。
陸培承不滿地看了眼太子,揮了下袖,將書案上幾本無關要的奏折扔給太子,“把這些批完。”
太子習以為常,他時常故意犯蠢,為的就是能看看父皇的這些奏折,即便是些瑣事,卻也是難得的鍛煉機會。
太子伏案而坐,陸培承長出了口鬱氣,又將目轉向了陸無昭。
“對了,不知阿昭可聽說,輔國大將軍班師回朝,正在路上,約莫不出一個月便要抵京了。”
陸無昭無聊地把玩著龍案上懸著的一隻用上好木料製的筆,聞言眼睛都沒抬,“未曾聽說。”
謝卿昀跑回京的消息早就被他瞞了下來,此時的他不應該知道軍中的事。
“朕還以為你們私下有聯絡呢,畢竟你時可是很喜歡跟著沈將軍後頭跑的,若不是……”
“皇兄記錯了,臣弟時沒什麽喜歡的人,與沈將軍不過點頭之,僅相識爾,並不識。”陸無昭平靜道,“何況大將軍在外出征十載,並未回過京城,除了皇兄,怎會與旁人來往過。”
“那是朕記錯了吧,”陸培承爽朗笑笑,“不過阿昭,你比我小了十二歲,記竟是還不如我,大將軍何曾出征十載?明明是六載才對。”
“是嗎?”陸無昭微挑了眉,“那是臣弟記錯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59 章

嫁給奸臣沖喜后
傅瑤要嫁的是個性情陰鷙的病秧子,喜怒無常,手上沾了不知多少人的血。賜婚旨意下來后,不少人幸災樂禍,等著看這京中頗負盛名的人間富貴花落入奸臣之手,被肆意摧折。母親長姐暗自垂淚,寬慰她暫且忍耐,等到謝遲去后,想如何便如何。傅瑤嘴角微翹,低眉順眼地應了聲,好。大婚那日,謝遲興致闌珊地掀開大紅的蓋頭,原本以為會看到張愁云慘淡的臉,結果卻對上一雙滿是笑意的杏眼。鳳冠霞帔的新嫁娘一點也不怕他,抬起柔弱無骨的手,輕輕地扯了扯他的衣袖,軟聲道:“夫君。”眾人道謝遲心狠手辣,把持朝局,有不臣之心,仿佛都忘了他曾...
46.3萬字8 58850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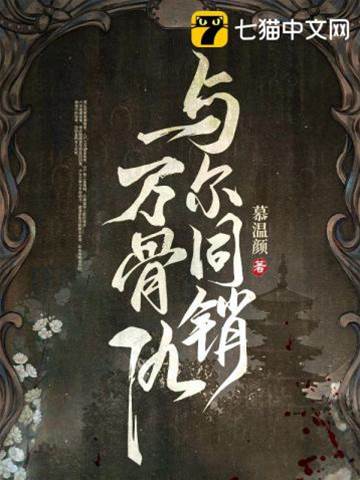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
完結191 章

妾身嬌貴
莊綰一直以為,她會嫁給才華冠蓋京城的勤王與他琴瑟和鳴,為他生兒育女。然,一夕之間,她想嫁的這個男人害她家破人亡,救下她後,又把她送給人當妾。霍時玄,揚州首富之子,惹是生非,長歪了的紈絝,爛泥扶不上牆的阿鬥。初得美妾時,霍時玄把人往院裏一扔讓她自生自滅。後來,情根已深種,偏有人來搶,霍時玄把小美人往懷裏一摟,“送給爺的人,豈有還回去的道理!”
51.9萬字8.18 18298 -
完結347 章

囚她
施家二小姐出嫁一載,以七出之罪被夫家休妻,被婆婆請出家門。 無子;不事舅姑;口舌;妒忌。 娘家一席軟轎把她帶回。 她住回了自己曾經的閨房。 夜裏,她的噩夢又至。 那人大喇喇的端坐在她閨房裏,冷笑睨她。 好妹妹,出嫁一年,連自己娘家都忘了,真是好一個媳婦。 她跪在他身前,眼眶皆紅。 他道:“不是想要活着麼?來求我?” “你只許對我笑,對我體貼,對我賣弄,對我用十分心計,藉由我拿到好處。”
56萬字8.18 32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