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劈腿後,我嫁給了腹黑總裁霍先生》 第52章那我走?
溫景初皺了皺眉,道理確實是這樣,說到顧爺爺,南城誰不豎個大拇指?
顧星遲跟顧清清但凡有一半顧爺爺的風骨,如今的顧家也不至於是這副景了。
在顧家待了這麽些年,自然是知道顧家是什麽虎狼窩的,但霍夫人知不知道,就不清楚了。
想,霍太太這樣的豪門太太自然是不會沉迷在朋友圈吃瓜的,顧清清那點破事大抵也傳不到而耳裏去。
所以心裏莫名有些張。
“嗬!”雕花牆那邊又傳來一聲輕笑,是霍夫人的。
“三嬸!”說:“顧老爺子自然是人人敬服的,可咱們現在說的也不是顧老爺子是吧!”
這話溫景初聽在耳裏,莫名便想笑,不假思索的朝霍喬年看過去,立馬被對方瞪了一眼。
那眼神,仿佛在嗬斥,你腦子呢?都在想些什麽?
溫景初收回目,轉而又想霍太太這話說的很是晦,顧夫人們若是就此打住,大抵還是能保住臉麵的。
可偏偏就是有人不識趣。
是霍喬年他三藍霜,拔高了嗓因噌怪道:“毓秀,你這話說的,清清是顧老爺子的親孫,能遜到哪裏去?”
Advertisement
霍夫人便在那頭“嗬嗬”笑了聲,“三嬸,有些事大家沒拿到臺麵上來說,不代表就沒發生過。”
“我們家呀,雖然對門第要求不高,可人自殘的媳婦跟苛待養的親家,是萬萬不敢要的。”
也沒指名道姓,但說的是誰說的又是什麽事,大家心裏再明白不過。
許是心虛,顧夫人竟也沒辯解。
跟著雕花木牆那邊傳來椅子挪的聲音,像是有人起了來,還是霍太太的聲音,“還要陪行止去做針灸,我先走一步,你們慢用。”
這表現分明是不想跟顧夫人和霍三再待下去了。
顧夫人們大概也是覺得麵上無,並沒有挽留。
幾秒鍾後,應該是霍夫人出了包廂,隔壁便不斷傳來砸東西的聲音跟尖銳的咒罵聲。
一直等到溫景初跟霍喬年吃完飯離開包廂的時候,隔壁顧夫人跟霍三還在罵罵咧咧,什麽,溫景初沒細聽。
想來霍太太畢竟地位擺在那裏,豪門圈的太太們都要給幾分薄麵的,們應該也不敢太過分。
倒是在提到自己的名字的時,顧夫人很是激,但估計是怕隔牆有耳,罵人的話也是挑挑揀揀。
想到那種敢怒不敢言的憋屈樣,溫景初便在心裏暗笑。
霍太太晚上的態度很明確,不會接納顧清清,同時還敲打了顧夫人。
雖然不完全是為了,但是還是心存激。
不知道霍喬年在這件事裏充當了什麽角,不過以他的手段,傳遞幾個消息給霍太太不是難事。
雖然不是他自己出麵,但結果是一樣的。
顧清清婚途不順,為了給顧清清找個好婆家,顧夫人對也應該會收斂一些。遷戶的事雖然還沒著落,但小目標已經達。
溫景初心不錯,自顧抿笑,誰想,男人的聲音便響了起來,“想什麽呢?”
他上雖是風輕雲淡,可那表分明就是,“你在犯什麽花癡?”那種嫌棄。
溫景初心裏高興,便也不跟他計較,歪著頭挑眉,“在想怎麽報答霍總呀!”
霍喬年先是頓了一下,跟著湊到耳邊,“晚上去你那裏?”
溫景初便懵了,就是這麽逗逗他,沒想男人竟然都沒跟客氣一下,今天都好幾回了,這個頻率,誰吃得消?
擰著眉,很是為難道:“今天不行。”
“什麽不行?”男人不假思索的問。
溫景初不知道他是真沒聽懂還是跟裝的,紅著臉說:“你節製些!”
下一秒,男人的嗤笑傳來,“溫老師這是虛了?”
“你才虛了!”溫景初揚起下,打死不承認。
男人便順手著的下,語氣曖昧的不行,“既然不虛,要我節製什麽?”
這是把自己帶裏了,溫景初恨不能回到剛剛咬了舌頭,便沒接話。
偏偏男人不依不饒,咬著的耳垂說:“是誰說隻有累死的牛,沒有犁壞的田的,嗯?”
溫景初真是服了他,猴年馬月的事都能拉出來再刑,還要問討個夠本。
“霍喬年,你討不討厭!”推他。
霍喬年踉蹌了一下,能覺出來,沒用多力,至比上回在停車場裏踹他的時候,收斂了許多。
他說去那裏,其實也沒想要做什麽,知道的狀況,他還沒那麽禽。
可自己偏偏就想去了那裏,卻也不說自己不舒服,還要一副為他著想的模樣。
他便想逗逗,畢竟他是男人,無論是言語還是力行自然不能被一頭。
卻沒想,這便臊了,才配合了這麽一下,否則,怕是還不知道怎麽下來臺。
溫景初可不知道男人是這樣的心思,還一副我暫時不想跟你說話的模樣俯去抱起鬆,“鬆,咱們回家。”
回到公寓樓下,霍喬年跟著下車,溫景初沒拒絕,兩人心照不宣。
到了門口,男人很是主的接過鬆,讓好騰出手去開門。
溫景初也樂的輕鬆,等進了屋,男人還站在門口,似乎在征求的意見。
霍喬年在的印象裏,自來都是強勢霸道的。
哪裏見過他這種時候,當然也是知道他並不是真的在征求的意見,而是在等開口邀請。
溫景初覺得狗男人簡直矯的要命,人都上來了還跟擺譜,就想讓他在門口站著算了。
但也就是想想,不敢真這麽幹,想著與其逞一時之快,回頭他給甩臉子穿小鞋,再費勁哄他,不如討他歡心一勞永逸。
勾起一縷垂落的鬢發掛到耳後,朝他看了眼,“霍總覺得門口的空氣比較好是嗎?”
承認,自己邀請的比較委婉,但意思確實是那個意思。
可男人就好像得了失憶癥,瞥了一眼,“那我走?”
溫景初撇了下,沒好氣說:“要走趕,別耽誤我關門!”
然後,裝模作樣的扶上門把……
猜你喜歡
-
完結70 章

我愛你,我裝的
寧思音的未婚夫是蔣家最有希望繼承家產的曾孫,無奈被一個小嫩模迷了魂,寧死也要取消婚約,讓寧思音成了名媛圈的笑柄。 蔣家老爺子為了彌補,將家里一眾適齡未婚男青年召集起來,供她任意挑選。 寧思音像皇上選妃一樣閱覽一圈,指著老爺子身邊長得最好看最妖孽的那個:“我要他。” 前未婚夫一臉便秘:“……那是我三爺爺。” - 蔣老爺子去世,最玩世不恭的小三爺繼承家業,未婚妻寧思音一躍成為整個蔣家地位最高的女人。 嫁進蔣家后,寧思音的小日子過得很滋潤。住宮殿,坐林肯,每個月的零花錢九位數,還不用伺候塑料假老公,她的生活除了購物就是追星,每天被晚輩們尊稱奶奶。 唯一的不便是,作為蔣家女主人,在外要端莊優雅,時時注意儀態。 忍了幾個月,趁蔣措出差,寧思音戴上口罩帽子偷偷去看墻頭的演唱會。 坐在下面喊得聲嘶力竭:“寶貝我愛你!” 后領子被揪住,本該在外地的蔣措將她拎上車,笑容涼薄:“再說一遍,你愛誰。” *白切黑狡詐小公主VS美強慘陰險大BOSS *我以為我老公歲月靜好沒想到心狠手辣,呵,陰險/我老婆表面上單純無邪背地里鬼計多端,嘖,可愛 *本文又名:《震驚!妙齡少女嫁給前男友的爺爺》《前男友成了我孫子》《豪門奶奶的幸福生活》 【排雷】 *黑心夫妻二人組 *非典型瑪麗蘇,一切設定為劇情服務 *人多記不住的,蔣家家譜見@碳烤八字眉
26.2萬字8 14514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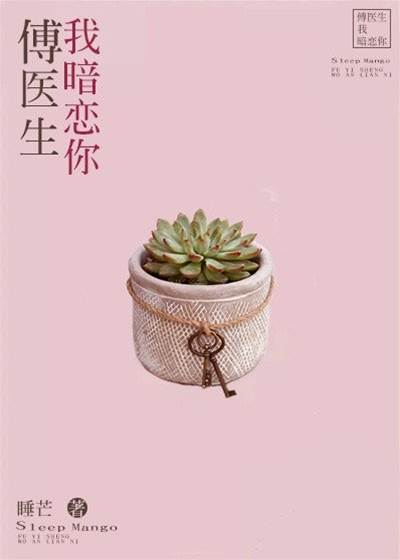
傅醫生我暗戀你
暗戀傅醫生的第十年,林天得知男神是彎的! 彎的!!!! 暗戀成真小甜餅,攻受都是男神,甜度max!!!! 高冷會撩醫生攻x軟萌富三代受 總結來說就是暗戀被發現後攻瘋狂撩受,而受很挫地撩攻還自以為很成功的故事……
44.4萬字8 7391 -
完結561 章
快穿:白月光渣過的男主全瘋了
(已完結)【1v1雙潔+甜寵+女主白月光】【病嬌瘋批+修羅場+全HE】作為世界管理局的優秀員工沐恬恬,本該退休享受時,突然被警告過往的任務世界全部即將崩壞?!那些被她傷過的男主們充滿恨意哀怨的看著她…冷情江少眸色晦暗,“恬恬,既然回來就別再想離開,不然我不知道我會做出什麼…”頂流偶像低聲誘哄,“跟我回家,我照顧你…”這次他絕不能再讓她離開…瘋批竹馬展露手腕劃痕,“如果你再拋下我,下次,我一定死給你看…”精分暴君看到她頸肩紅痕,眼尾殷紅,“你怎麼能讓別人碰你?”沐恬恬,“我沒…唔~”天地良心,她從始至終只有他一個人啊!沐恬恬本以為自己死定了,結果腰廢了。已完成:①冷情江少燥郁難安②頂流偶像醋意大發③邪佞國師權傾朝野④病嬌始祖上癮難戒⑤黑化魔尊囚她入懷⑥天才竹馬學神校霸⑦精分暴君三重囚愛末日尸皇、忠犬影帝、偏執總裁、妖僧狐貍、病態人魚、黑化徒弟、虛擬游戲、腹黑攝政王、殘疾總裁、無上邪尊。有婚后甜蜜番外,有娃,喜歡所有世界he的小伙伴不要錯過~
98.4萬字8 5079 -
完結337 章

南小姐別虐了,沈總已被虐死
沈希衍很早以前,警告過南淺,騙他的下場,就是碎屍萬段。偏偏南淺騙了他,對他好,是裝出來的,說愛他,也是假的。從一開始,南淺的掏心掏肺,不過是一場蓄謀已久的陰謀。她裹著蜜糖的愛,看似情真意切的喜歡,隻是為了毀掉他。當所有真相擺在沈希衍麵前,他是想將她碎屍萬段,可他……無法自拔愛上了她。愛到發瘋,愛到一無所有,他也無怨無悔的,守在她的房門前,求她愛他一次,她卻始終不為所動。直到他家破人亡,直到她要和別人結婚,沈希衍才幡然醒悟,原來不愛他的人,是怎麼都會不愛的。沈希衍收起一切卑微姿態,在南淺結婚當天,淋著大雨,攔下婚車。他像地獄裏爬出來的惡鬼,猩紅著眼睛,死死凝著坐在車裏的南淺。“兩年,我一定會讓你付出代價!”他說到做到,僅僅兩年時間,沈希衍就帶著華爾街新貴的名頭,席卷而來。但,他的歸來,意味著——南淺,死期將至。
69.2萬字8.46 11142 -
完結445 章

離婚後,千億前妻驚豔全球
她把所有的愛情都給了傅西城,可是三年,她也沒能融化了男人的心。“我們離婚吧。”江暮軟一紙離婚證書,消失在了男人的世界。離婚之後,她消失的幹幹淨淨,可是傅西城慌了。追妻漫漫……傅西城發現,原來自己曾經拋棄的女人不僅僅是財閥大佬這麽簡單……
77.6萬字8 2521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