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故人戲》 7.第六章 沉酣戲中人(1)
;
冬天過去,開始上課以後,傅侗文也開始了他在國的社活。
每月能見到他一兩次,偶爾會問到的課業。一問一答,總是他說的多,答的,反倒是顧義仁和婉風和他說的話多些。三月的一個周末,傅侗文留宿在公寓,這天他神出奇地好,在客廳和他們一起喝下午茶,大家討論時事,說實業救國,婉風忽然問到傅侗文常去八大胡同,是否見能讓蔡鍔為之傾倒的小仙?
傅侗文笑笑:「未曾有幸。」他對傳聞中的「肆意用」從未辯解。
他不答,反倒將視線落到上:「怎麼不說話?」
一不留意時政,二際圈小,不像婉風和顧義仁,可以這麼快流到國的消息,實在沒談資,只能端起茶壺:「我去給你們添水。」
等到將茶壺端回來,顧義仁正立起子說:「義仁必當終其一生報效家國。」
突如其來的表忠心,像在告辭。;
果然,傅侗文的回答應證了的推測:「保重子,萬事都要想到,『留得青山在』這個道理。」
顧義仁慷慨激昂:「三爺放心!」 ṡẗö.ċöṁ為您帶來最新的小說進展
沈奚這才覺得燙手,將茶壺砰地放到了桌上,掌心都燙紅了。顧義仁和婉風都笑來,婉風拉住的手,著:「就是怕你捨不得,我們今日才說。」
「你們?」沈奚更是錯愕。
「是我們,」婉風笑了,「我們結伴一道走。」
沈奚憬然,難怪他會回來,要和眾人一敘。
顧義仁對傅侗文的尊敬是打從心底的,臨行前這一夜,喝了個不省人事。傅侗文被他的緒染,飲去數杯,沈奚默默給他滿杯的次數,到第四杯時,傅侗文察覺了,過來。
Advertisement
沈奚立刻別過頭,去看牆壁上掛著的鐘。;
「看什麼呢?」婉風小聲問。
「要送他上樓去嗎?醉這樣,明日如何登船啊?」沈奚耳語。
「你去好嗎?」婉風用的手腕輕輕在的後背上,求饒,「我想和三爺單獨坐一會兒,」話未說完,又將子轉過來,面對著沈奚,「求你了,我明天就走了。」
單獨坐一會兒?
沈奚懂了的意思,孩子之間不用說穿的那層意思。
婉風喜歡上傅侗文了。什麼時候的事?也許遠比認識傅侗文還要早。
「求你了。」婉風聲音極低。
沈奚食指指尖下意識著桌子,到盤子邊沿,冰的。
「我去人來,扶他上去。」沈奚妥協了。
發現,離開這個飯桌的艱難程度遠超的想像,以至於跟著傅侗文的那個年架起顧義仁,要求打一把手時,沈奚還在走神,魂不守舍。;
顧義仁到樓上大吐特吐,暫解了的胡思想。跟著收拾,到乾淨地板,看到床上疊得齊整的白襯衫,還有一條深藍的針織領帶。這應該是他準備歸國的「戎裝」了。而自己呢?還有一年,兩年?還是更久?
顧義仁在床上翻了,裡咕噥著什麼,沈奚湊近聽,在說橋樑土建。
將棉被攤開,蓋在他上:「再見吧,顧兄。」
顧義仁自然聽不到,夢中和周公訴衷腸,表著建造大橋的心愿去了。
沈奚坐在床邊沿,看床上的一塊表,過去一小時了,還沒靜。想下樓怕撞到不該撞見的,可坐在這兒也踏實不下來。兩手撐在後,直腰桿,舒展自己的腰,配合著顧義仁,開始背誦《黃帝經》。雖學西醫,但篤信老祖宗的東西,所以任何中文的醫書也從未放過。「總會有用。」這是常有的論調。
「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肺移寒於腎,為湧水,湧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於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
門被扣響。
沈奚停下,後的男人還在講著他的畢業論文。
開了門,是婉風。
婉風雙目泛紅,在看向時,像有含的一番意思。
「去吧,去三爺那。」低聲說。
去傅侗文那裡?
沈奚錯愕,沒等發問,婉風已經將雙手握住的:「這一別,山高水遠,你要好好照料自己。明知學海無涯,讀不完,慢慢讀。」
「這才三點,道別太早了,」沈奚低聲回,「明早我送你們。」
婉風淡淡笑笑,頷首。
離開,可還覺得有什麼不對。說不清,道不明的。
顧義仁的房間在一樓,出來時,廳堂的燈滅了。
開關在大門邊,懶得再去,黑爬樓梯。
;
夜深人靜,高跟鞋的鞋跟落在樓梯上,有響聲,聽得讓人心焦。索踮起腳跟,快步跑上去,一路到了傅侗文門外,駐足。
門虛掩著,想從隙看一眼,沒有用。
只得著頭皮:「三哥。」
無人應聲。
沈奚輕輕推門,看到傅侗文背對著門,正穿西裝:「關上門。」他說。
沈奚反手將門關上,著他的背影。
傅侗文說:「今日是告別夜。」
「嗯。」明白。
「看你的樣子,也很傷?」
沈奚再點頭:「大家都是,尤其……婉風,我想最捨不得三哥。」
覺得這話說得再平整不過,可傅侗文卻忽然回來看。不言不語的,竟讓心虛起來,窗外刷刷落著雨,從這裡看,能見到雨滴斜砸在玻璃窗上的一個個印子,麻麻。;
「你以為,方才和我說了什麼?還是做了什麼?」傅侗文忽然笑問,「是不是只要我和一個孩子共一室,總能讓人去誤會?」
沈奚再次驚訝於他讀心的本事,訥訥道:「並沒有。」
雖然這是一句假話。
傅侗文饒有興致地笑著:「我說告別夜的意思是,我該離開紐約了。」
「你要走?和他們一起回國嗎?」
「不,我利用了他們,其實要走的是我。」
傅侗文用最簡單的話解釋,他因為不想與人合作片生意,惹了點麻煩。所以他現在必須走,用顧義仁的份走。此行,他帶來的僕從都不會跟隨,包括那個年,也會按照他原定的旅程去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分院,去拜訪他的一位老朋友。
而顧義仁和婉風也要離開,過了今夜,這裡將是一個空置的公寓。
他輕描淡寫,好似在說他要去踏青,從北京城東到城西。;
可這是匆匆潛逃,遠渡重洋,三個多月的航程。稍不甚就會要了人命。
「只有你和譚先生?」沈奚急匆匆問,「這怎麼可以。」
「這怎麼不可以?」
傅侗文從書桌上的雜誌里,翻出了一張支票和一張名片:「你來,只是想說抱歉。你們三個都會被安排離開,沈奚,日後沒人再照料你了。」
他走到面前,將支票遞到眼下:「你去加利福尼亞,換一位導師。」
天高海闊,他在和告別。
沈奚低頭看名片上的名字,很有名的一位學者,所以他剛來時,婉風說他去「探朋友」,難道就是早為做了另一手的安排。
「骨科的。」他說。
沈奚手有千斤重,抬不起,搖搖頭。
不是三年前的了。
那時不懂,沒見過世面,想得,正因為那樣目狹隘,才會覺得不過是出國讀書。現在不一樣了。離別夜,或許也是訣別夜。;
萬里之遙,家國盪,全世界都在打仗,在逃離,在骨分離。每一次道別可能都是最後一面。沈奚的心空出來一大塊,發慌,不由自主地搖頭。
「我想回國。」低聲說。
這是一個讓他意外的回答。
「每個地方都是兵荒馬,」沈奚覺得自己在胡言語,因為腦子完全跟不上,「我怕我學時,沒了回國的機會,或者我還沒回國,國就參戰了。這些都說不準,萬一……我是說萬一,我學了,反倒客死他鄉,那豈不是這些年的辛苦都白費了。」
他終於微笑起來:「你有點像我四弟,迫不及待,好像晚一分鐘,晚一秒鐘,都要國破家亡了。」他說這話時,是笑著的,可卻讓人到了一種極其無力的傷。
說完,他沉默著,掏出懷表。
這是在看時間,也是在考慮。
等待的忐忑緒排山倒海地過來,在想,倘若他拒絕,要再用什麼理由說服他。;
分分秒秒。
窗外的雨勢更大了,砸得玻璃窗砰砰作響,一定混雜了冰塊,才敲得如此起勁。
沈奚輕輕地換了口氣,耐心等。
「你的前程,在你自己手裡,」傅侗文將懷表收回去,「也許,一百多天的航程,你會死在海上。那時,你後悔就再來不及了。」
這是答應了。答應了。
沈奚的流心房,激的臉頰紅紅,笑起來。
「就像Titanic嗎?」
傅侗文輕搖頭,笑嘆:「醫學生大概都是一個子。」
死生無忌諱。
原定計劃,沈奚是最晚離開這裡的人,自然也沒有讓提前準備。是以,傅侗文從做了決定後,沈奚一刻也沒敢再耽擱,沖回到自己的房間,將擱在床底下三年的老皮箱子拉出來。上頭落了厚厚一層灰塵,巾草草了,開始裝行李。;
裳,外的,計算三個月的時間,只要及時清洗,無須太多替換。書籍太重,丟掉又捨不得。將箱子蓋上,又覺得不放心,再打開,將手刀放到了最上層,最容易拿到的地方。最後書的比例太大,比譚慶項的箱子還要重。
費力提著皮箱子到了客廳,年負責幫裝上車,提起的一霎,臉就變了:「你這是要拖三爺的後嗎?」
沈奚臉一白,想奪下箱子,再刪減一番。
「讓帶,又能重多?」譚醫生笑著,接過箱子,輕鬆自如,「我看,你是看不慣你家三爺不帶你走,帶了吧?」
年倒也不否認,板著臉問:「三個月在海上,你曉得如何伺候三爺嗎?」
伺候人……過去的知識庫里,只有如何伺候大菸鬼的教程。
「我何時需要人伺候了?」
傅侗文從樓梯走下來,兩隻手的手指從後向前,過立領襯衫的領口,最後落在了領帶上,輕輕扳正。這一番做派,真不是去逃命。;
「尋常的瑣事……倒也不用,」年鬱郁,「可誰給三爺洗燙裳?」
「這個我會。」沈奚舒了口氣。
「會配裳嗎?三爺穿西裝,連子皮鞋也是要配好的。」
這關乎審,沈奚遲疑了一下。
「沈小姐,」他雖看不上沈奚,倒也不得不隨著三爺這麼喚,「若是路上真有生生死死的事,記得三爺是救過你的。攸關命了,你要和我們一樣,保三爺。」
話沒接上去,年又了重擔下來。
「你這咄咄人的樣子,倒很像個白相人。」
年啞了。
沈奚沒聽明白,輕聲問年:「白相人是什麼。」
幾個僕從都笑了。
其中一個中年人回說:「小錢的家鄉話。」
沈奚點點頭,其實沒懂。;
他們在這時都是輕鬆的,在客廳里,像在送傅侗文去赴一場宴席。當有人為傅侗文他們開了大門,氣氛漸冷了。沈奚也被這抑氣氛搞得張不已。
風灌門廊里,颼得額頭髮。眼前頭,傅侗文高瘦的背影,從大門走了出去,不回頭,看了眼這公寓。擺放在門廊上的大理石雕像,桌上沒有水和鮮花的玻璃花瓶,鐘錶,還有地板,最後看了一眼曾翻找出巧克力的柜子。
這一晚,前半場沉浸於離別,而後半場,卻是在匆忙中離去。
與人的告別很不舍,可和這間公寓的告別,竟也讓心生傷。顧義仁還在酣睡,婉風一定在照顧。誰都沒料到,是先離開了。
三年留,沉酣一場夢。
猜你喜歡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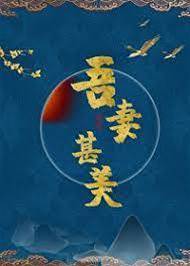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
完結240 章

淪陷:熱吻野玫瑰,於他心上纏綿
【高甜互撩+寵妻+雙強+馬甲+團寵+雙向奔赴】唐芷酥在兩年前不小心闖進了一個神秘男人的浴室裏。看了眼一絲不掛的他,因此被追殺了兩年。兩年後,參加好姐妹的婚禮,機緣巧合之下她竟然把當年那個俊美陰鬱的男人給睡了!——傳聞帝瀾國最矜貴神秘的男人暴戾殘忍,不近女色。可唐芷酥不久後發現他把避孕藥換成維生素,才知這個男人對她不是一時興起,而是蓄謀已久!後來,炎魁將她圈在懷裏,低頭埋在她頸窩間,深情又虔誠:“我說過,你要對我負責。”
44.9萬字8 33357 -
完結104 章

他的癡纏
【京圈?雙釣係?畜謀已久?雙潔·甜寵】周燼是京城裏出了名的混不吝。傳聞他對女人尤為的挑剔,一般貨色入不了他眼。得知自己被當做替身的那晚,遲醉抱著試試的心態,約上了周燼。-這晚過後,遲醉發現自己不論處於什麽樣的“險境”,都能落入一雙懶散的眸子裏。他眉宇風流,欲帶她做盡下作之事。......小劇場,某個豪華包廂裏。遲醉被吻的滿臉紅暈,喘著粗氣,也不能將身上的人,推開半分。“你夠了。”周燼狹長的眼眸,一臉癡迷的看她媚意從骨縫裏流出來。低笑一聲,薄唇摩挲著她耳垂。“就愛你的這一麵。”獨屬於他。——遲醉一直認為,不小心聽到宋雲崢把她當做替身的那晚,是巧合。直到再次不小心,偷聽到他兄弟的對話。才得知。這些所有的巧合,都來自於他的籌謀。他早就愛她入骨,也非她不可,而她也同樣沉溺於他所有的體貼。**-所做的一切不過引你沉淪。多巴胺的綁架沒有救贖,唯有你才是使我上癮的囚徒。
19萬字8.18 8074 -
完結102 章

我的林先生不說話
【1V1+初戀+一見鐘情+雙箭頭互相寵愛】【溫暖細膩特教老師✖自卑敏感全職作家】 * 剛搬來新家的林昭昭一直以為住在隔壁的鄰居是一位人美心善、熱愛生活的小姐姐,直到她那天晚上遇到了從電梯里走出來的大帥哥林星野。 一日,林昭昭對父母宣布:你們啊,要有女婿了! 又一日,面對編輯的連環催稿,林星野告訴他:我有喜歡的女孩子了。 林昭昭說:救命之恩,你怎麼也得以身相許吧! 林星野在胸膛前打出一串串優美的符號,眉眼認真地告訴她:醒來后的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歡上了。 * 戀愛后,林昭昭看到網上最近很火的【對象和異性關系你能忍到幾級】測試題,于是—— 林昭昭:第一級,見面打招呼。 林星野一臉嚴肅,堅決地搖頭。 林昭昭:第二級,有聯系方式。 林星野身體前傾,雙手握拳捶向桌面,堅決地搖頭。 林昭昭:第三級,偶爾的關心。 林星野往后推開凳子,抬腿往玄關去。 林昭昭追上他:你干嘛去? 林星野氣呼呼地比給她看:你欺負我!我要去告狀!
17.7萬字8 341 -
完結167 章

靳總別怕!夫人靠烏鴉嘴爆紅了
【錦鯉體質/烏鴉嘴/重生爽文/娛樂圈甜文】 江晚星重生了,還意外覺醒了烏鴉嘴能力! 只要是她詛咒別人的事,她一定會烏鴉嘴讓那件事變成真的。 于是……江晚星靠著這個離譜的外掛,成了娛樂圈“姑奶奶”,誰都惹不起她。 遇到上輩子害死他的渣男前男友,江晚星小手一揮 “又想來騙我錢?滾吧你,死渣男!” 帥氣的多金總裁在床上,赤紅的雙眼里含著淚水。 “前世他也跟你這樣玩過嗎?” 江晚星伸手扯住男人的領帶,表情嬌媚。 “我只跟你這樣玩。”
30.5萬字8 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