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配不摻和》 第135章 神醫19
治到第三個療程, 牛大寶已經可以扶著牆壁走幾步了, 餘下的一個療程只需鞏固效果便好, 應該出不了什麼差錯。至此, 林淡已收集到厚厚一沓資料, 全都是在治療的過程中寫下的心得和注意事項,有了這個, 再來治療大哥,應該會有相當的把握。
這日, 辭別牛大寶和牛大嫂,又採集到足夠的藥材, 便匆匆趕回了家,等大哥吃完晚飯才握住他的手,慎重道:“大哥, 從今天開始,我來爲你治。”
薛伯庸經由兩名侍衛之口, 已得知林淡在田鄉做的事, 倒也並不到驚訝。
“那就拜託你了。”他反握住林淡的手, 目中充滿信賴。
“大哥, 我用的方法比較冒險, 你若是懷力,千萬不要運功抵抗,只平靜接便好。第一個療程結束, 你應該就會產生麻的覺, 第二個療程結束, 雙的知覺能恢復大半,第三個療程便可以站立起來,自行走幾步。不過大哥的比尋常人強健很多,武藝又高強,或許不用三四個療程,只一兩個療程,就會有奇效。”林淡語氣平靜地道。
“好,我明白了。不管治不治得好,我都無所謂,你別太有力。”薛伯庸掏出手絹,替小丫頭掉額頭上的汗珠。此時已是隆冬時節,屋即便燃了火盆也冷得很,卻不知不覺冒出滿頭汗,可見心裡是很張的。然而聽侍衛說,在田鄉爲那名年治療時,全程都很冷靜從容,未見出任何不自信的神態,所謂關心則,爲不相干的人治療和爲親近的人治療,到底是不一樣的。
思及此,薛伯庸輕笑兩聲,表越發溫。林淡奪過他的手絹,把汗溼的後頸也了,惹得他從低笑變爲朗笑。
Advertisement
站立在門口的一名侍衛忽然說道:“將軍,事關重大,我們要不要通知老太君和夫人,再修書一封告知大將軍?”薛大將軍曾回過府中一趟,見兒子被林淡照顧得極好,又放心地走了,現在已抵達邊關,想來一兩年都不能歸家。
“不用告訴他們,祖母年紀大了,一驚一乍的對不好。母親是個心的子,也會整天記掛著,倒不如等我徹底痊癒了,再去他們面前走一走。”薛伯庸擺手拒絕,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給小丫頭太大力,也不想讓那麼多人出現在面前,打攪的安寧。
侍衛點頭應諾,再不提告訴前院的話。
林淡讓大哥除去上和長,只著一件短,平躺在牀上。正準備丹藥片,忽聽大哥語氣沉沉地開口:“爲那牛大寶治療時,他也穿這樣?”
“是呀。”林淡眨眨眼,表無辜。
薛伯庸闇自咬牙,卻也沒再說什麼。醫者父母心,在人命面前,男大防都得靠邊站,小丫頭這樣做沒什麼不對。他努力開解自己,臉這才和緩下來。
林淡完全不知道大哥在想些什麼,只管把好的丹藥片和丹座放置在他的各大要上點燃,熱之後再行施針。大哥的質果然比牛大寶好無數倍,金針剛開始,他就已經有了反應,早已麻痹的雙竟不控制地搐了一下。
“將軍,您覺怎樣?”守在院外的侍衛,此時已全數來到門口,張而又期待地看著他。
被螞蟻啃噬的覺實在談不上舒服,但比起曾經的毫無知覺,眼下的痛苦竟似一場歡愉。薛伯庸咬牙道:“我很好,前所未有的好!”
“大哥,你現在可有微麻的覺?”林淡輕輕捻針尾。
“不是微麻,是劇烈的痠麻,像是有無數螞蟻在我的皮裡鑽。”薛伯庸目不轉睛地盯著林淡,然後擡起袖口,爲掉額頭的汗珠。
林淡也不躲避,反倒把側臉上去,在他袖子上蹭了蹭。現在兩隻手都在捻鍼尾,藉助針尖的震來探知勁衝的況,本沒空去料理汗溼的自己。
薛伯庸被小貓一般的舉逗笑了,即便深陷皮之痛,即便心神也在劇烈的翻涌,但與眼前這個實實在在的人比起來,一切都顯得不那麼重要了。他常常說這雙治不治得好都無所謂,讓林淡不要太過拼命地學習,更不要給自己太大力,那絕非虛言。能痊癒固然很好,不能痊癒,他的生活也很滿。
林淡完全沒料到大哥的反應竟如此強烈,當即便冒出一頭一臉的冷汗。給牛大寶治療時,可以心靜如水,可眼看著大哥苦,卻覺得十分難,更產生了難以言喻的慌。
“大哥你撐住,熬過去就好了。”重複呢喃著這句話,也不知是在安大哥,還是在安自己。
薛伯庸立刻把痛苦之下,然後極力控制住不停搐的雙,安道:“我覺好多了。”
“真的嗎?”林淡看著不停震的金針,表有些不確定。
“真的不痛了,也不麻了,雙開始有知覺了。”薛伯庸微微一笑,狀似驚喜。
林淡這才大舒口氣,喟嘆道:“難怪業界有一句箴言‘醫者不自醫’,先前是我心,差點誤了事。”
薛伯庸握住的手輕輕拍了拍,瞬間就覺得自的痛苦已經遠去,唯餘溫暖喜悅。
又過了三刻鐘,金針才停止震,林淡拔針後給大哥熬了一碗藥,親眼看著他服下,躺平,閉了眼睛,才放心地回房。但不知道的是,等走後,薛伯庸又坐了起來,著自己痠麻脹痛的雙,久久無法睡。
---
半月之後,薛伯庸開始頻繁地外出,老太君和薛夫人派人去打聽況,只得了句“外出散心”便沒有下文了,只能隨他去。他願意走出薛府是件好事,總比悶在家裡強。
林淡照舊每天出去行醫,天黑了纔回來。老太君不管,薛夫人倒是頗有微詞,每每想把喚來正院訓斥,派去請的僕婦卻先被大兒子狠削一頓,哭哭啼啼地回來覆命。大兒子對林淡的維護簡直到了不分是非黑白的地步,林淡想做什麼他都支持,想要什麼他都給予,完全不問因由。
才短短數十天的功夫,他那嘯風閣的一半房屋便被林淡改裝了藥房,院裡院外曬滿了各種草藥,味道能薰死個人。他非但不管,還把隔壁一戶人家的小院買下來,說是要打通院牆,給林淡建造更多庫房用來保存藥材。
薛夫人有時候甚至在想:若是林淡要兒子的命,他恐怕也捨得給吧?他簡直中了林淡的毒!
至此,林淡對薛伯庸的影響已達到了無人能夠取代的程度,在府裡,他就樂呵呵的,不在府裡,他便沉著一張臉,不言不語、不喜不怒,著實冷得嚇人。更甚者,他還會懶得在府裡多待,林淡前腳出門,他後腳也走了,臨到傍晚才與林淡一塊兒回來,被侍衛擡下馬車的時候滿臉都是溫的笑意,彷彿完全變了一個人。
薛夫人眼睜睜地看著兒子越來越依賴林淡,竟不知該勸阻還是放任,跑到老太君那裡把這事說了,老太君擺擺手,給一句話——兒孫自有兒孫福。如此,薛夫人便也不管了,且由他們去吧。
大兒子的未來彷彿有了著落,小兒子這頭卻出了問題,軍營不去了,差事不要了,整天待在家裡飲酒,把自己弄得醉醺醺的。薛夫人不用想也知道,必定又是吳萱草鬧出了什麼事,讓小兒子吃心了。
正準備找小兒子聊一聊,順便開解他,許久未見的吳萱草卻自己登門了,還帶來了很多禮。薛夫人極想去打聽況,卻被小兒子拒之門外。兩人談了片刻,隨後便和好如初,把薛夫人氣了個倒仰。深恨自己爲何肚皮那般不爭氣,生下來的兩個兒子都如此沒骨頭,被人哄一鬨就找不著北了!
此後,吳萱草就經常來薛府玩耍,偶有一日救下了不慎落池塘的二房長孫,二房對激涕零。但凡來,二房的老太太和嫡長媳都會親自作陪,把當做上賓看待,時不時還會追問老太君何時給和薛繼明舉辦婚禮。
薛夫人雖然很憋屈,卻也念吳萱草的救命之恩,對倒也沒有先前那樣牴了。
終有一日,吳萱草聽說薛伯庸的椅壞了,準備拿去木匠鋪修理,便自告勇地說可以幫忙看一看。由於椅是發明的,況且二公子親自帶過來,侍衛倒也沒敢阻攔,把他們請了嘯風閣。
吳萱草看了看椅,說自己能修,但是手頭沒有工,讓侍衛去找。侍衛不疑有他,很快便離開了。吳萱草又找了個藉口把薛繼明支走,然後快速跑進林淡的書房,一眼看準了那口紅木描金的大箱子。
有一個強烈的念頭在腦海中反覆迴盪——是的,就是這口箱子!你要的東西就在裡面!
猜你喜歡
-
完結390 章

帶著空間超市去種田
夏稻花穿越了,後腦勺上破了個大洞,誰幹的? 好消息,辛苦經營的超市跟來了! 壞消息,她住的縣城遭遇了侵略! 夏稻花在戰火中捨命救人,救出來一個帥哥,帶出來三個拖油瓶,和好幾波敵軍與刺客; 夏稻花抗旨不遵,結果竟然當上了攝政王,還被先帝託孤? 聽說夏稻花還沒嫁人,媒人踩破了門檻; 大將軍揮揮手把他們都趕走:攝政王今天不相親!
66.9萬字8 41635 -
完結548 章

穿越後,替身王爺哭著求我不和離
天下人都說,王妃葉知舟愛慘了寧王,她以一個棄妃之身,一夜之間成為神醫,治皇帝,救妃嬪,逆轉乾坤,為寧王掙萬兩黃金家財。 誰要是敢動寧王一下, 她葉知舟能提著刀把那人斬首示眾。哪怕寧王將她虐得肝腸寸斷遍體鱗傷,她也依舊甘之如飴。 直到有一日,她喝得爛醉,對寧王說: "寧渡, 你笑起來很像他,隻要你肯笑一笑, 想要什麼我都能給你。” 冷傲矜貴的寧王聞言忽然發了瘋,將她壓在床上,一遍一遍問他像誰。 後來,有人說寧王被王妃寵瘋了,王妃對他厭倦,他就跪在他門前,啞著嗓子說自己心甘情願做替身,她卻再也不肯看他一眼
82.5萬字8.33 66567 -
完結20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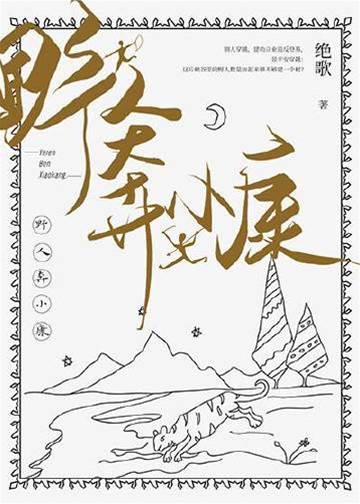
野人奔小康
景平安在職場上辛苦打拼,實現財富自由,卻猝死在慶功宴上,悲催地穿越成剛出生的小野人。有多野?山頂洞人有多野,她就有多野,野人親媽茹毛飲血。鉆木取火,從我開始。別人穿越,建功立業造反登基,景平安穿越:這片峽谷里的野人數量加起來夠不夠建一個村?…
80.8萬字8 5299 -
完結217 章

朕的愛妃太能卷了
互聯網大廠卷王姜嫻穿越了。穿越前,她剛因為焦慮癥向醫生求助:“我一天不加班渾身難受,放一天假就呼吸不暢,怎麼辦?”朋友問道:“你這病傳染不?來我公司待一下,抓緊把這病傳染開去!”穿越后,來到慢節奏的后宮,人人無所事事,她快閑瘋了!于是她二話不說,直接開卷。*某不愿透露姓名的答應:十一月份,京城雪下得最大的時候,姜答應天天在梅園跳舞!我的親娘啊,用得著這麼賣命嗎?爭寵什麼的,那就不是我們年薪四兩該操心的事。所以同年,姜答應成了美人,而她還是答應。*再后來,傳聞姜貴妃和后娘關系不睦,後孃得子後進宮求見,貴妃娘娘賞她十五字真跡,掛在便宜弟弟牀頭——距離科舉考試還有四千三百七十天。在老闆面前刷存在感,姜嫺是專業的。你見過凌晨三點的後宮嗎?宮妃五點起牀,她三點:宮妃賞花賞月看戲扯淡的時候,她在練舞練歌練琴,鑽研大老闆的喜好,業務能力和奉承阿諛兩不誤,姜閒相信,只要這麼卷下去,老闆升職加薪必然第一個想到她。而皇帝見識過無數爭寵手段。還真獨獨記住了姜嫺一一這女人實在太愛朕了!
35.6萬字8 24253 -
完結615 章

採石記
作爲穿越女的穆長寧,似乎出場就是炮灰命。 在忍不住反抗之後,老天終於給她開了扇窗,莫名其妙丟了塊石頭進來。 嗯,那就好好修仙吧……
157.3萬字8 11954 -
完結410 章
仵作狂妃
她本是令罪犯聞風喪膽的名法醫兼犯罪心理學專家,一朝穿越,成了西孰國一名普通人家百般寵愛的小女兒韓玥。 為報仇,她重新拾起解剖刀。 快速得出驗屍結果、收錄指紋的高科技人體掃描器成了她的神助攻。 為完成前世抱負,她又不得不對他百般討好。 然而,兩輩子都沒談過戀愛的她,對這種事實在是不怎麼拿手。 尤其對方還是西孰國唯一的異姓王,軍功壓人,腹黑狠辣,權傾朝野卻對女人嗤之以鼻。 初時,她笨拙地討好,做美食,送禮物。 他雙眼危險一眯:「你想從本王這裡得到什麼? “ 她鼓起勇氣:”我想借你的面子,進衙門,做仵作! “ 後來,他百般縱容,一路護航。 可惜,某女無動於衷,忍不住問道:“我這般對你,你可有什麼想法? “ 某女一臉嚴肅:「王爺放心,我會把每具屍體都驗的明明白白,絕不給你丟臉! “ 他吐血:「你敢不敢來驗驗我的心! ”
70.2萬字8.18 2174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