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配不摻和》 第129章 神醫13
眼看薛伯庸狀況已經穩定, 而自己也到了該積累經驗的時候, 林淡終於決定出門行醫。
“大哥,我出門去了,許是下午才能回來。”臨走之前, 先行去隔壁房間打招呼。
薛伯庸看見穿一套布裳,背上揹著一個竹簍子,手裡拿著一串搖鈴, 一副出門遠遊的樣子,眉頭就是一皺, “你去哪兒?”
“我去城外的各村各寨走一走, 替人看病。該看的醫書我都看完了, 該懂的醫理和藥理, 我也都懂了, 現在就差實踐。京城裡的人特別講究,有病都去醫館看坐堂大夫,我這種初出茅廬的愣頭青, 醫館肯定不收, 就只能去偏遠的鄉野走一走。那裡的百姓生活條件比不上城裡人,得了病大多隻能捱過去,除非嚴重了才套上牛車進城。我若是主找上門去替他們看病, 再收一點診費,想來他們是願意的。待我積累了足夠的經驗, 早晚有一天我能把大哥的治好, 大哥你等著吧。”林淡一邊說一邊擺手, 竟就這樣走了。
薛伯庸連忙喊住:“你給我等等,你一個弱子整日在外行走,若是遇見危險怎麼辦?”
“大哥,我不是弱子。”林淡了自己的小拳頭。
想起輕鬆抱起一個大男人的力量,薛伯庸表微微一滯,卻還是強道:“你要行醫我不攔你,但你出門在外必須帶侍衛,否則你就給我在家待著。”
林淡見他表堅決,只好敷衍道:“好吧大哥,我都聽大哥的,你、你,跟我一塊兒出去。”話落隨便點了兩個侍衛,轉頭就走,也不管人家跟沒跟上來,那架勢簡直比沙場點兵的元帥還練。
Advertisement
薛伯庸看著直的背影,表有些氣惱,又有些無奈,頃竟扶著額頭低笑起來。他擺手道:“去吧去吧,隨去吧,務必把人保護好。”
被點到的兩名侍衛這才拱手領命,大步追上去。
看著已經關嚴實的院門,薛伯庸搖頭呢喃:“我並未怪你,你這又是何苦。”話雖這麼說,但他冷的心,卻早已被這倔強的小丫頭攻陷了一角,變得起來。
林淡走後,院子裡顯得格外安靜。以往這個時候,已經在書房裡唸書了,嘀嘀咕咕的背誦聲時不時傳出來,像一大羣蜂在嗡嗡。薛伯庸曾抗議過幾次,習慣地答應下來,到了後面又會忘記,背書背出聲音彷彿是的習慣。及至現在,薛伯庸竟也習慣了的習慣,這聲音忽然消失了,他反而覺得哪兒哪兒都不自在。
他讓李忠把自己背到外面曬太,嘆息道:“小丫頭今天早上沒問我中午想吃什麼菜。”
李忠下意識地答道:“林姑娘說下午才能回來,中午的飯菜是方廚娘做。大公子您想吃什麼,我現在就去廚房說一聲。”
薛伯庸意興闌珊地擺手:“不了,我什麼都不想吃。”
見大公子表抑鬱,眉頭皺,彷彿又回到了剛傷那會兒的樣子,李忠連忙說道:“要不小的現在就把方廚娘過來,問問今天小廚房進了什麼新鮮食材?”
“不用了,過午再說吧。”薛伯庸依舊沒有興趣,只是盯著院門,不知在想些什麼。
以往早飯剛吃完,林姑娘就引逗著大公子把中午想吃的菜點好了。今天林姑娘不在,大公子菜也不點,還說午飯得等到過午再說,這擺明了是不想吃東西的節奏!李忠越發張起來,壯著膽子丟下一句“我去小廚房看看”就跑了。
薛伯庸閉上眼睛,表有些寂寥。儘管他邊圍滿了侍衛,儘管在這院牆之外,還有數不清的僕婦伺候,可他忽然之間就覺得心裡空的,沒個著落。
過了一會兒,李忠便跑回來了,焦急的表已被滿面笑容取代,“大公子,您肯定沒想到,林姑娘走的時候在竈臺上燉了一鍋牛,等到晌午就燉爛了,您正好能吃。我方纔聞了聞,那滋味簡直絕了,若非我手捂得快,口水都會滴進鍋裡。也不知林姑娘放了什麼調料,不掀開鍋蓋便罷,一掀開,滿廚房的人差點被薰醉,我從來沒聞過那麼香的牛!”
原本還有些心不在焉的薛伯庸,此時已扭過頭來認真聽他說話,漆黑的雙目不斷閃爍亮。他這纔想起,昨日睡的時候,小丫頭曾跑到他房裡來問他最近有沒有特別想吃的東西,他當時隨口說牛,卻沒料這道菜今早走的時候就燉上了。
走了還擔心大哥的午飯沒有著落,這小丫頭……思及此,薛伯庸以拳抵脣,極力遮掩自己高高翹起的角。
---
林淡臨走的時候已經把該做的事都做了,該代的也都代清楚了,完全不用擔心大哥那裡會出問題。僱了一輛牛車,緩緩朝城外駛去,眼看城門在即,便對兩名侍衛說道:“我是爲了安大哥才答應讓你們跟來,但其實我一個人就可以應付所有突發狀況。你們跟著我也無事可做,不如幫我去尋找一個人。”
兩名侍衛一言不發地坐在車棚外,完全不想搭理。
林淡也不生氣,繼續道:“你們幫我尋找與大哥的癥狀一模一樣的人,都是摔倒之後雙癱瘓的,找到之後把那人的地址告訴我,我去醫治。我沒有經驗,不好隨意在大哥上下針,想找一個類似的病人診治看看。我告訴你們一句實話,林朝賢是我的曾曾曾……祖父,我家祖傳的玄濟針法或可治好大哥的雙。無論如何,這也是一條生路,請你們務必重視。”
抱著佩刀閉眼假寐的兩名侍衛猛然睜開雙眼,朝車裡看去,卻只看見一層竹簾。
“林朝賢是你的祖輩?”二人齊齊開口,語氣慎重。
“自然,這事大哥也知道。”林淡掀開竹簾,追問道:“這個忙你們幫是不幫?”林朝賢的醫被人傳得神乎其神,但他留下的醫書偏偏了最重要的一本,於是乎,林家人才匿起來,不敢隨意宣揚,唯恐保不住這份傳承,反而徹底壞了先祖的名聲。
林家祖傳的鍼灸之法和推拿之,均要輔以勁纔會見效。沒有勁,醫者一針扎死,病人就會立刻嚥氣,這不是在救人,而是在殺人!也因此,林老爹明明懷家傳籍,卻不敢學,只鑽研了最簡單的跌打損傷之,實屬無奈。
其中,兩名侍衛並不知曉,也無意打聽。他們只知道,任何一點治好將軍的希,他們都必須抓住,於是立刻點頭:“可以,這個忙我們幫了!城裡人多,我們先在城裡找,若是沒有,再去周邊的鄉鎮。”
“那好,你們就在這裡下車吧,酉時我們準點在西城門匯合。”林淡敲了敲車轅,示意車伕停下。
車伕是個大老,什麼林朝賢,什麼玄濟針法,他一概不知,即便他知道並宣揚出去,林淡也不懼。有自信解決任何麻煩。
шшш _тт kǎn _co
兩名侍衛下車之後把腰間的令牌亮給車伕,警告道:“這是薛將軍府的小姐,你定要把全須全尾地送回來。你家在何,有幾口人,我們清楚得很。”
車伕誠惶誠恐地答應下來,等兩名侍衛走了,背後的服已被冷汗浸。早知道這幾位客人來頭如此大,他就不接這單生意了。
“走吧,有我在,路上不會出事的。”林淡擺擺手,語氣平靜,完全沒意識到保護者和被保護者的位置已經被完全顛倒過來。
其實薛府也有馬車,但裝潢都很華貴,不適合在鄉間行走。再者,若是府里人需要用馬車,就得去薛夫人那裡報個備,如此,林淡的計劃還能不能行都是個問題。薛夫人可以容忍留下照顧兒子,不見得能容忍去當一個行腳大夫,給薛家丟臉。
說一句不中聽的話,林淡對講究面的薛夫人十分不喜,若非原主留下的孽債必須由來還,早就甩手走人了。
車伕被小姑娘強橫的態度逗笑了,張的心瞬間鬆懈下來,抖著繮繩趕著牛車,緩緩駛出城門。
林淡把藏在竹簍裡的一套銀針和一個人形木偶取出來,抓時間練習鍼灸之法。已極力控制住勁,卻還是在針的時候略微失了分寸,暴的罡氣順著針尖匯木,瞬間炸出一個小小的空腔。
只聽“噗”地一聲悶響,雪白木屑從空腔裡噴出,灑了林淡一臉。所幸這套銀針的材質十分特殊,能夠承勁的摧折而不斷裂,否則連吃飯的傢伙都會一併毀掉。要是把木偶換真人,可想而知,現在灑一臉的就不是木屑,而是鮮和碎。若是不能控制好勁地輸,這套針法就只能殺人,而非救人。
是以,剛纔對車伕說的那些話也不算誇張。只要手裡拿著一針,便可以遇人殺人,遇佛殺佛,完全不怕踏險境。
猜你喜歡
-
完結937 章

一胎二寶:神醫嫡女寵上天
江浸月穿越了! 她一個二十一世紀最強特工組織頭號殺手,業內聞風喪膽的醫毒天才,竟然穿越成了一個懷著龍鳳胎的孕婦,還在穿越當天生產了! 孩子爹是誰?她一個半路穿越過來的人給忘記了… 沒人認領她就只得自己養,拿了人家的身體,可就得替人家報仇,把那些不該享受滿門榮耀的人重新踩回地獄去,可踩著踩著,她竟然絆倒在個美男身上。 “小月月,今晚陪伴可好?” “滾,帶著你的倆娃一起滾!”
175.7萬字8 192912 -
完結217 章

醫女凰謀
華夏醫學聖手,一朝穿越,成為越國將軍府的大小姐,父親逝去,她被一張聖旨招入宮中成為皇後,而他護她,守她,卻不能愛她。
38.2萬字8.18 40462 -
完結2757 章

我家王妃很任性
鬼醫毒九一朝醒來,成了深崖底下被拋尸體的廢物,“哦?廢物?”她冷笑,丹爐開,金針出,服百藥,死人都能起死回生,這破病就不信治不了了。然而低頭一看,還是廢物。“……”…
499.8萬字8 413827 -
連載104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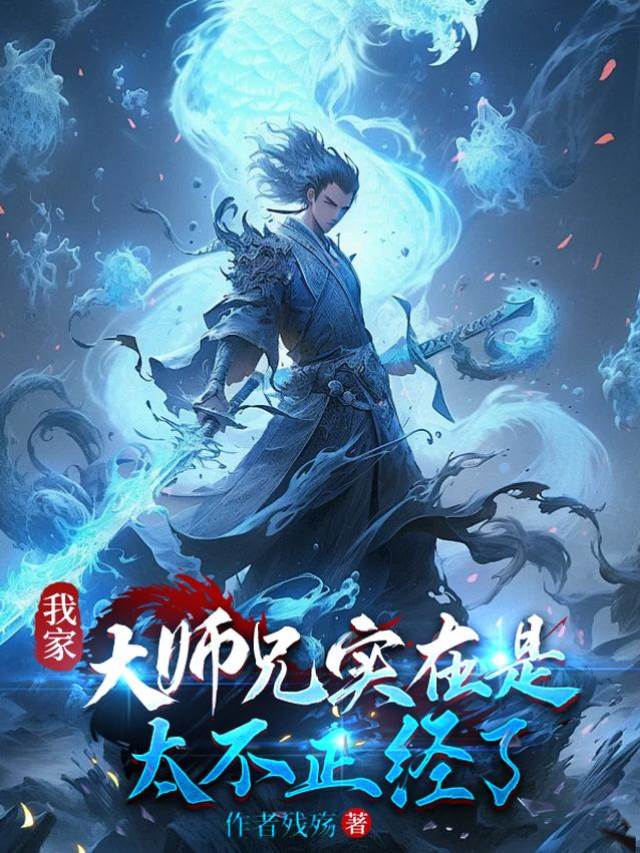
我家大師兄實在是太不正經了
(無敵 輕鬆搞笑 茍道 穿越 無係統)別人家大師兄都是德才兼備,品行端一,風華絕代,天驕無雙,萬人敬仰,宛如璀璨星辰!而我家大師兄懶惰、貪財、不正經。明明擁有混沌大道聖體,卻一心隻想著搞錢!修煉?狗都不修。我都無敵了,搞點錢不過分吧?——摘自陸小川語錄。
192.3萬字8.33 287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