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得美!新婚夜出軌,還跪求我懷崽》 第6章 車禍中絕處逢生
薄荷綠的跑車,在駛出霍氏總廈的地下停車場,正準備轉彎前往市區方向時,一輛大貨車突然從對面疾馳而來。
而這條路,恰巧是一條單行道。
剎車,在這個關鍵時刻,無論霍清昂如何用力,都毫無反應。
眼看兩車即將撞上,對面的大貨車,不僅未減速,反而還加快速度。
像是發瘋般,徑直衝了過來。
車毀人亡之際,坐在副駕駛的顧翩翩,起撲向霍清昂,手將方向盤來了一個大轉彎,車前半截得以躲過大貨車的前。
車的尾部則與大貨車的車頭,撞在一起,發出“砰”的驚天巨響。
顧翩翩的子,被強大的衝擊力所彈起,腦子徑直撞向擋風玻璃,滾燙的順著臉頰,肆意流淌。
令所沒有想到的是,大貨車在重新啟之後,不是從跑車的尾部立即向後退,而是繼續碾。
Advertisement
這樣的舉,擺明是想致車裡的他們於死地。
接著,又是“砰”的一聲。
是跟他們車後的霍清昂保鏢的車,搶先大貨車的碾,直接撞上來,將他們的車撞出了大貨車的碾範圍。
撞空的大貨車,在一個急剎後撞向一旁的圍牆,徹底熄火。
而顧翩翩僅存的一意識,在絕逢生後的連續翻滾中,逐漸然無存。
被下屬從跑車裡抬出來的霍清昂,渾上下都是,部麻木,毫無知覺。
如果不是顧翩翩反應迅捷,接著又擋在他上,減了緩衝,這一刻的他,只怕是早已經見閻王。
這輛出事的跑車,是霍震雲送給顧翩翩個人的新婚禮。
今日一早,由他親自開回的別墅,因此他百分之兩百的確定,車絕對是沒有任何安全問題的。
但現在,時間才過去半天,剎車就失靈,天底下哪有這麼巧合的事?
“立馬封鎖現場,青的人到之前,任何人不得離開。”霍清昂漆黑深邃的眼眸,寒乍現。
低沉的嗓音,威嚴得奪人心魂。
卻還是在說完這句話後,被的傷擊敗,暈了過去。
青,錦城神組織,國際刑警終合作伙伴。
至今無人知曉他們的老大是誰,傳言:這世間只有他們不想理的事,沒有他們理不了的事。
至於,霍清昂為什麼請得青的人?
同樣無人知曉。
……
顧翩翩睜開眼時,天空籠罩在橘黃的面紗中,霞萬丈。
“霍太太醒了。”一記陌生的男音,徐徐耳。
顧翩翩抬頭,菸灰的柳葉眉,微微擰著,“你是誰?”
陌生的房間,陌生的男人,還有頭痛得快要炸的自己。
“我是霍先生的朋友,也是你的主治醫生。”江尋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工牌,溫一笑道,“把這顆藥吞下,頭就不會那麼痛了。”
顧翩翩接過水杯和藥,並未服下,頓了頓,“霍清昂……他還好嗎?”
車子翻滾的過程當中,霍清昂一直將的頭,護在他的膛裡。
這是關於整場車禍,最後的印象。
“霍先生的況不太好,剛完手,人還沒有醒來。”江尋遲疑了一下,回答道。
顧翩翩神一怔,“手?什麼手?”
“霍先生的,在車禍中被重所,導致中斷過久,暫時站不起來了。”江尋嘆了一口氣,聲音很輕,“以後,只能坐著椅生活。”
霍清昂殘廢了?
重?
那個重不就是嗎……
只一瞬間,顧翩翩的子像是被冰凍住了似的,瘮骨的涼意,以眼可見的速度,吞噬著的每一個孔……
猜你喜歡
-
完結1497 章

天才雙寶:傲嬌前妻抱回家
一場意外,她懷了陌生人的孩子,生下天才雙胞胎。為了養娃,她和神秘總裁協議結婚,卻從沒見過對方。五年後,總裁通知她離婚,一見麵她發現,這個老公和自家寶寶驚人的相似。雙胞胎寶寶扯住總裁大人的衣袖:這位先生,我們懷疑你是我們爹地,麻煩你去做個親子鑒定?
267.8萬字8 65089 -
完結100 章
萌妻迷糊︰第一暖男老公
他陰沉著臉,眼里一片冰冷,但是聲音卻出其的興奮︰“小東西,既然你覺得我惡心,那我就惡心你一輩子。下個月,我們準時舉行婚禮,你不準逃!” “你等著吧!我死也不會嫁給你的。”她冷冷的看著他。 他愛她,想要她。為了得到她,他不惜一切。 兩年前,他吻了她。因為她年紀小,他給她兩年自由。 兩年後,他霸道回歸,強行娶她,霸道寵她。
8.9萬字8 26664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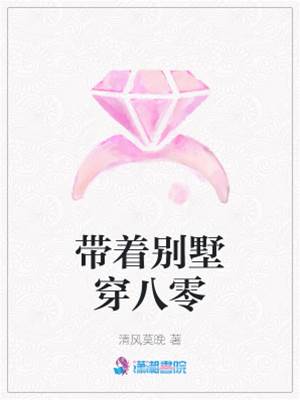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9526 -
完結332 章

辣妻致富1990
身價千億的餐飲、地產巨亨顧語桐,訂婚當天被未婚夫刺殺! 再次醒來的她,發現自己竟然穿越到了生活在1990年的原主身上! 原主竟然跟一個傻子結了婚? 住進了貧民窟? 還在外面勾搭一個老流氓? 滿地雞毛讓她眉頭緊皺,但她顧語桐豈會就此沉淪! 一邊拳打老流氓,一邊發家致富。 但當她想要離開傻子的時候。 卻發現, 這個傻子好像不對勁。在
61.2萬字8 14929 -
完結921 章

一胎三寶:夫人又又又帥炸了
被設計陷害入獄,蘇溪若成為過街老鼠。監獄毀容產子,繼妹頂替她的身份成為豪門未婚妻。為了母親孩子一忍再忍,對方卻得寸進尺。蘇溪若忍無可忍,握拳發誓,再忍她就是個孫子!于是所有人都以為曾經這位跌落地獄的蘇小姐會更加墮落的時候,隔天卻發現各界大佬紛紛圍著她卑躬屈膝。而傳說中那位陸爺手舉鍋鏟將蘇溪若逼入廚房:“老婆,什麼時候跟我回家?”
229.5萬字8 73055 -
連載342 章

從摸魚開始成為學霸
【校園學霸+輕松日常+幽默搞笑】“你們看看陳驍昕,學習成績那麼優異,上課還如此的認真,那些成績不好又不認真聽課的,你們不覺得臉紅嗎?”臺上的老師一臉恨鐵不成鋼地
83.3萬字8.18 41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