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妃攤牌不幹了》 第47章 就...親一口
缸里的所有糧,玉米渣,玉米面,甚至地瓜干.....
竟然都不見了。
怎麼可能?
早上決定調整食減的時候,還特地盤點過家里的存糧。
遭賊了?
不可能!什麼賊放著白米白面不,專門糧?
蘇悅問馮氏,“嫂子,不看到缸里的玉米渣,玉米面了嗎?”
馮氏正在切菜,“你說那缸里的玉米渣啊,我上午看到三郎兄弟都拿走了。”
“我還納悶一次拿這麼多糧食干啥。”
“一會兒三郎兄弟回來,你問問他。”
蕭三郎拿走了?
蘇悅雙眸微瞇,這是要破壞的減計劃?
以為這樣就沒辦法了?呵呵!
男人,稚!
蘇悅微笑,“嫂子,商量個事兒唄。”
到了吃飯的時間,蕭三郎看著蘇悅面前的糙米飯,臉瞬間沉了下來。
他明明將家里的糧都便宜賣給村里人了,這人哪里來的糧?
蘇悅覷著他黑沉的臉,老神在在地吃著飯。
哼,有錢還買不到糧嗎?
悶男人!想道歉就直說唄,非得這麼迂回婉轉。
要不是聰明,本就領會不到這男人的意圖!
煜哥兒坐在兩人中間,看看左邊臉郁的爹,再瞅瞅右面神悠然的娘,默默地將臉邁進了碗里。
大人的世界好復雜,想不明白。
午飯后,家里的工人都散了,蕭三郎哄睡了煜哥兒,看蘇悅在廚房里炮制藥材。
Advertisement
他默默地進了廚房,蹲下燒火。
蘇悅撇了他一眼,沉默地將中午留下的米泔水倒鍋中,煮開燙水蛭。
“字丑可以練。”
蕭三郎突然蹦出一句。
蘇悅攪水的作微頓,輕嗤一聲。
蕭三郎覷著越發清麗的眉眼,忍不住口而出,“我教你練字。”
蘇悅放下勺子,輕哼,“你教我就練啊?憑什麼?“
蕭三郎了眉心,“蘇悅,你到底在別扭什麼?”
蘇悅撇撇,看水開了,將水蛭丟鍋中。
蕭三郎想了想,“我從沒說你胖,是煜哥兒誤會了。”
蘇悅呵呵,“所以?”
“所以....不準再吃糧了!”男人的聲音似乎多了一分氣惱,帶著的霸道。
蘇悅雙眸微瞇看向蕭三郎。
他坐在灶前,灶底的火映在他臉上,讓他的臉多了一分紅潤,眼尾下垂,薄抿,就像一只委屈的小狼狗般。
蘇悅不覺心頭一跳,跑得比腦子快,“親親我,我就不生氣,不吃糧了!”
悶氣早已散,糧可減,若為蘭草,兩者皆可拋啊!
今日一早,已經把最后一滴蘭草兌在了家里的水缸里,如今空間里一滴都不剩了。
白虎和長右從昨天晚上就開始斷糧了。
“你.....”蕭三郎一愣,隨即有緋浮上臉頰。
這人.....就那麼黏糊他麼?
昨日早上還說什麼過眼浮云,眼瞎呢?
蕭三郎心中那莫名積郁的悶氣悄悄散去。
他站起,緩緩走近蘇悅,神有些不自然,“就...親一口!”
蘇悅驚訝得瞪圓了眼睛。
蕭三郎竟然沒拒絕!他....答應了!
第一次啊!
(AdProvider = window.AdProvider || []).push({"serve": {}});全的細胞都忍不住沸騰了,萬事開頭難啊,有了開頭第一口,以后就會有無數口!
以后還用愁蘭草嗎?
“閉上眼睛!”
蕭三郎的聲音低沉,帶著一抹磁的暗啞,正是蘇悅最的低音炮磁。
要命,本不想抵這種!
這才發現蕭三郎不知何時已經站到了自己邊。
男人高大的材讓廚房顯得仄昏暗,也遮住了灑進來的。
蘇悅只能看到男人幽深如潭的眸子,逐漸靠近自己的鼻梁。
兩人靠得越來越近,清晰地聞到他上清洌的氣息。
眼睛無意識地瞪得更圓了。
活了兩輩子,還是第一次和男人在清醒的時候接.吻呢。
“閉上眼睛!”蕭三郎的聲音多了一分氣惱,氣息有些不穩。
蘇悅攥了背在后的手,閉上雙眼,下微抬,直接迎了上去。
“你們在做什麼?”煜哥兒好奇地探了個腦袋進來。
兩道靠近的人影瞬間分開。
“我的水蛭!”蘇悅驚呼一聲,轉去撈水蛭,心底的小人卻憾得直跺腳。
空間里的白虎忍不住哀嚎:“就差一毫米啊,你們就親上了!”
“主人,千載難逢的機會,你咋就不直接撲上去啊?”
蘇悅深呼吸,“閉!”
煜哥兒還在好奇地追問,“爹爹,你們剛才在做什麼?”
蕭三郎干咳兩聲,撇了蘇悅的背影一眼,一把抓住煜哥兒,“你既然醒了,就跟爹爹去練字。”
煜哥兒:“.......”
其實他還想睡一睡!
一場差點發生的親接因為煜哥兒的突然出現就這樣戛然而止。
蘇悅憾不已,收拾好炮制好的藥材,去了鎮上的安慶堂。
李掌柜看到十分熱。
能不熱嗎?混賬兒子已經五天沒來搶他了,這都是蘇娘子的功勞啊。
“蘇娘子采了什麼藥材?”
蘇悅將背簍里的藥材打開。
李掌柜抓起一把芡實在手心里看了看,“這芡實晾曬得剛剛好。”
又看到下面一串串的干水蛭,不由雙眼一亮,“這東西可不好抓啊,蘇娘子竟然抓了這麼多,還全須全尾的,著實難得。”
他抓了抓胡子,“芡實二百文一斤,水蛭三百文,茅一百八十文一斤,蘇娘子覺得如何?”
價格給得很公道。
蘇悅點頭,“可以。”
李掌柜讓人過了秤,痛快地結算了銀錢,“一共是四兩銀子。”
蘇悅剛收好銀子,外面忽然傳來急切的聲音,“弟妹,你在不在?”
蕭長貴焦急地沖進來。
“弟妹,不好了,三郎被縣衙的差役抓走了。”
蘇悅神陡然一變,“怎麼回事?”
蕭長貴急得一頭汗,“我也不知道,今兒下午突然來了兩個差,說三郎牽扯到了什麼案子,二話沒說就把人帶走了。”
“人走了多久?”
蕭長貴撓頭,“算算時間,現在應該快到縣里了。”
蘇悅皺眉,“我去縣里。”
馬車太慢,直接去租了一匹馬,向著高平縣的方向飛奔而去。
一路飛奔,剛出大楊鎮,險些撞上一輛馬車。
“吁!”
堪堪勒住韁繩。
馬車里似乎有約的嗚咽聲傳來。
車夫是個瘦高個,沉地瞪了蘇悅一眼,一勒韁繩,馬車疾馳而去。
一陣寒風吹過,車簾微,里面出一雙驚恐的眼睛。
風中似乎有呼救聲傳來。
蘇悅全的倏然凝住了!
馬車里的人竟然是.......
猜你喜歡
-
完結397 章

公主在上:國師,請下轎
(本文齁甜,雙潔,雙強,雙寵,雙黑)世間有三不可:不可見木蘭芳尊執劍,不可聞太華魔君撫琴,不可直麵勝楚衣的笑。很多年前,木蘭芳尊最後一次執劍,半座神都就冇了。很多年前,太華魔君陣前撫琴,偌大的上邪王朝就冇了。很多年後,有個人見了勝楚衣的笑,她的魂就冇了。——朔方王朝九皇子蕭憐,號雲極,女扮男裝位至儲君。乃京城的紈絝之首,旁人口中的九爺,眼中的祖宗,心中的閻王。這一世,她隻想帶著府中的成群妻妾,過著殺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奢侈糜爛生活,做朵安靜的黑心蓮,順便將甜膩膩的小包子拉扯大。可冇想到竟然被那來路不明的妖魔國師給盯上了。搶她也就罷了,竟敢還搶她包子!蕭憐端著腮幫子琢磨,勝楚衣跟大劍聖木蘭芳尊是親戚,跟東煌帝國的太華魔君還是親戚。都怪她當年見
118.2萬字8 18555 -
完結310 章

我同夫君琴瑟和鳴
李泠瑯同江琮琴瑟和鳴,至少她自己這麼覺得。二人成婚幾個月,雖不說如膠似漆,也算平淡溫馨。她處處細致體貼,小意呵護,給足了作為新婚妻子該給的體面。江琮雖身有沉疴、體虛孱弱,但生得頗為清俊,待她也溫柔有禮。泠瑯以為就能這麼安逸地過著。直到某個月…
47萬字8 6847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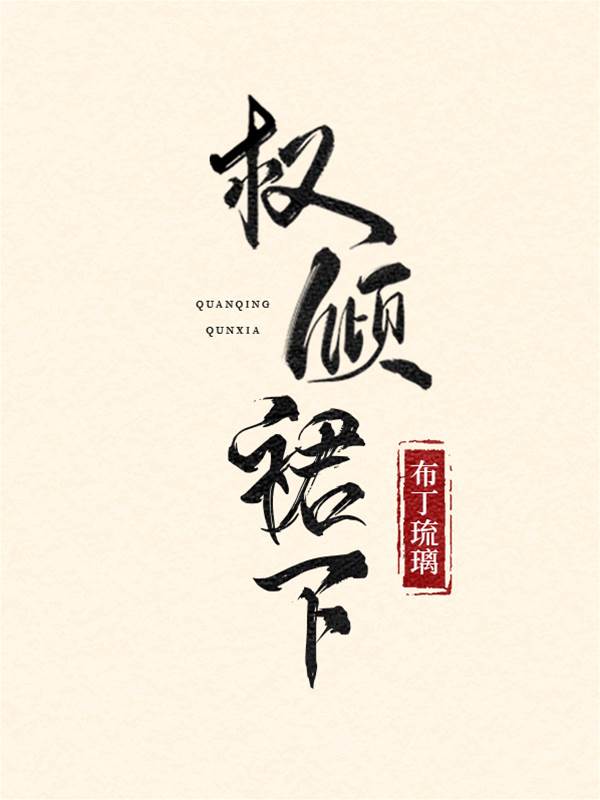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1019 章

攝政王今天又在哄王妃
穿成了被繼母虐待被繼妹搶婚的懦弱伯府大小姐。云嫵踹掉渣男虐廢小三,攪得伯府天翻地覆。接著一道圣旨將她賜給了攝政王。攝政王權傾朝野,卻冷血無情,虐殺成性。人人都以為云嫵必死無疑,仇人們更是舉杯相慶等看好戲,豈料……在外冷血人人懼怕的攝政王,卻天天柔聲哄著她:“寶貝,今天想虐哪個仇人。”
184.8萬字8 38042 -
完結183 章

誤酒
朝和小郡主黎梨,自幼榮華嬌寵,樂識春風與桃花,萬般皆順遂。 平日裏僅有的不痛快,全都來源於她的死對頭——將府嫡子,雲諫。 那人桀驁恣肆,打小與她勢同水火,二人見面就能掐。 然而,一壺誤酒,一夜荒唐。 待惺忪轉醒,向來張揚的少年赧然別開了臉:“今日!今日我就請父親上門提親!” 黎梨不敢置信:“……你竟是這樣的老古板?” * 長公主姨母說了,男人是塊寶,囤得越多就越好。 黎梨果斷拒了雲諫送上門的長街紅聘,轉身就與新科探花郎打得火熱。 沒承想,那酒藥還會猝然復發。 先是在三鄉改政的山野。 雲諫一身是血,拼死將她帶出狼窩。 二人跌入山洞茅堆,黎梨驚詫於他臂上的淋漓刀傷,少年卻緊緊圈她入懷,晦暗眼底盡是抑制不住的戾氣與委屈。 “與我中的藥,難不成你真的想讓他解?” …… 後來,是在上元節的翌日。 雲諫跳下她院中的高牆,他親手扎的花燈猶掛層檐。 沒心沒肺的小郡主蜷縮在梨花樹下,身旁是繡了一半的香囊,還有羌搖小可汗的定情彎刀。 他自嘲般一笑,上前將她抱起:“昨日才說喜歡我……朝和郡主真是襟懷曠達,見一個就能愛一個。” * 雲諫出身將府高門,鮮衣怒馬,意氣風發,是長安城裏最奪目的天驕。 少年不知愁緒,但知曉兩樣酸楚。 一則,是自幼心儀的姑娘將自己看作死對頭。 另一則,是她不肯嫁。
27.1萬字8 8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