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腔》 第8頁
鍾彌回:「去取一件服。」
沈弗崢說話時,他的司機已經撐起一把傘下車來迎。
黑傘如庇護一般到面前來,鍾彌站在風雨里,沒步子,著車裡的男人,微微發愣:「沈先生還沒問我去哪兒?就要送我嗎?」
沈弗崢輕輕一笑,回:「去哪兒都送。」
「上來吧。」
鍾彌上了車,上還有細碎水珠往下墜。
車門關上,隔絕風雨,司機穩穩啟車子,沒坐實,沈弗崢察覺到,將一旁擱置的西裝外套遞給。
鍾彌目從那隻手移至那雙眼,目倉促匯,短暫如燃一支火柴,焰薄薄,潤的眼皮閃避開,一斂就熄。
慢慢接過服,卻沒穿。
低著眼,兩頭看看,一時分辨不出是小牛皮的車貴,還是手上這件定製西裝更貴,弄哪個算值當。
車裡冷氣足,鍾彌涼,頭不控朝前一磕,打了噴嚏:「哈欠——」
「小心冒。」
一旁的男聲似乎微微含笑,鍾彌頓覺窘迫,囔著鼻子,這才乖乖把服披至自己肩頭,說了一句謝謝。
Advertisement
「不用客氣。」
車子過前方減速帶,由主道切進綠植茂盛的小路,行過低矮的居民小區,停在一棟頗有年頭的木樓前。
歇山頂樣式,往前撥朝代,一百多年前還曾是位廉的私人府邸,幾經風雨周折,多番修葺,如今依舊覆黛瓦,撐木窗。
梁枋有古樸的雕刻裝飾,正門掛匾,題的字是鍾彌剛剛跟司機說過的地址。
「沈先生,鍾小姐,寶緞坊到了。」
剛剛在車上簡單聊了幾句,鍾彌才知道,他初來州市,住酒店,這種天氣出門沒急事。
只是賞雨,看看新鮮。
章清姝是寶緞坊的老主顧,一年四季的服大半都是在這兒定做的,寶緞坊穿長袍的老闆認識鍾彌,一見進門便笑著說:「剛剛才說到你呢,說下這麼大雨,今天怕是不會過來了。」
鍾彌俏皮道:「再不來,我媽媽就要罵我啦,說我瘦了,我來試試尺寸。」
介紹沈弗崢,「這位是沈先生,今天下雨我沒帶傘,要不是路上遇見沈先生送我,可能真過不來了。」
沈弗崢頷首。
長袍老闆微笑打過招呼,徒弟取了服來,將鍾彌送進試間。
這是一家三代傳承的做工坊,從鍾彌外婆那一代起,章家就在這裡做裳,店還保留著老布莊的陳列格局,裁臺上,隨便一把烏木尺子都年深月久包了漿。
鍾彌去試。
店裡的學徒很客氣,雖是專做裝的老店,但來者是客,給沈弗崢倒來一杯熱茶,靛藍花紋的平口碟子放兩塊白糕配兩塊糖,都是州市本地的糕餅小食。
淺碧茶湯里,沉著無芽無梗的六安瓜片,雨前茶,清熱消暑。
最宜夏飲。
沒等茶放涼,厚重簾布被一隻纖穠合度的玉白手臂從起,換上旗袍的鐘彌娉婷現,走到鏡子前。
白底青花的料,行間,微有澤,似暈得恰到好的水墨,襯極了這漉漉的晦雨天。
鍾彌左右各側端看了一番。
自我欣賞,正沉浸,冷不防從落地鏡里看到後一雙清矜的眼。
似雨時的窗,晦中生明,拂來一涼。
男人骨節分明的一隻手,端青瓷杯,輕轉著,不知是在品茗,還在看人。
對視那瞬,鍾彌睫一沉,心口倏然短了半口氣,很快藏住自己眼中窘態,心想你看我,我也看你,大大方方一轉,由鏡中的虛,直面他本人的實。
「沈先生,覺得怎麼樣?」
窗角的灰瓦盆里養一株次第開花的唐菖,穠芳依翠萼,站在舊窗前,微微揚起下。
旗袍的最後一粒扣子定在鎖骨中央,往上看,肩線優,脖頸修長,下頜收秀致,再往上,連五也皮骨相宜,挑不出半分瑕疵。
唐菖開花,漸開漸敗。
而的次第開花,都是最好的。
「很好看。」
作者有話說:
瀰瀰和沈弗崢年齡差八。
第4章 新旗袍 鍾靈毓秀的好山水。
往年章士替定做的旗袍,從寶緞坊拿回來就擱進柜子里,等換季,淑敏姨就會幫收起來,鍾彌基本不會再看。
就像景區購回的裝飾項鍊,有幾個人日常會往脖子上戴,用做紀念的東西,到手就已經完「紀念」本的儀式了。
可今年不同。
晚上洗澡出來,吹乾頭髮,鍾彌穿一淡藍碎花邊的吊帶和短,棉綢質地,布料單薄,方便坐在椅子上,架一隻換一隻地塗。
稍顯黏膩,在胳膊上機械地來回塗抹均勻,鍾彌走了神,隔一面圓鏡,看見後櫥那兒掛著的新旗袍。
按上的蓋子,起走過去,連著架將旗袍取下,剛過小的長度,配一米六九的個子正好。
往全鏡前一站,服比在上,手指抓著料收腰,稍稍歪著脖子,垂著眼,自下往上,若有所思地打量著。
「很好看麼?」
晚上臥室的燈過於昏黃朦朧,不似那個雨天寶緞坊里的場景。
灰中泛青的天,檐下雨,窗角的花,和輕靠桌前持葵口杯打量人的沈弗崢,都與這件旗袍相配。
猜你喜歡
-
完結96 章

分手後我懷了大佬的崽
褚雲降和路闊最終以分手收場,所有人都嘲笑她是麻雀想飛上枝頭。幾年後,她帶著兒子歸來。見到路闊,隻是淡漠地喚他一聲:“路先生。”那一刻,風流數載的路闊沒忍住紅了眼圈,啞聲道:“誰要隻做路先生。”
24.9萬字8 25546 -
完結830 章

裴少寵妻成癮
“喜歡我,愛我,眼睛隻許看我!”男人咬著她的唇,霸道宣告。為了讓她留下,不惜逼她懷孕產子。“裴慕白,你就是個瘋子!”她嘔盡最後一滴血,硬生生割裂了和他所有的聯係,他崩潰嚎啕卻於事無補。多年後她於人海中出現,長發及腰笑得妖嬈。“好久不見,裴總,有沒有興趣一起生個孩子?”男人咬牙切齒:“我倒缺個女兒,你感興趣嗎?”
150.7萬字8 4190 -
連載824 章

二嫁頂級豪門,婁二爺悠著點腰啊
領證的路上,言茹茵遭遇車禍,昏迷了三年。再次醒來,丈夫因車禍失憶,怪她惡毒,說她棄他不顧,身邊已另有新歡。 言茹茵對這種眼盲心瞎的男人沒有挽回,離完婚扭頭會所偶遇一個寬肩窄腰、八塊腹肌身體好的小白臉。 小白臉又欲又野,卻不要錢要名分…… “寶貝,你快跑吧,我跟我老公還在冷靜期,這點錢你拿著,我怕他打你。” 言茹茵丟了支票就跑了,電話都沒留。 第二天,言茹茵跟冷靜期的丈夫參加婁家家宴,見到了那位傳說中神秘狠辣的婁二爺。 男人將她抵在墻角:“錢我要,人也要!都是我的。” 言茹茵驚:“二,二哥??”
144萬字8.18 95736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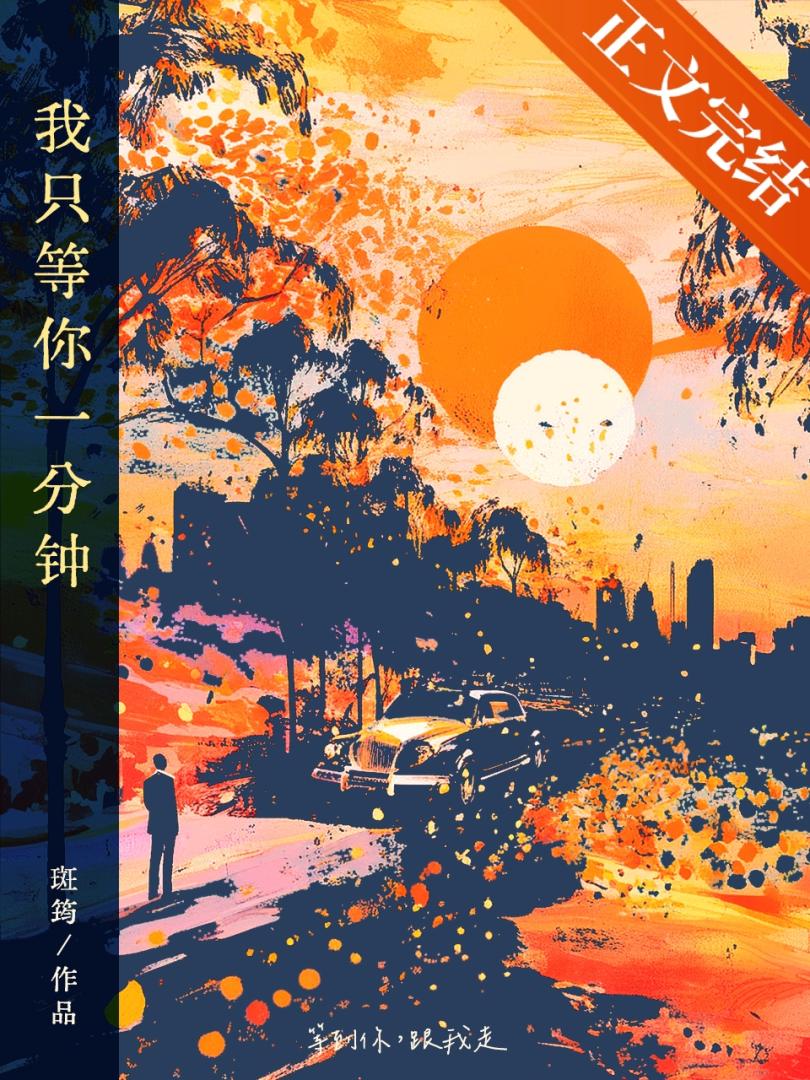
我只等你一分鐘
為躲避催婚,卿清也開始聽從母親的安排相親,意外與萬俟延相遇。此時的他已經成為新聞報道裏的科技新貴,中國最強游戲制作人,美國海歸,同年少時大為不同。卻是一樣的氣質冷峻,淡漠疏離,仿佛任何人都無法輕易靠近。決定領證時,二人已有6年未見,卿清也稍顯猶豫。她站在民政局門口思考,還未等捋清思路,便看到有人迎面走來,臉色冷冰冰的,足足盯了她5秒鐘,才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地問她:“不進來,站在門口做什麽?”這目光帶有重量,卿清也忍不住後退,忽聽他開口:“你可以現在走,走了就沒有下次了。”卿清也的腳步倏地頓在原地。緊接著,她聽到身後人語調平靜地說:“我和你,只有做夫妻和陌生人這兩道選項。”*在外人看來,這兩人一點都不搭、一點都不合適,他們的婚姻就像是兒戲,遲早要完蛋。但卿清也并不覺得,他們約好了不告訴父母,也不互相幹涉,并且萬俟延領完證就飛往國外工作,一去就是許多天。卿清也也開始忙起泥塑事業,沉醉忘我,晝夜顛倒,全然忘了自己已婚的事情。然而某天她忽然收到一條消息——【夜不歸宿?】這條尚且還讀不出那人的情緒。可間隔半小時後的下一條,萬俟延又給他發來一則消息,是一個簡單的“?”。小劇場:①某天,卿清也接到她母親的電話,徐蕙蘭氣勢洶洶地問她:“檔案上顯示你已婚,是怎麽回事?”卿清也裝傻充愣:“你聽誰說的?”徐蕙蘭:“警察。”卿清也:“假的,別信。”徐蕙蘭:“......你最好給我一個解釋。”②兩家父母來找他們討要擅自結婚的說法。卿清也把萬俟延拉到一旁商量對策,她沒想到會遇到這麽棘手的場面。還沒商量好,就見萬俟延轉身走到父母面前,隨即,卿清也聽到他說:“爸爸媽媽們。”他的態度端正,讓對面的父母們也不自覺正了正身子。卿清也走過去,坐到他身旁,打算聽聽他的解釋,下一秒,就聽他說——“我希望你們不要破壞我的婚姻。”卿清也:“......”父母們:“......”一個沒良心VS一個死心眼—————————————————————預收文文案:文案1:家裏即將破産,為幫母親分擔債務,郁芣苢答應去相親,一路猶豫不決地在酒店盡是蓮科名的包廂門前打轉,最後在“芙蓉”和“芙蕖”當中任選一間,走了進去。哪知,繞過黃花梨木嵌雲石插屏,卻看到對面露出一張矜貴清冷的臉。他正在接電話,聽聞動靜,冷冷地朝這邊掃來一眼。郁芣苢慌忙道歉:“抱歉,我走錯包廂了。”轉身就跑。薄言初本在跟母親討價還價,他不理解為什麽這樁生意非得自己來談。待看到誤入包廂的人奪門而出,薄言初趕忙起身去追。正巧,對門也同時打開,他看到“芙蓉”裏頭出來一對挽手的璧人,再看身側郁芣苢臉上露出“大事不妙”的表情,當即明白了是怎麽一回事。想到郁芣苢當初同自己提過的分手理由,薄言初當即沉下臉來,質問她:“你來相親?”“你跟他就合適?”*搞砸相親的當晚,郁芣苢抓著手機思考該如何同母親交代,意外翻到了分手那天薄言初給她發來的消息:【你考慮清楚了嗎?】時間來自半年前。郁芣苢深思熟慮後,冷靜地給他回複:【我考慮清楚了,我答應跟你結婚。】薄言初不理解,并且很快地給她回來一個無語的“?”。*常年潛水、一言不發的薄言初,某天突然在家族群裏發了一張自己的結婚證照片。薄母先是鼓勵式地對他表示了真心的祝福和恭喜。過了三秒,意識到不對,又發來:【不是,兒子,配偶欄那裏的名字是不是不太對?】文案2:薄言初一側過臉,不看她,郁芣苢就知道他生氣了,不想搭理自己。每次遇到這種情況,她就會把平日憋在心裏強忍著沒說的話沖他一頓瘋狂輸出。等到他終于忍不住皺起眉回看自己,想問她是怎麽回事之時,郁芣苢就會翻臉一樣,笑著對他說:“別生氣了嘛。”一個忘性大VS一個氣性大內容標簽:都市情有獨鐘青梅竹馬婚戀業界精英輕松卿清也萬俟延(mòqíyán)郁芣苢(fúyǐ)薄言初其它:@斑筠在流浪一句話簡介:等到你,跟我走立意:成為更好的自己
22.8萬字8 815 -
完結348 章

認錯白月光后,我慘死,他哭瘋
在向我求婚的游輪上,傅寒燚將兩億天價的鉆戒,戴在了養妹的手上。那時我才知道,這個對我謊稱得了絕癥,讓我拼死拼活為他攢錢買續命藥的男人: 竟然是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金融大佬。 可他偽裝成窮人,玩弄我的真心。 他把我賣血換來的天價藥,一顆顆扔在地上,讓我被他們的上流圈子嘲諷。 他們說,窮人的真心可笑又廉價。 在生命消逝前的幾分鐘,我不甘心的打電話向他求救,他卻讓我去死。 我終于歇斯底里:“傅寒燚,明明是你隱瞞身份對我戲弄,為什麼你卻像個批判者一樣堂而皇之的踐踏我?” 他輕蔑一笑:“溫媛,等你死了,我會在你墳前告訴你。” 如他所愿,我真的死了。 可當他發現我的尸體被迫害得慘不忍睹時,整個人卻咆哮了。 再醒來,我重生在她人的身體里。 傅寒燚跪在我的墳前懺悔:媛媛,欠你的,我很快就能還了……
57.7萬字8 78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